文/Bogie
“即使走在最明媚的陽光下,腳下也會一直有陰影存在。”

舊日陰寒
19世紀末,大批意大利移民湧入美國。新奧爾良是當時意大利移民大舉進入美國時最主要的登陸地,由於意大利到美洲的移民首站通常是巴西和阿根廷,而新奧爾良港又有大量的船隻與其通航,因此這座城市聚集了大批意大利移民,也包括來自西西里的黑手黨。從貧民窟崛起,並以敲詐勒索等種種不法手段給這個城市帶來災難的暴民同樣混跡於其中。
《新奧爾良時報》曾報道:“臭名昭著的西西里殺人犯、造假者和竊賊已經佔領了這座城市,他們組建了犯罪集團公司,正給這座城市帶來侵略與騷亂。”

當時的市長還曾公開稱這幫來自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移民是“生活在我們之中最懶惰、最邪惡、最低賤的一群人”。他甚至對此發出威脅:“為了結束這些邪惡的意大利人到處騷亂的局面,如有必要的話,我們得把所有意大利人扔出地球。”
身處浪潮中的犯罪群體其不斷激生的醜惡暴行無疑劣化了移民在當地群眾眼中的印象,加之政府官方與各路跟風媒體後續一系列對於移民形象的不良輿論導向,使得這些初來乍到的意大利移民不管善類與否,在新奧爾良的生存都變得愈發艱難。

很快,一個惡性循環就此誕生。為了求存,一些黑手黨成員、罪犯、以及部分普通意大利移民開始自發地抱團組成幫派,在新奧爾良從事各類灰色活動。據估算,1888年至1890年這十年間,在新奧爾良僅涉及意大利黑手黨的謀殺事件就有40餘起。
當時在新奧爾良最臭名昭著的兩大黑手黨組織是普羅文扎諾家族和曼特蘭加家族,但在他們最肆無忌憚時,卻碰上了一位剋星:警察局長大衛·軒尼詩(David Hennessy)。
這位局長誕生於警察世家,他的父親老軒尼詩是美國內戰時期的老兵,戰爭結束後就在新奧爾良應職擔任警察。1869年,老軒尼詩被同事謀殺,當時大衛·軒尼詩才剛剛12歲。就在父親死後第二年,大衛·軒尼詩心懷信念,申請加入新奧爾良警隊。在一次街頭巡邏中,小軒尼詩曾憑藉赤手空拳與兩名盜賊搏鬥,最終成功將他們逮捕入獄——虎父無犬子,由於他在職期間的優異表現,軒尼詩在20歲時就成為了一名正式警探,在新奧爾良可謂聲名鵲起。

大衛·軒尼詩下車伊始就著手於對警隊內部進行大刀闊斧的清理改造,一掃新奧爾良警察無能腐敗的消極風氣。同時,為了從根本上改變新奧爾良的治安情況,軒尼詩開始拔刀直向黑手黨,首當其衝的便是普羅文扎諾家族和曼特蘭加家族這兩大勢力。
在此時期,軒尼詩通緝並逮捕了許多普羅文扎諾家族的成員,併成功將他們從幕後推上法庭。而且,當時還盛傳軒尼詩將在法庭上出示一系列決定性的證據,這些證物不僅能將普羅文扎諾家族一網打盡,還能連帶把曼特蘭加家族也一同送入監獄。
軒尼詩是個好警察。但軒尼詩卻沒能活到黑手黨被消滅的那天。1890年10月15日晚上,已為局長的軒尼詩如往常一般下崗回家,途中意外遭遇了數名來路不明的槍手。他因此連中數槍,且反擊未果,在一片混亂的槍焰聲中倒地不起。趕來的同事在把軒尼詩送往醫院的途中,軒尼詩只低聲沙啞地說了一個單詞——“意大利人”。

在這之後,新奧爾良警隊執令抓捕了大批黑幫成員——其中足有19人被認定為黑手黨成員且與有涉於局長遇刺之案。但最終審判時,卻有16人以無罪的名義被法庭釋放,陪審團對剩下的3人也始終無法給出斷罪的定論。
審判後的次日,因不滿於結果而憤怒的市民轟然聚集於監獄門外。他們強行打開獄門,將那19名意大利嫌犯拖行而出,其中9名意大利人被殘忍槍殺,2名意大利人被活活吊死。而這被處決的11人中僅有3人被確定逾越了法律的邊界,1人是眾所周知的黑手黨同僚,但其中至少有5人並沒有在案的犯罪記錄。這一事件無疑在新奧爾良埋下了一顆仇恨的種子。
變異刺客
路易斯安那州的事件隨著“變異刺客”的出現形成了一個令人詫異的轉折點。在刺客出現之前,大部分怪物都具備強悍的直接性行動實體——儘管它們原是為其他目的而設計的。但是這具有完整人形姿態的“變異刺客”卻似乎是專門為了震撼與摧毀人類而降生的。

在大多數可溯的目擊報告和調查資料中,對這一異常生物的描述基本是相似的:不知是由於某種古怪的戲法,還是生理上的特殊變化,這隻體型高大的人形生物似乎隨時能自主地轉化為一大片昆蟲。與此同時,“變異刺客”還擁有著多項堪稱非凡的能力,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它能夠分化出最多3個偽身,這些偽身甚至具有獨立行動性,能夠作為一種誘餌吸引乃至襲擊目標,分散其注意。
而如果想要更為深入地分析有關“變異刺客”的所有線索,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傳奇般的獵人人物,他的經歷以及與“變異刺客”的遭遇能夠為我們提供許多寶貴的參考。

“他在各行各業中所接受的‘大雜燴式教育’使他獨具慧眼,看到一般人難以洞見的聯繫,在他人只能看到瘋狂的地方看見理性。”
研究員哈羅德·布萊克(Harold·Black)並非一開始就是一名獵人。曾就讀於哈佛大學自然科學系的他因在校時對世俗生活感到不滿而決心輟學,走上從戎之路,並小有成就。不久後,父親的過世為他獨立闖蕩的理想斬斷了最後的牽掛,他開始一路向南而行。
1890年10月,哈羅德在當地的一家報社擔任特派記者,出於職業需求與個人興趣,他也是大衛·軒尼詩遇刺案的跟進者之一。經過多日的追捕與盤查審問,在仍未找到真兇的情況下,警方仍因案關押了19名意大利人。在結審的第二天,哈羅德正好在現場親眼目睹了暴民們對囚犯所施的私刑,野蠻的行徑讓他不忍直視。而當他準備返身離開時,一名身處人潮外圍的男子吸引了他的目光。他的身材高大健碩,情緒憤然,但哈羅德卻從他的舉止中嗅出了一絲詭機,幾番斟酌後,哈羅德決定對他展開跟蹤。

行至半程,哈羅德終究沒能躲過男子的察覺,隨著從監獄裡傳出的一聲槍響,二人之間的一場追逐也進之展開,那時的哈羅德還尚不知曉對方選擇逃跑的緣由。
直到哈羅德將男子逼入某個巷陌角落之後,哈羅德才得以窺見那異樣的根源——只見男子猛然轉身,將一團裹挾著甲蟲的塵灰甩打在哈羅德臉上。而當哈羅德艱難地重新恢復視線時,眼前的一幕卻突破了他對於人類的過往認知:那男子正在以某種奇特的運動方式攀爬著一面臨近建築的剪力牆,懸掛其上後,還揮手朝哈羅德擲出了一柄匕首,雖然在哈羅德的驚慌騰挪之下並未命中,但男子卻趁此機會消失在了哈羅德的視線之中。

在回到崗位遞交這一新聞專欄後,高級編輯約翰·C·維克菲(John C. Wickfield)並不認可哈羅德對於私刑場面的描述與觀點,因為此人當時也位列私刑者行列當中。在爭執中,哈羅德失去了報社的工作。而後路易斯安那州的副州長希拉姆·R·羅特(Hiram R.Lott)倒獨具慧眼地相中了他的才華,僱傭了哈羅德幫忙執行基層的文職工作。前職場令其不甘的教訓與現職場日復一日的枯燥生活在極大程度上消磨了哈羅德的意志,每個昏沉的夜晚他幾乎都酒不離身,也是在那時候,哈羅德遇見了一位好友,他叫做文森特·奧斯卡(Vincent Orsica)。
由於深夜常能在這樣那樣的酒館和吧廊裡相遇,兩人很快便認知併成為了朋友,年長几歲的文森特就著冰涼的威士忌與點燃的菸灰,為哈羅德提供了不少誠懇的學習與工作建議。

一年光景轉瞬即逝。隨著日益俱增的信任,哈羅德開始向文森特分享各種秘密,而文森特似乎也對哈羅德口中的職場故事與生活經歷很感興趣,並與其多次談心。另一面,文森特也對哈羅德長期沉湎於酒精之下的身體狀況深感憂慮,於是決定帶著他去一處附近的森林裡散步,偶爾練習一下槍法,這樁活動到後來漸漸變成遠足和狩獵,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哈羅德的健康情況,也為他提供了豐富的野外經驗。
在最後一次與文森特相約的夜晚,他們一直暢飲到天明。其間,哈羅德向文森特分享了一則趣聞:他的僱主羅特先生,十分堅定地相信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的運河會穿過尼加拉瓜,儘管哈羅德嚴厲批評了他不應為這些蠢事而拋棄公務,也仍無法阻止羅特先生當天下午乘船前往尼加拉瓜的行程,而哈羅德也因此再次失業。
直至破曉時分兩人才晃晃悠悠地離開酒館,興許是酒精的作祟,文森特的背影在哈羅德的眼裡似乎隱隱分裂,並最終同時消散在了小巷深處的漆黑之中。

不久後,雖然與曾經的寫作領域相去甚遠,哈羅德倒是在一位名為薩姆森(Samson)的人那找到了一份嶄新的工作——成為了一名獵人。而通過薩姆森的介紹,他同時還結識了另外一群年輕的同行,以便在日後的任務中結伴互助。
作為獵人直面威脅的那天還是來臨了。那時他們正步行於勞森路的新監獄上層,恐怖的伏擊不期而至,首先其中一名獵人受到了一團未知蟲群的突襲,它們爬過他的臉,滲進其嘴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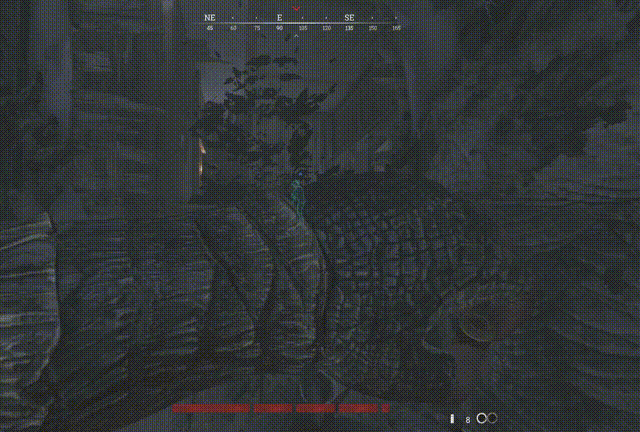
那名獵人在尖叫中驚慌失措,卻全然沒有注意到從其背後迅速升起的一抹陰影——眾人顧不及驅散飛蟲,只驚恐地察覺他背後的陰影凝聚變化,最終形成一具人形。
電光石火間,那具人形便將利刃刺入那獵人的肚腹,這是目擊報告中所提及的“變異刺客”的第一次殺戮。眾人緩過神來後,便火速拉動扳機朝那身影射擊,但卻無濟於事,在眾人的視線中,它正以某種古怪的形式分裂為多個偽身,向獵人們衝襲而來。
這是哈羅德首次成為獵物,身前的致命身影與周身的蟲群才是真正的獵人。顯而易見,他的射擊沒有產生任何實際的效果,子彈在鐵石上彈開,蟲群沒有受到影響。眼見情勢不妙,他只能趕忙越過支架,衝過房門,跨過戰友們的屍體,跌跌撞撞地跑出迷宮一般的監獄。回想起那道身影空洞的臉龐,出奇的有幾似曾相識——在那層陰霾之下,他似乎看見了文森特。

脫身以後,哈羅德將他寒酸的住所翻了個底朝天,尋找每一片存有字跡的紙張,以及每一段在時間長河中被遺忘的痕跡。他為此還登門拜訪了心理學家,甚至當地的神棍,為的就是通過一切手段回想起關於文森特的一切。
憑藉著一張皺巴巴的紙條和外界多方提供的線索,他最終還是找到了文森特的住所——那是一個破爛不堪的閣樓,幾乎沒有任何傢俱,從窗口能俯瞰到當年執行私刑的監獄。當哈羅德重返街道時,他才意識到自己曾來過這,當年那個行徑古怪的男人就是在眼下這條巷子中消失不見的。
某個偶然,哈羅德在沼澤的一處廢教堂裡找到了一位名叫格蘭頓(Glenton)的年輕獵人,他也曾與“變異刺客”遭遇,那場戰鬥一直從深夜持續到天明。戰鬥的結局以格蘭頓用手中的Romero霰彈擊中“變異刺客”的胸膛作為落幕,他活因此而活了下來。而當哈羅德詢問這場戰鬥的發生場所時,他笑了笑,略顯吃力地伸手指了指這座教堂。事實上,他就是在等它回來。

哈羅德回到城鎮後,便開始著手整理線索,並藉此號召其他獵人,籌劃起一場針對“變異刺客”的獵殺。然而實際情況卻與哈羅德預想的不同,隨著“變異刺客”行動的增多,哈羅德先前所積累學識與研究已然成為了獵人們最為寶貴的指南,他們承諾會將賞金分給他,但絕不再允許他以身犯險。
換句話說,獵人們極力希望他能夠繼續進行對這一怪物的研究,為他們指明行動的方向,思考權衡之下,哈羅德最終同意了這份“用知識武裝獵人”的幕後任務。
而這亦是哈羅德·布萊克日記的起源,也是這本日記會到達我們所有獵人手中的真正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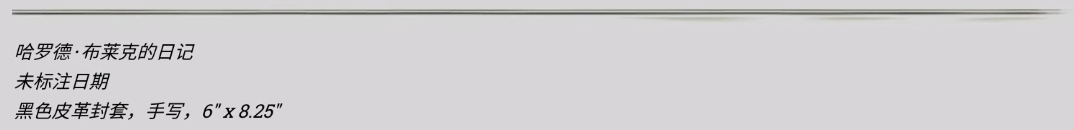
蟲與利刃
在對“變異刺客”於遊戲中的故事進行整理後,我們可以得出“變異刺客”的原型就是研究員哈羅德的好友文森特·奧斯卡的事實。在被黑暗徹底侵蝕成為一具行屍走肉的怪物前,文森特就已掌握了諸多過人技巧(哈羅德與文森特的初見是在1890年,遊戲中瘟疫的大規模爆發在幾年之後)。而從背景故事中所涉及的那段真實美國往事來看,由大衛·軒尼詩刺殺案所引發的一系列新奧爾良平民暴動私刑事件,多半與“變異刺客’的原型文森特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文森特·奧斯卡本是從大洋彼岸漂洋而來的意大利移民,掌有一身本事的他同樣是為了追求飄渺的美國夢而來到這片新大陸。但現實卻向他展露了殘酷的獠牙,無業移民的身份使他在這座魚龍混雜的城鎮中如同無根之葉,加之外界對移民身份的排擠,生存環境每況愈下,只能在髒活累活的間隙下苟且偷生,酒館幾乎成了他消遣的唯一去處。

但接踵而至的爆發性事件卻徹底擊碎了他心中最後一絲對這片大陸的嚮往——親眼目睹同鄉同族甚至是至親之人被汙衊並加以處刑。但他彼時的身份,已然是名優秀的獵人,他知道自己需要對抗的目標尚在高處,為了等待時機,他必須選擇隱忍。有意或無意之下,他盯上了副州長希拉姆·R·羅特手下較為親密的文員哈羅德·布萊克,長久的往來與信息交換最終給他帶來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並最終將羅特置於死地。而長期被複仇私慾所吞噬的他也被另一維度的邪惡選中,讓他化身成了河口的又一具恐怖實體:“變異刺客”。
精妙的是,文森特的名字“Vincent”與一個起源於意大利語的單詞“Vendetta”有著一些結構性的相仿,而後者的意思恰好便是“仇殺”。並且“Vendetta”一詞也曾作為一部電影的名字在1999年上映,這部作品在國內被譯為《天堂夢醒》,而影片所描述的核心故事正好就與新奧爾良的暴動私刑事件息息相關。

相比起豬面的“狂暴屠夫”和詭異的“人形蜘蛛”,“變異刺客”的外形顯然要收斂許多。瘦高的軀殼之上沒有任何多餘的毛髮,唯一的“裝飾”就是掛在身上那件殘破的黑色風衣以及雙手上作為攻擊手段的利刃,精煉的肌肉結合空洞的面部倒頗有些許歐美都市傳說中“瘦長鬼影”(Slander Man)的獨特韻味。
除此之外,在“變異刺客”的整體設計中最為突出的元素必然就是那渾身環繞的蟲群。無獨有偶,這一設計也在《生化危機8:村莊(Resident Evil Village)》中表現驚豔的“三女兒”身上有所體現。RE8中的“三女兒”可以利用隨時轉化為蟲群的機制巧妙地規避傷害,在前期探索過程中遇到她們,玩家基本都得退避三舍,直到劇情推進到玩家發現了她們的弱點後才能將其擊殺。其間的設定和“變異刺客”近乎是一致的:藉由蟲群狀態下的“無敵”之身,怪物便能毫無道理地將玩家設於“無力化”的弱勢地位,在與其戰鬥的過程中進而產生獵殺與被獵殺之間關係的模糊處理,使初見怪物的玩家激增對於這位“獵手”的恐懼。

在許多恐怖角色的設計中,蟲群的作用不言而喻,無論是上文所提及的“三女兒”和“變異刺客”,還是影視作品《康斯坦丁(Constantine)》中出現的由各類節肢昆蟲結合成的惡魔實體“害蟲”(Vermin Man),蟲群這一具象化的存在都能將“汙穢”與“惡”的意象高度綁定於角色設定。
而從生物概念上看,蟲群卻又總能予人生命力頑強、難以殺絕的特徵,由於其誇張的繁殖能力與群居性的生理習慣,使其成為一類難纏的聚集型敵群。籍此,我們在各種作品中也不乏能看到蟲群對於常規攻擊手段的超常免疫性,與群起而攻時所產生的可怖毀滅力。

再者,蟲群自古以來就為人類的生產生活造成接連不斷的困擾。在其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的加持下,它們啃食乃至摧毀大規模的糧田作物的先例不勝枚舉。而在《聖經》的《出埃及記》故事中也曾提及,耶和華為了懲罰法老王的剛硬,便在埃及連續降下“十災”,其中的第七災便是蟲災(蝗災),在這一浩劫中,蟲群直接沖垮了人類原本穩固的糧食生產體系,自此,人類對於饑荒的恐懼便成為了蟲群所帶來的另一面威脅映射。
毫無疑問,蟲群成功賦予了“變異刺客”最為顯著的能力標籤,但如若拋去蟲群這一設定,它相比於普通人類的異處卻僅有那張空洞腐敗的臉龐。這層不詳的朽鏤於暗中低聲訴說的,或許就是“極端仇恨”所應得的最終落幕:投身黑暗者,必將被黑暗所噬。

「這裡是怪物學術,讓我們來聊聊怪物與怪物之外的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