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推想小說,當代文學又如何把推想作為一種方法?這一期,我們邀請到青年作家雙翅目、慕明,常駐嘉賓宗城,一起從具體案例出發,對談推想小說。
【本期主持】
趙一靜:幕後的幽靈
【本期嘉賓】
雙翅目:科幻作家,喜愛理論與幻想的連續體,出版《公雞王子》《猞猁學派》
慕明:科幻作者/程序員,以小說搭橋,作品集《宛轉環》籌備中
宗城:小說和評論學徒/席地而坐發起者
Part1:何為推想小說

圖源:《燃燒女子肖像》
宗城:我們先從科幻文體的危機聊起。在劉慈欣的小說《三體》成為現象級作品後,科幻文學崛起成為一個主流判斷,但是在科幻小說家眼中,這一判斷未必成立。在在豆瓣閱讀前主編徐棲的文章《從科幻到推想小說的變與辯》,作者開頭就寫道:“被我們叫做「科幻小說」的文體,正處在一個危急關頭:再不進入主流話語中,它遲早要被遺忘和消亡。”為什麼科幻小說的文體會面對危機,作為方法提出的“推想”又如何回應這一問題?
雙翅目:大家在讀科幻小說時,會發現單純靠一個特別好的點子,也許能撐一個短篇小說。如果人物情節寫得好,也許能撐一箇中篇小說。但是如果一個好的科幻作品要撐到長篇,它一定要根據這個點子做出一套比較完整的推演。這一套推演包括技術層面,或者社會層面,當然也可以包括人性層面,比如說《弗蘭肯斯坦》、《莫洛博士島》,哪怕像《格列佛遊記》中的大人國、小人國,也是在諷刺當時的社會政治。換言之,科幻小說的推想性,如果撐到長篇的一個體量,都要有對點子本身的推想。
我們可以從一個很簡單的角度去理解科幻小說和推想小說的區別。科幻小說,一般可以從一個點子去判定;但推想小說不一定要有技術點,就像《使女的故事》,它不是一個技術點,反倒是社會和整個技術世界退化而構建的世界觀。為什麼要脫離科幻去聊推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點子文學”有它的問題:現在大家都說開腦洞,但什麼樣的腦洞算是真正的、原創性的腦洞?什麼樣的腦洞就是一個段子?

這件事其實不管是在文學、商業,還是視聽語言的一個大市場中,有些時候是不好判斷的。對於真正好的幻想小說,它的內核需要這種推想性。而對於科幻,比較早的科幻理論家達可·蘇恩文(Darko Suvin)受過西方馬克思主義影響,他提出了一個定義:科幻是新奇性加認知有效。新奇性可以理解為“點子文學”裡所謂的點子。這個定義的適用性到現在也還比較強。認知有效這個詞來源於文學分析當中的認知疏離。但很有意思的是,達可·蘇恩文強調的認知有效,也就是說科幻小說構建的世界,一方面要疏離於我們現在的現實世界,另外一方面又要具有有效性,而不是全然破碎、崩塌的。所以在這樣的邏輯下,科幻小說本身就要求從一個點子出發,然後生成一個“可能世界”。黃金時代的作者基本上會以這樣一個思路去創作。
推想性小說,即speculative fiction,這個概念反倒是黃金時代的“三巨頭”之一海因萊因提出來的。他當時提出的一個背景就是冷戰時期。黃金時代的科幻作者中後期的創作,和新浪潮時期的科幻作者的早期創作是重疊的。所以,基本上70年代左右的時候,在美國或者說英美的科幻圈裡面,黃金時代與新浪潮同時進行創作,既可以看到新浪潮作者有“點子文學”的那種感覺,也可以看到黃金時代的作者走向推想小說。
這個時候,海因萊因本身就比較擅長寫社會類小說,尤其是寫在各個流派上都很政治不正確的小說。他才會提出推想,注重思想實驗,也就是想撇開飽受詬病的“點子文學”的侷限,去深入小說本身的結構性。結構性決定了推想類小說的質量,結構的完整性和審美特徵,決定推想類小說的藝術品質。
我們今天想分析的就是這種小說本身的內在結構。比如,以後會聊到的勒古恩,就會稱之為思想實驗。內在的結構既可以是對於社會體制的一個推想,像《1984》。當然,這種烏托邦類的小說基本上出現在現代性社會誕生以後。英國進入大航海時代,看到了其它不同的世界,在這樣的背景下才產生了去構想完整異世界的能力,而不完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構想。而另外一類對於“何為人”的異種的構想,從《弗蘭肯斯坦》開始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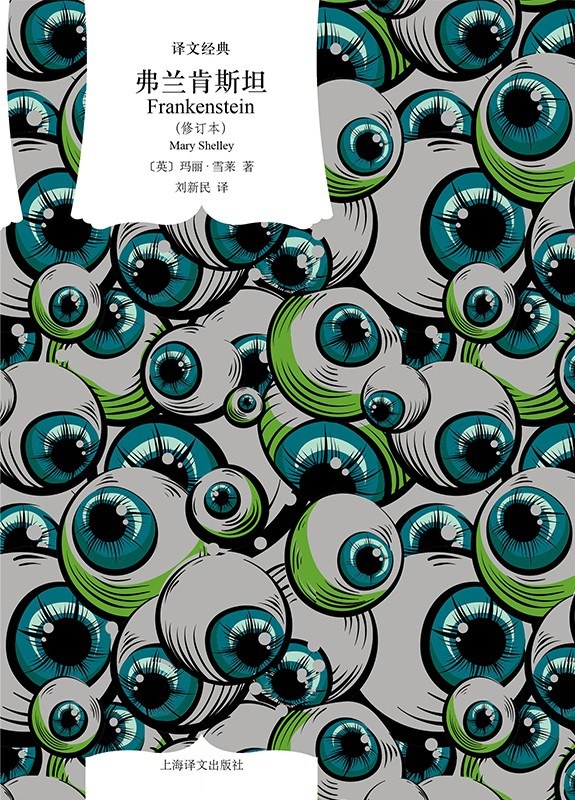
從這兩個層面來說,當科幻經歷黃金時代,進入新浪潮的時候,大家已經不再強調“點子文學”,而強調推想的結構性和認知的審美。
後來,在賽博龐克,或者說新浪潮晚期時候,美國的後現代文學作家跟新浪潮的科幻作者有過一段不分彼此的文學交流。期間誕生了如文學方面的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科幻方面的迪克(Philip K. Dick),他們在文學和推想的先鋒性上都達到了比較極致的狀態。如今歐美文學有成熟的主流文學和類型文學的混合,但國內的情況不太一樣。什麼是推想,什麼是思想實驗,什麼是文學結構本身的審美特徵,國內對於這些才剛剛開始去討論和反思。
慕明:我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我每次聽到科幻小說的時候,都有一個問題,我想知道科幻小說在讀者和聽眾心目中的定義到底是怎樣的。我覺得現在大家可能很多時候並不能從科學史的角度理解什麼是科學。科幻小說的英文是science fiction,直譯就是科學小說,所以我覺得可以先做兩個辨析,第一,什麼是science,科學,第二,什麼是fiction,小說。
科學本身其實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它是一個變化的概念,它甚至不是一個進化的概念,而是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為“範式轉移”的過程,這個概念是托馬斯·庫恩提出來的,他是上世紀最著名的科學史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裡提出來,大家可以看一看,相當於是一個針對科學本身的達爾文主義的研究,它就是想研究為什麼以前的科學共識在經歷了發展之後,它就不是科學了,新的科學到底是什麼?我們到底是怎麼定義科學本身的?
我在這邊做一個非常粗淺的總結,托馬斯·庫恩認為,科學可以看做是一種人對客觀事實的不斷建模表述,根據新的觀察,不斷去修正以前的東西,並且我們發現這些非常重大的科學進展,在剛開始的時候幾乎全都是不被接受的。像數學史的第一次危機,希帕索斯發現了無理數,畢達哥拉斯學派立刻認為他是異端,把他給扔海里去了。比如說“日心說”、“地心說”、“日心說”這個大家很熟,布魯諾被燒死了。“相對論”,當時諾貝爾獎也沒有給愛因斯坦,給的是他的光電效應理論,“達爾文進化論”,這不用說了,這個不光是科學界,整個社會都產生了非常激烈的反對。
所以說當我們討論科學的時候,我們不要把它看做是一種固定的東西,它更多的是一個過程。我看過很多人就批評說這個東西不夠科學,或者說這個物理學上就不夠硬,那我很想問問這些對“什麼是科學”有特別強烈的觀點的讀者,你依據的是中學物理、大學物理、研究生物理還是《三體》裡的物理,它都是一個變化的東西。
如果討論科學的話,更多的應該是從思考方式和認識論來討論。如果你真的對科學發展史和現狀比較瞭解的話,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現在越來越多人,不管是老師也好,或者前沿的研究者也好,他們意識到什麼?他們意識到了,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知識是呈指數增長的,指數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牛頓革命以來,人類的知識每17年倍增一次,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算,這個數都不是我說的,是一個叫理查德·漢明的這樣的一個ACM的fellow,然後也是最早的圖靈獎獲得者,他算的。他基於的是什麼?他基於的是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90%的科學家現在還活著,這就是指數的意義。
另一個意義,是每15年學校裡教的知識——當然他講的主要是像信息科學或者比較偏應用的東西——每15年很多知識都被淘汰了,這個就提醒我們不要以一個靜態的眼光去看待科學。他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知識指數增長的時代,只教授已經精心打磨過的理論和證明是沒用的,我們必須放棄那種帶我們遊覽數學畫廊式的教學,而是講授怎麼創造出我們需要的數學的方法。在我看來這是唯一的長期方法。
這裡面我們就看到了,真正搞前沿科學的人,他其實對科學的概念是更接近於我們所說的認知,或者說Speculative,的概念。它教授的不是一個確定的概念,而是一個方法、一個道理。這個就是我對科學的辨析。
那什麼是Fiction?Fiction也是一個變化的概念。虛構的傳統可以追溯到《荷馬史詩》,但我們現在所說的Novel是一個很晚近的產物,它是市民階級興起之後的一個產物了。
那剛才我說了,文學書寫最早就是對夢的模仿,我們如果要去回想一下Fiction,或者說去回想一下虛構,我們發現最早的這些神話史詩,甚至是歷史本身它都充滿了所謂現在不入流的這個幻想,幻想對真實的影響,現在雙雪濤他們搞奇幻小說,但這東西你如果去讀讀《左傳》,《左傳》裡全都是這玩意,就都是做夢。像晉文公他在城濮之戰之前做了個夢,夢見他跟楚王兩個人單挑,晉文公被楚王一下就壓在地上。楚王趴在他身上吸他的腦子,這個夢可不可怕,是不是非常的哥特。“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嘏其腦”,就是吸他的腦子,當時晉文公覺得,這個夢要對我產生什麼影響?當時有主戰、主和兩派大臣,主戰的大臣非常嚴謹地給他解夢說,大王躺在地上,向著天,楚王趴在他身上,是伏罪的標準姿勢,而且人腦是“柔物”,這代表楚王柔服,所以要打這一仗。另外一個人說這個夢是主和,每個人一套理論,大家去看《左傳》裡全是這種,幻想如何影響到現實。
包括像《信條》,現在像諾蘭這個時間倒流,《左傳》裡就寫過,《公羊傳》裡寫“霣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 六隻鳥,鷁鳥倒著飛過宋都。
這些東西在以前是跟我們的歷史,跟我們的整個民族的文化完全扭合在一起的,它並不是幻想或者說是這些不現實的東西,它並不是憑空冒出來的,那為什麼這些東西還在不斷重複出現?是因為它其實反映了一種人類心理的底層慾望。這方面的書可以看弗萊的《批評的解剖》,包括像列維施特勞斯、榮格,他們都是認為神話或者說這些帶有幻想色彩的東西,是書寫潛意識的,書寫的是一些現在沒有辦法用我們的知識體系表述,但是可能在我們的潛意識中的東西。
所以我們發現,文學中的好多母題,它在不斷描摹這種所謂的幻想,比如我說了一個預言,我說了一個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沒有人相信。比如說像普羅米修斯的故事,俄狄浦斯的故事,卡珊德拉的故事,這些故事全都充滿了這種想象性的因素。包括像對時間的恐懼,他試圖直接表現一些想象中的東西。那為什麼這些東西現在不太在主流文學裡出現了?這個我們現在就不展開講了,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下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在其他的世界》,她是把這些問題都講得很清楚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從可能是工業革命以來的這個祛魅,使人不再相信魔鬼、上帝或者說這些幻想、夢境的東西,或者說這些語言體系所代表的其他世界的存在。
阿特伍德有個非常重要的論斷,就是說天堂和地獄現在都去了X星球,很多我們無法用日常生活,日常科學邏輯解釋的東西,它現在只能放到科幻小說或者推想小說裡了。在很久以前,在科學或者說工業革命出現以前,這些東西其實是一直跟人生活在一起的。
當然了我們現在講了science、fiction它倆都是流動的概念,你把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了,你就會發現這兩個詞好像還互相沖突。如果是你用那種特別固定的想法去想什麼是science?如果你認為就是確定的事實,如果你認為fiction是一種虛構,那這東西好像就是互相沖突,這個阿特伍德也講了。所以我覺得就不要那麼去帶一個標籤,標籤在很多情況下他都是來賣書用的。把文學劃分為不同類型,是文學整體商業化的結果。這個表述在很多很多不那麼主流的文學大師那裡,他都會這麼說。比如阿特伍德的論文,她就說你就是看我寫的小說,就叫Novelist了,你叫我小說家,我不願意把商業化產生的標籤貼在我的作品上,這就是我首先想補充的。
另外一個就是剛才翅目講了很多科幻小說或者推想小說的一些經典的作品,我想說的其實如果大家把目光往放的遠一點,放的大一點,就會發現,異世界的呈現和構建的是推想小說最成熟的一種,也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剛才提到像《使女的故事》和《1984》這樣的作品。但是在我們現在這個語境中,只做異世界是不太夠的。這就是很多奇幻大片為什麼失敗,只做一個了一個特效很強大的異世界,可以給一個視覺衝擊,但是沒有思考的骨架支撐。
像是《使女的故事》,或者說像厄休拉·勒古恩的作品——這是另外一位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作家,大家可以看一下,短篇集《變化的位面》和長篇小說《黑暗的左手》,她以人類學手法寫的科幻或者推想小說——這些都是異世界,不管它是一個外星球,或者說是它是一個烏托邦或者反烏托邦,這些東西它都是為作者思考的意圖而服務的。
你如果只做一個異世界,只去描述這個世界怎麼奇怪,他可以說是一個形式,但並沒有真正的表現出你的意圖,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諾蘭他有點走火入魔,這些方法可以用,但這是外家功,內家功夫是對這個人生或者說是對現在的社會環境整體的思考。所以我們就是看《使女的故事》,或者說看《黑暗的左手》,很多文學評論把它作為一個女性主義,或者說是一個後現代思潮來看,而不是說把它作為一個異世界構建來看,為什麼呢?
因為這就是兩個方面,你是看這個東西的形式還是內容本身,你是看內功還是看外功,這兩個東西怎麼結合、怎麼互動有相當多的說法,但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作品可能並不會被劃分為科幻和推想,但它是利用了科幻和推想作為方法的。還有一些別的作品其實不在我們傳統的叫做推想的這個門類裡面,也是用到了非常強,而且是非常嫻熟的推想的技巧,比如說託卡爾丘克這個諾獎得主,她的成名作《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其實這部作品中我感受到了非常強大的榮格的理論的意象構建,因為託卡爾丘克本人也是心理學出身的,好像是給人當心理諮詢師,就是在開始全職寫作之前。所以你可以看到她很多意象的構建,包括“星群敘事”這種散點式敘事,對神話原型,包括民間傳說的引用和補完,都是基於一些融合的心理學理論去構建的。

波蘭作家託卡爾丘克
這些東西,如果你只去把目光集中在科幻小說這個類別的話是看不到的。我想特別提到的反而是另一類作品,我覺得在中文閱讀裡被提到的比較少,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是我讀過那些文學作品裡真正特別推想的,就是推想得特別難的,這一套作品是什麼?就是德奧系作家的一些作品,像赫爾曼.黑塞的《玻璃球遊戲》,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包括去年赫爾曼·布洛赫的《夢遊人》。這些作品都是那種大部頭,一般人也不會去看。
![作者: [奧] 赫爾曼·布洛赫,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品方: 中國圖書網,譯者: 流暢](https://image.gcores.com/84dceb62-6754-4952-a686-5f8db5a364ee.jpg)
作者: [奧] 赫爾曼·布洛赫,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品方: 中國圖書網,譯者: 流暢
《玻璃球遊戲》它講的是什麼呢?講的就是有一個異世界,所有的人把“玻璃球遊戲“當做一個學科理論的一個基礎,你可以把它理解為大家所有的學科理論和所有宗教信仰都圍繞著“玻璃球遊戲”展開,這個非常非常的可以講。其實赫爾曼·黑塞的《玻璃球遊戲》是得到了雨果獎的提名的,但是大家一般情況下不會去把這個東西當做一個推想小說或者科幻小說來看。
《浮士德博士》講的則是音樂宇宙學,這也是托馬斯曼通過構建一個虛擬的學科,來把他腦中的這些精神性的想法,這些非常巨大的思想體系囊括起來,他們用小說是幹這個事的。喬治.斯坦納的《語言與沉默》裡專門有一章討論這種寫法,他把這個東西叫做“畢達格拉斯文體”。
畢達格拉斯是古希臘數學家,為什麼喬治·斯坦納特別推重這個東西?因為喬治.斯坦納意識到了現代以來小說面臨的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這個世界變得特別特別複雜,尤其是喬治.斯坦納大概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寫的這一套東西,但是他已經意識到了知識的不斷膨脹這件事,現在使得小說它不再去試圖描述一種整體,不再是一種全景式的途徑,而更多的轉向體驗交換,一個很小的接口,一個人的故事。
所以喬治·斯坦納認為現在讀者不是很信任虛構,我們也可以想到現在那些很嚴肅的思想者,他有多少人是從小說裡來獲得對世界的認知的?現在可能即使是文學類的小說,非常嚴肅的文學類小說,可能也只是提供一種經驗,而不是一種真正的思考。喬治·斯坦納認為這個是小說的危機,這個其實不是科幻小說的危機。但是他反而認為是像托馬斯曼這個東西,這些試圖在小說裡建立一個真思想體系的這種東西,他認為布洛赫的東西,他說是一種小說、哲學、音樂、數學為一體,打破了傳統的邊界,斯坦納認為這種東西反而是對小說危機的一個救贖。
他認為文學家只有打破傳統的界限,因地制宜,廣納兼收,使得不同學科特長的內涵做文學之用,才能夠挽救語言的問題,才能夠解決說越走越窄的這樣的一個問題。當然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你要達到喬治·斯坦納這樣的東西,可能光搞搞數學、搞搞哲學、搞搞音樂可能還不夠,你可能還要懂信息等等技術研究的邏輯,公司體系、現代司法、流行文化,特別特別多,所以為什麼託卡爾丘克在2019年的諾獎演講裡就說了,“我們現在沒有準備好,沒有準備好怎麼去面對高度發展的時代,快速變化的時代。”所以託卡爾丘克就基本上是在那篇文章裡呼籲我們需要新的隱喻、新的故事、新的預言和新的神話,我們需要有科學知識去重寫、去重構很多故事。
所以現在這個時代對於寫作者,尤其是對嚴肅一點的小說寫作者,它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我們其實也變聰明瞭,這點上我是想吹一下雙翅目,因為她本身就是學歐洲哲學出身的,所以其實我覺得她的作品是更接近於德奧思想體系,更接近於所謂的畢達哥拉斯文體,而且她把握了這個關鍵。她的小說也寫了,她說幻想小說的特點就是“既通其理,文字可棄,現在萬事萬物都能網絡檢索,學會數學,懂得道理就夠了”,這講的是什麼?講的是,不是具體的知識,小說呈現的不是具體的知識,呈現的是思想的過程。
Part2:文學的自我革新
雙翅目:剛才慕明說的畢達哥拉斯文體就強調思想性,這種思想性本身對於問題是有影響的,比如說拿慕明的小說《宛轉環》、《沙與星》和《鑄夢》這三篇舉例,三篇小說彼此之間差異性看似比較大,文字和角色塑造上各有各的風格,但核心邏輯有一致性,只是放到三個不同的背景時代,需要有所契合,所以會出現風格差異。也就是說,推想小說本身內在機制的構建有點像設計遊戲,每個遊戲都有一個核心玩法,但核心玩法要跟它通過感性表達所營造的體驗搭配好,這樣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作品。而慕明每一篇小說中的核心機制與感性表達都達到了完美的匹配。這是我理解的當代畢達哥拉斯文體所需達到的狀態。
像慕明說的,信息時代的發展,以後5G、6G,增強現實和虛擬現實,對於我們的體驗是革新。它不是早年古典信息的時代,不是古典的、歐幾里得的時空就可以覆蓋和闡釋的世界。也就是說,我們如果不是從一個理性的角度,或者不是從一個算法推想的角度去理解推想小說,就會錯失現在社會很多因科學和技術而產生的感性體驗。而關於當代物質的體驗性研究,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媒介理論現在比較火。這些都說明了,技術、算法、像素點、屏幕,哪怕是我們天天乘坐的交通工具,它對於生活的經驗都有著重構。如何用文字或其它手段,將新經驗表達出來。這是當代的畢達哥拉斯文體,或者當代的推想小說所需要去做、需要去思考的問題。
我們面對的情況是,如何去寫推想類小說,把日新月異的信息和信息體驗放入其中。也就是說,現在同古代的邏輯不一樣,古代認為我們的世界是永恆的。比如做編劇的話,會被推薦看《千面英雄》,因為《千面英雄》裡提出了一個英雄先下降,再上升的過程,但這樣的神話人物弧線是一個非常古典的弧線。我們當代的弧線是什麼樣的呢?一個很直接的體驗是,我們的父輩經歷過不同的時代,所以不能認為一個人物的一生只經歷一個弧線。現在“碎片化”時代導致每個人的人生都要經歷不同弧線,每個人的人生都比大部分的公司和商業資本所運作的期限要長。
所以小說創作和推想小說的創作,要去超越現當代人生和現當代社會發展的短週期視野。對於人生,對於世界的長結構的變革,“上升、下降、上升”的人物弧線或故事弧線,反倒是一個比較短的狀態。所以當代英雄,比如《刺殺小說家》中的主角,他不一定在某一個世界或者某兩個世界經歷某種人物弧線,他可能需要經歷體不同的社會經驗和不同的人物弧線。當代神話人物的構建,或新的當代神話世界的構建,是當代文體危機和創作的背景,簡言之,如何去構建一個豐富視角和豐富視野的故事。這也是為什麼《冰與火之歌》非常受歡迎。因為《冰與火之歌》的小說和影視劇,對不同人物的視野具有豐富的構建。

《權力的遊戲》最終季
小說POV(視角)的處理,在我們中國有比較悠久的歷史,但視聽語言對於不同POV的處理,比較難。這需要視聽語言創作系統的完善,我國也是這些年才變得成熟。人們的審美能力才跟上。所以,面對現在的文體危機,可能會有人說視聽語言在衝擊小說,其實正相反,因為小說構建世界本身的結構,要先於視聽語言的編寫。這也是為什麼《刺殺小說家》選擇文本的時候,最看重的還是兩個世界之間的交錯關係,在電影中給予基本保留。我覺得文本性的小說或者劇本,作為構建的核心,是以後推想類小說或者推想類作品的樞要。
Part3:慕明和雙翅目如何與科幻結緣
一靜:我感覺聊了很多,就是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從不同的作者上,我們現在想了解輕鬆的話題,想問一下就是兩位科幻作家你們自己是怎麼跟推想小說或者跟科幻結緣的?然後最初啟發你們的作品都有哪些,你們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比較有趣的經歷可以分享給大家呢?
雙翅目:我還蠻簡單的,從小看《機器貓》長大。現在《機器貓》叫《哆啦A夢》了,但是當年我看的時候它還叫《機器貓》。《機器貓》之後看《凡爾納》。當時我看的《凡爾納》還不是全本,是一個縮寫本。現在這樣好的縮寫本不多了。它是把《凡爾納》最經典的三部曲,還有《從地球到月球》、《地心遊記》合在一起,縮編為一本書。《凡爾納》和《機器貓》對於我來說是科幻的啟蒙。所以,雖然我現在本身寫不了黃金時代的質感,但是我對黃金時代科幻還蠻有感情的。
奠定我理解推想類小說的創作思路和風格,是本科時候讀到的博爾赫斯。讀了博爾赫斯以後,去搜類似的長篇小說,又讀了《哈扎爾辭典》。直到現在,我沒事還會再去讀一讀博爾赫斯,不管他的評論類文章還是虛構類小說,或是像《惡棍列傳》那種有點拉美英雄主義的寫實風格,我都蠻喜歡的,然後會去讀,因為它本身有一個異世界的質感。
《哈扎爾辭典》可能算某種宗教類的推想小說。它講的不是宗教的神聖性,反而是神秘主義的推想。它把三大一神論宗教,以一個很有意思的方式融合為完整的一本書。這本書是所謂的辭典,按詞條去寫,但詞條之間並非線性邏輯。《哈扎爾辭典》的故事情節有著三層嵌套,也暗示了人物的三種形態。能超越《哈扎爾辭典》寫法的作品很少。《哈扎爾辭典》也算是一類很核心的推想作品。它對於宗教的使用不是現在奇幻小說對於宗教的使用,而真正把一神論宗教敘事中,很本質的一些東西重新建構為作品性的邏輯。像《哈扎爾辭典》這種偏文學類的推想,很難寫。所以比較簡單的入手方式,還是類似於“黃金時代”的創作:先找一個點子,然後從點子文學入手,再考慮怎樣進行結構和文體上的書寫。

作者: (塞爾維亞)米洛拉德·帕維奇,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副標題: 一部十萬個詞語的辭典,譯者: 南山 / 戴驄 / 石枕川
慕明:我很小的時候,最早看到是凡爾納的一套《氣球上的五星期》、《海底兩萬裡》這些,小學的時候看覺得太好玩了,然後當時就覺得這東西都是怎麼寫出來的,超厲害。中學的時候,大概我們就是剛上初中那會兒,正好是《魔戒三部曲》引進國內,然後特別火,大家都瘋狂看了這部。
我當時總是看艾薩克阿西莫夫的《銀河帝國》,《銀河帝國》當時是川科社出的,當時都覺得這東西特別好玩特別喜歡,因為我爸媽都是搞文科的,是那種特別古老的文獻,然後我一直對理科還蠻有興趣的,最後大概是高中就是選專業的時候,也是選的理科,覺得科學的世界特別有意思。我後來是選的人工智能專業,當時是沒有什麼人學人工智能,大家對這東西完全不理解,我們學校當時應該是全國第一個排智能專業的學校,然後我們是第三屆,當時什麼情況,這個專業沒有人去,跟現在不一樣。然後我看了這些科幻小說,我說我要把東西弄明白做好,當然可能當時學現在學完全不是一種東西,但是怎麼說呢?可以說是看科幻小說這件事指導了我選專業了。當時看有一本書叫《人工智能的未來》,其實是一個科普,然後像“第一推動叢書”,然後也看了《GEB》這種書,就覺得這些都特別神奇。
上大學之後學了人工智能,或者說學了理科後,反而更多看主流文學,因為就覺得科幻好像滿足不了我了,看paper更有用,自己也沒有想著寫,最後怎麼寫科幻,大概就2015年、2016年,看到特德姜和劉宇昆的作品,他們的作品就給我感覺,可以把對於這些文學的理解和這些真正的現在比較先進的一些科學的思想結合起來,而且不是很僵硬。之前就覺得好多太過類型化的科幻小說它探討的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科學的思維,或者說比較僵硬,或者比較老派,像阿西莫夫這種東西。我是看了這兩個作者之後才開始開始寫科幻的。
這塊就講一個神奇或者說好玩一點的例子。我之前在可能在CH也講過,就是我大概是2016年開始寫,到2018年的時候就正好就知道了,因為我現在還在紐約,就知道這邊有一個start-up,叫control-lab,他們做什麼呢?他們就做一個神經接口,其實是意念捕捉,可以通過捕捉你的神經信號,他們叫intention capture,就是在你的手做出動作之前就把你的神經衝動捕捉了,之後想幹啥幹啥,可以放到屏幕上做動作的重建,打遊戲什麼都可以,他們想法就是你以後不用鍵盤了,也不用用鼠標了,你就想,甚至連手可以都不要,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demo,好像是車禍有個人就沒有手指了,但是經過他們intention capture之後,給他電腦上操作所有的東西,他很快就學會了怎麼去用神經去操作,當時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然後我就寫了個小說。然後2019年這個公司就被facebook收購了。
科幻小說真的幫助了我的思維方式的形成,可以讓我比別人看得更遠,可以讓我分析技術也好,或者說社會現場的一些內在邏輯,從而做出這種前瞻性的思考。寫作最大的意義,它是對認知的一個提升。
雙翅目:我高中時候也是理科生,喜歡看科幻,因為高考成績,去了哲學院(第一志願報哲學的學生很少)。我到現在還在唸哲學,因為我發現哲學和科幻蠻像。《果殼中的宇宙》中文版2003年出版,出版以前,《科幻世界》登了對霍金的介紹。因為介紹,我去看了《果殼中的宇宙》和《時間簡史》。本科念哲學的時候,我才發現,《時間簡史》的強人擇原理和弱人擇原理,就是哲學概念。科幻當中很多有意思的體驗,在哲學中可以發現。我個人現在的專業方向偏文科,跟偏科幻的寫作能互相幫助。換言之,比較幸運的,我的主業和副業可以結合,而且目前可能接受度比以前高一些。因為本科或研究生時候,我基本上不和周圍同學聊科幻閱讀或者科幻寫作,但近兩年慢慢的我會發現周圍更多的人,對科幻或者對推想性作品感興趣。這是比較有意思的一點,不管是文科的偏理論的方向,還是理科的偏哲學或思想方向,最終融合到一起。像剛才慕明說的,現在很多思想實驗,不管理科層面還是文科層面,都有一致性。
另一方面,從當代視角反觀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不管是《科幻世界》,還是所謂“低幼”的二次元,其實蠻新、蠻前沿。現在的風潮可能不像當年那麼前沿,這讓我有點失望,或者新風潮正在醞釀中,還沒有進入普及階段。這兩年國內人文類期刊關於人工智能或是關於文學未來的討論,很多在上世紀科幻或推想小說中已有過思考。人文領域關於主體間性的研究、共情研究、情緒研究,在很多科幻小說或推想小說中也可以找到。科幻小說、推想小說,或推想類電影和科幻類電影,它們其實參與了現在世界的一些基礎認知構建。這類構建開始被引用、被研究,這是很有意思的一點。
反觀當代的創作,我可能會想,以後的寫作,如何可能慢慢地同體驗或者經驗的構建結合在一起。從最初唸書到現在回顧當年閱讀的東西,其中有些“通俗讀物”反倒被國外或國內的一些學術引用了。這讓我想到狄更斯的情況,蠻有意思的。零幾年的時候,大部分科幻小說的封面都很醜,因為要按照地攤文學的邏輯去銷售。我在《科幻世界》增刊第一次讀《基地》系列,當時會把它認作為一種通俗小說。而現在,基地系列已成為被引用的嚴肅小說。
又比如小時候看宮崎駿,雖然很多內容屬於推想。但早年不管是成年人還是少年兒童,都將宮崎駿作品視為通俗少兒動畫。而如今,吉卜力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它的敘事,它的美術,尤其是它的音樂,在國外是一個研究門類。專門有關於宮崎駿、吉卜力的seminar。在英國時候,我發現吉卜力主題seminar,專門去了。在那裡,牛津劍橋的學者,或是年紀比較大的退休學者聚在一起,每個人都帶著一篇論文,專門討論宮崎駿不同的電影和不同的音樂。大家聊得很開心。這是我在本科時候,不會幻想的氛圍。我希望以後不管是學術還是非學術,這種對於摯愛作品的深度討論多一點。這種氛圍也可能激發大家從不同學科角度出發,進行想象力延展。
一靜:其實我想問問大家或者說具體一點問題,就是說你們在自己的作品裡會比較注重思考什麼樣的問題,或者說你們剛剛提到黃金時代也好,前輩們也好,你們覺得你們這一代的科幻寫作者跟上一代相比會更關心什麼問題?要不從慕明老師開始說。
慕明:我一般寫小說都會有一個技術發展路徑,一個人思考的路徑,還有一個故事路徑,我更多的是想做這個搭橋的工作,像比如我準備出小說集了,《宛轉環》,大家如果看過就知道它是一個莫比烏斯環,它是連通兩個維度這樣的東西。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們現在小說也特別缺的,怎麼去把這些不同的思想體系,不管它是真的假的,是來源於歷史文化傳統,還是來源於文學傳統,還是來源於藝術,還是來源於科學的東西連接起來,覺得小說它就是一種讓人從已知躍升到未知這樣一個存在,不管你是一個理工科背景的讀者,還是一個文學或者說是類型小說讀者,我都希望他能夠在我的作品裡知道一些不同的東西。當然這麼做的壞處就是,好多人一看覺得跟他預期不符,這有些人覺得好,有些人覺得不好,也沒什麼辦法,但是這個是我的一個創作上的追求。
另外一點就是,我覺得我還是受俄羅斯的那一套東西影響比較深。我覺得我比較關心的是像《宗教大法官》裡面寫的,聰明人的良心的問題,在一個大時代,一個變化的時代,在一個充滿機遇的時代,作為一個聰明人,作為一個有能力的人,我的主角一般是建築師、研究者、或者說學者這樣的,我覺得這些人他們在時代下的境遇和命運,他們的選擇特別重要。這東西不光關乎於科學技術的理解。
所以說這塊我特別推薦一下喬治·斯坦納的《語言與沉默》。這本書第一篇《人文素養》講的是,一個作者的寫作,或者說是評論家觀察的選擇,他其實並不是只站在文學這一片土壤上,更多的是站在整個文化或者整個人類的精神土壤上。他也是猶太人,他很多時候是反思文學到底能做什麼。他有一個最有名的段落,就是有些人晚上彈巴赫、讀歌德,早上起來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他覺得怎麼回事,他必須得把事情想清楚,他必須得把小說放在整個大的人類的精神背景之下去考慮這件事情。而對於我們現在來講,我們還得把科學也放在這個背景裡面這個是我想達到的一個地方。
雙翅目:我其實就跟慕明說的情況一樣。我有所謂的問題意識,因為我本身天天或者在看論文,或者在寫論文,我創作的最初動機就是把不能放到學術論文裡的東西,寫成小說。這對於我個人創作的幫助,就是問題性會很清晰,所以寫起來蠻自然的。如果從創作角度來說,比如說今天的聽眾,大家各有各的職業情況,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在自己的職業當中獲得表達,好多自我表達被職業壓抑。在這個情況下,藝術表達是一個出口。我越忙的時候,寫作衝動就越大。我會以小說的方式把我的想法或情緒表達出來。今天的聽眾或者重聽的各位朋友們,可以把各自被壓抑的狀態,或者現在思考的問題寫出來。短篇小說是一個最簡單的起步點,並且它的氛圍性和切身的體驗性會更強。
剛才主持人問到,有沒有新入門推想小說或者新入門作者的平臺。還真不太多。像慕明和我,比較幸運,趕在豆瓣閱讀平臺還有中篇小說體量的發表機會時,發佈了最早的作品。我連續寫了4年,正好有了一本書的體量。從推想小說的角度上來說,如果寫更偏向於科幻類的推想,建議去參加幾個比較重要的比賽,或者投“八光分文化”或《科幻世界》。以短篇為基礎去投稿,這樣慢慢地根據反饋,就會知道自己的狀態。如果偏文學性,不一定要是科幻,現在像《特區文學》、《花城》會接受慕明和我這樣比較新的作者,可以在這樣的語境下去發表。當然,核心還是先有一個寫作的過程。如果是長篇推想類作者,可以嘗試豆瓣閱讀平臺的長篇徵文,或者投“八光分文化”和《科幻世界》。不用很長,10萬字左右就行。長篇體量主要考驗人物之間的關係。
說到剛才主持人的提問,我的創作首先是表達我的問題,然後才去想世界的建構和文字的表達。
我現在的缺點是對人物關係沒有好的把握。現在人物關係寫得好的內容,很多是歐美劇裡。而國產劇寫得比較好的人物關係,大部分披著“封建外衣”,或者用了比較“傳統”的視角。那麼如何用中國的人物去寫一個比較貼近現實的,又跟科幻相結合的現代性的角色,我現在沒有把握好這個問題。可能因為周圍的案例還沒有那麼多,我自己的體驗還不夠。我基本上是一個社會經驗比較少的人。而現在有很多社會經驗很豐富的作者,在網上寫過很長的小說,可以考慮把閱歷和幻想揉一下,以推想類小說的狀態去表達。這類推想類小說是構建性的,不一定是科幻,可能在技術要求上比科幻的門檻低,而對於社會性和人性理解的要求更高,這樣可能會出現另外一批更擅長寫推想作品的作者。其實國外有很多例子,說一個比較特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其實有點類似於公案小說,他的《罪與罰》就算是某種意義上的懸疑破案小說。類型化的東西是一個類型,其下的文學性表達可以很豐富。所以,即使是以一個類型的思路去創作,也可以融進去很多東西,而不被類型框住。這是我覺得創作者可以打開思路的一個方式。我現在也想嘗試去閱讀更多的經典作品,這樣會打開我的思路和視野。
慕明:我就補充幾個比較短平快的東西,因為剛才雙翅目已經講了去看書或者說是平臺這些。其實現在主流文學平臺對咱們還是有一些支持,像我的話,我看徐晨亮老師也在這,之前徐晨亮老師主持《中華文學選刊》是發了一些科幻作品,包括我的《鑄夢》上到收穫文學排行榜,也是徐老師推的,我覺得這還是有人在幫咱們,也不用特別悲觀,包括像《花城》,像《特區文學》,這些編輯咱們也都漸漸認識了。就是如果真的你覺得自己寫的小說想發的話,就是你可以加我們,我們去幫你,推給這些編輯。當然前提還是你自己有一個比較新或者說是完成度比較高的作品。
我接下來就說兩個東西,一個是資源。寫作上面,如果你真的想開始寫的話,我覺得最好的東西就是masterclass,就是《大師課》系列。一個是《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講創意寫作》,還有尼爾蓋曼《講故事的藝術》,這兩個片子應該在B站上都是可以看的,因為我覺得,教寫作這事兒其實市面上書特別特別多。那這兩個人,首先他倆是非常著名的作家,又是暢銷作品,而且是批評家也很看重的推想小說作者,作品也很過硬,如果你能喜歡他的作品更好。
第二個他更多的是講道,而不是講術。對於推想,你的想象力從哪裡來?這是尼爾蓋曼特別愛說的一句話,我也特別愛研究。尼爾蓋曼說啥呢?尼爾蓋曼說,想象力是肌肉,不練就沒,就萎縮。這就解決很多人的問題。很多人說,哎呀我想不出來故事怎麼辦?那尼爾蓋曼就說,你要練。就跟你剛開始不能跑5千米,你就從800米開始跑,對吧?跑著跑著你就會發現自己到5千米了,這就是練習。
然後也像是我剛才說的,類型可以靠比賽快速建立自己的特色,但是如果你要長期發展的話,還是要注重跟編輯的交流,跟你的讀者的交流,因為寫作它本身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就是你可以把寫作理解成一個開創業公司這樣的過程,不單是悶頭寫。
作者是個很綜合的素質。當然我也沒寫多少年,就5年,這個是我5年的想法。你要寫的好,就相當於是工程師,或者說是技術員。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產品得過硬,你這個東西想解決市面上有什麼問題,或者說解決整個人文環境下的什麼問題,這個是產品項目經理的事情。那怎麼把你的東西賣出去,這個是市場營銷的事情。那怎麼處理這些用戶評論,這個是PR終端的事情。
寫作,我們要有這種一個人是一隻隊伍的感覺,我也看到好多作者他就是悶頭寫的,也沒有發表渠道,可能這種人他反而堅持不了太久。這方面我覺得就可能是你剛開始的時候感覺不到,其實也不太重要,但是如果你已經寫了一段了,然後覺得沒有人認識自己,或者說發不出去,或者說是有這些困惑在阻撓你寫作的話,我覺得還是要有這種創業的精神。
【本期提到的書籍、影片】
中國文學:《三體》《左傳》《公雞王子》《宛轉環》《沙與星》《鑄劍》《朝聞道》《詭秘之主》《殺破狼》《殘次品》《小行星掉在下午》《夜晚的潛水艇》
外國文學:《弗蘭肯斯坦》《莫洛博士島》《格列佛遊記》《使女的故事》《1984》《荷馬史詩》《在其他的世界》《變化的位面》《黑暗的左手》《太古和其他的時間》《我這樣的機器》《玻璃球遊戲》《浮士德博士》《夢遊人》《冰與火之歌》《從地球到月球》《地心遊記》《哈扎爾詞典》《惡棍列傳》《氣球上的星期五》《海底兩萬裡》《銀河帝國》《機器人大師》《銀河系漫遊指南》《山月記》《卡拉馬佐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
科學史著作:
《科學革命的結構》
電影:
《信條》《魔戒三部曲》《降臨》《三體》
學術、科普著作:
《批評的解剖》《語言與沉默》《千面英雄》《人工智能的未來》《GEB——一條永恆的金帶》《果殼中的宇宙》《時間簡史》
雜誌:
《中華文學選刊》《收穫》《花城》《特區文學》《科幻世界》
寫作課程: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講創意寫作》《講故事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