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兩位俄羅斯大宅子製作的,以美少女戀愛題材的恐怖遊戲《米塔》在全網爆火。一方面是哥倆兒聖誕檔前後上線,把“Santa”寫成了“Satan”的國際烏龍,另一方面是女主角米塔的人物塑造與遊戲流程中飽滿的戲劇矛盾,吸引了眾多被《心跳文學部》帶起的同類題材遊戲粉絲,直接一躍成為年底最大黑馬,黑猴和小機器人之間沒完沒了的撕逼,最後也沉沒於藍色百褶裙與紅色絲襪之間,略帶肉感的“絕對領域”之中。

我最近也用了不到4小時的時間通關了一週目,結合最近爆火的一本“御宅學”讀本——《00年代的想象力》,從敘事角度聊聊《米塔》的愛。文章裡會涉及超大量劇透內容,介意的玩家朋友自行選擇閱讀。本文的人物分析不涉及所謂的各種陰謀論等分析推斷,即從敘事文本角度出發,剖析人物形象的特點。
《米塔》有多優秀
《米塔》講述的故事其實很簡單,主角“我”作為一個被優化的程序員,過著遠離社交的家裡蹲生活,把自己關在家裡,每天只吃杯麵,玩玩電腦,假裝自己還活著。某一天,好友給自己發過來個名叫“米塔”的app,是一款戀愛模擬的手遊,模擬與名叫“米塔”的女主角的生活。
快餐化的虛假甜蜜讓主角迅速沉迷。與此同時,恐怖的是“米塔”似乎也沉迷於主角“我”給予的溫柔,屏幕裡的二頭身形象少女向主角發出了詭異的邀請,隨即米塔和他的房間便出現在了你的眼前。但米塔的願望不僅僅是為了見到自己最熟悉的陌生人,背後還有更加恐怖的目的,一場恐懼的賽博世界大逃亡也隨即開始。

大體上來說,《米塔》就是一部病嬌與AI失控兩個題材雜交而成的逃生系恐怖遊戲。遊戲的內容這樣聽起來有些平庸和普通,但從銷量和眾多好評也確實證明了《米塔》絕對有它的獨到之處。一方面是這二位俄羅斯製作人根正苗紅的二次元氣質,哥倆兒歷經三年時間,手搓出了這部作品,據說有數個月的精力都放在打磨主角米塔的建模上了。二人的努力並非無用功,3D體模的比例極其完美,與2D渲染的適配性也極高,完全不存在“偽人化”的詭異感。
得意於此,甚至讓幾次瘋狂米塔的“跳臉殺”,都不覺得有多驚嚇。而且米塔整體的人設簡單利落,服裝也沒有刻意的繁複設計,二位老哥還把深藍與深紅的撞色搭配調整得很適當,讓米塔整體的形象還帶著些復古與成熟的美感,大有成為2025年新進“waifu”有力競爭者的實力。

而在劇情上,二位製作人創造出一體多面的眾多“米塔”們,在性格、語言和故事上也都各有千秋。想佔有控制玩家的瘋狂米塔,幫助主角的賢內助善良米塔,性格古靈精怪的帽子米塔,讓眾多玩家難忘的米拉,文字avg世界的平面米塔等等的一系列形象和她們的故事線,被製作人巧妙地融入到了短短4-6小時的劇情中,強烈的戲劇矛盾在極短的時間中爆發,給第一人稱視角體驗的玩家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而且從山岸由花子開始,到我妻由乃爆火,病嬌女主這個設定就飽受大宅子們愛戴,悉心照顧你的真二次元病嬌女友,我相信應該不少人能深陷其中,甚至有人直接揚言:“一個有老婆和互聯網,不愁吃穿,誰還沒事想出門啊。”
臃腫之愛的魅力
那為何充滿傷害性的“病嬌之愛”如此有魅力呢?甚至成為了一種“萌”屬性備受討論。而在御宅文化被廣泛討論和認知的今天,病嬌這種扭曲化表達愛情的形式竟然沒有被批判性的反對,而是受到了全世界範圍的推廣。2017年發行由美國人制作的,大火的視覺小說《心跳文學社》拿下了全世界百萬的銷量,將病嬌女主與臃腫之愛正式帶到了亞洲以外的亞文化世界。今天《米塔》的爆火,則也是對《心跳文學社》的延續,但無可厚非,“病嬌”這一主題已經足夠吸引人了。

心跳文學社 全家福
在最近大火的文學批評類書籍《00年代的想象力》中,作者宇野常寬提出了“母性敵託邦”這一概念,他以高橋留美子的《福星小子》中的拉姆和富野悠遊紀的《高達》系列中的拉拉為例,廣泛的討論作品中女性角色膨脹的力量。其中的後者——夏亞與阿姆羅一生糾葛的起因——少女拉拉·辛,是包含母性溫和的一面,同時不斷地向外擴散,從而影響感懷著周遭與其發生著交互的生命,最後用自己的生命,帶給兩位“少年”以成熟的最關鍵一課,這是母性敵託邦中溫柔的一面。

左:《福星小子》拉姆 右:《機動戰士高達》 拉拉·辛
而前者——神秘外星少女拉姆——則象徵著母性敵託邦瘋狂蓬勃的慾望,作為當代戀愛喜劇鼻祖級的作品,《福星小子》完善了戀愛幻想樂園般得世界,這裡隔絕了外界一切的客觀因素,甚至隔絕了時間。但在押井守作為監督製作的劇場版《綺麗門中人》中,對這樣夢幻異世界做出了超前的批判。反派夢邪鬼認可了拉姆,為了實現她的願望“永遠和朋友們過著愉快的校園生活”,將她的情敵們一一消滅,化為了夢境世界中的祭品。
押井守想揭示的既是高橋留美子作品背後“母性的暴力”。乍一看,《福星小子》中的世界是沒有缺憾與父權壓抑的烏托邦,但取而代之的則是將內外完全隔絕開的母性佔有暴力,在這裡排除敵人、做成祭品,把夥伴納入名為“後宮”的“子宮”,永遠不許逃離、不許背叛,這種虛幻幻想的反烏托邦共同體既是“母性敵託邦”。
在《福星小子》之後的作品《相聚一刻》中,高橋留美子巧妙地將這份母性的暴力溫柔處理,而同時也進一步強化,故事結尾男主角五代選擇與女主角公寓管理員音無響子結婚,永遠的生活在“一刻館”之中,使得本應該作為主角五代裕作“gap year”的過渡性象徵的公寓“一刻館”,成為了他永遠留在其中的“子宮監獄”。雖然後續的《亂馬》通過性別流轉,以及《犬夜叉》通過戈薇對桔梗世界的反抗,否定了曾經作品中“母性敵託邦”的強制存在,但《福星小子》2024年的重製以及後宮系男性向作品的泛濫,也確實說明了“母性敵託邦”是成功的創作樣本。

漫畫家 高橋留美子
那既然“母性敵託邦”是對母性力量的展現,那是否是具有超前性的女性權力討論呢?顯然答案肯定是“否”,而且這無非是對男性沙文主義的另一次強化。男性不再只有成為“父”,或者比“父”更具備權威性的“父”,而是可以選擇回到子宮,在母性帶來的安全中,不承受責任帶來的痛苦,幸福的繼續生存在重複的日常裡。
在《EVA》中,教導真嗣、陪伴真嗣的人並不是對其給予厚望的碇司令,反而是讓真嗣借住在自己家的葛城美里。同時初號機本身也是真嗣親生母親的具象化存在,真嗣逃避關於戰鬥的思考而是連攜度意外超標,與LCL融為一體,更是從父權社會逃避,迴歸母體子宮的最具象化表現。可以說“母性敵託邦”帶給了男性受眾逃避的合理性,力量穩定的“母性敵託邦”就是男性受眾完美的幻想樂園,這也就是為什麼“日系後宮”的敘事系統一直存在,並飽受追捧的原因。

圍繞真嗣的父權與母權 碇源堂與葛城美里
話說回來,這些和病嬌與米塔有什麼關係呢?當“母性敵託邦”力量失控,或者說是越界的那一刻起,病嬌的敘事系統便誕生了。病嬌系的女性角色往往會圍繞一名處於絕對弱勢的男性角色展開,這些男性角色往往會被冠以“不起眼”、“不合群”、“沉默寡言”等等否定性質的標籤,同時“溫柔”也決定會是對他們的承認。而在此之前,與這類男性角色同框出現的大多是因為自帶的標籤,而更為弱勢的女性,她們往往存在諸如疾病、殘缺、原生家庭問題等等的“原罪”,以絕對下位者的姿態等待尋求“彌賽亞”般的拯救。
但當“暴力”與“佔有慾”成為了該敘事系統中的“原罪”,也就是將“母性敵託邦”中氾濫的母性力量融入其中是,創作者發現這樣的敘事系統依舊成立。於是,這樣就誕生了“因為我的溫柔而感動了暴力的她”,“我只要滿足了她的佔有我便安全”,諸如此類的敘事幻想。因此,病嬌的敘事系統也就成立了。

21世紀病嬌敘事想象力啟發者 《未來日記》
而這樣的敘事系統則更進一步強化了男性沙文主義的力量,即便不存在“性張力”的男性,不但可以吸引處於弱勢的異性,也能吸引反而處於更強勢的異性,雖然我需要付出“某些自由”。這裡的“某些自由”更應該稱為一個閾值,因角色的特質而異。當男性角色的某些突破該閾值之後,病嬌系的角色就會開始進行對其他個體角色的傷害性行為。可能是對其他異性角色的傷害,懷疑與所佔有的男性角色有染;也可能是對所佔有的男性角色傷害,施加恐懼來增強誇張佔有慾的展現;也可能是對其他角色的傷害,通過非邏輯性的施暴增強非可控性帶來的恐懼。
如果被傷害的是“自己”,即使如同《日在校園》中的伊藤誠,他的死也將他從悲劇始作俑者的位置上拉到了受害者的位置上,罪人卻成為了被辜負的女性。如果被傷害的是其他人,那主角更可以在子宮般的安全庇護中“反省”。所以無論被傷害的對象是誰,所佔有的男性角色,以及帶有所佔有的男性角色的受眾群體,均是在“安全卻痛苦”的狀態下得以心安理得。

《日在校園》男主角 伊藤誠
把話題拉回《米塔》上來,邪惡米塔的閾值是純粹的佔有,製作人同時也將“佔有”提純,將舞臺設定在了逃避討論“忠貞”這一議題的虛擬世界裡,將邪惡米塔的行為進一步的恐懼化。但其行為則很大程度上背離了病嬌敘事系統的準則,試圖將主角“我”變成卡帶,同時也以此方法對其他的主角行兇,這一與“愛”完全不相關的行為動機,引起了玩家關於邪惡米塔起初的表現是“愛的表達”還是“單純玩弄”的考慮,我覺得這也就是為什麼有國外網友說邪惡米塔不是病嬌女主,而是徹頭徹尾的惡魔。

露出獠牙的米塔
但她對其他米塔的殺戮,則反而是母性暴力的最直接表現,當排除異己的驅動力膨脹到極限時,甚至可以殺掉往昔自我的存在。同時其他米塔被殺掉後系統化的復活且重製,則更是“母性敵託邦”中男性角色可以“安全卻痛苦”的存貨的完美展現。由此,不管《米塔》的主角是否是病嬌,但依舊改變不了這部作品中所展現的“母性敵託邦”中佔有慾的可怕力量,那麼《米塔》對“母性敵託邦”的探討是否到位呢?
《米塔》的超越性?
BB姬最近的文章裡,有一篇就是寫《米塔》敘事文本的,這位編輯老師稱《米塔》的故事具有俄羅斯文學的悲劇性。且不提大量的論述逾越了《米塔》遊戲的本身,把血腥化暴力恐懼成為瘋狂的悲劇,這本身就是錯位的解讀。其他的暫時先不談,那我先說個我的結論吧,《米塔》畢竟是兩位製作人僅花費了兩年製作出來的遊戲,劇本上很難說存在超越性,很多劇情部分的討論淺嘗輒止,甚至讓我萌生了寸止的痛苦。
先看看遊戲的標題——《米塔 MiSide》,女主角的名字米塔後面跟了個“MiSide”。這個說法可以追溯到磁帶,A面B面如果用英文講就是“A Side”和“B Side”,這種說法在當今得到了一種延伸,年輕人往往會把展現給外界的一面稱為自己的“A Side”,而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或者一些看起來和外表形象不太相符的特質愛好,就都被稱為“B Side”。而“MiSide”一面指米塔並不只是遊戲裡的二頭身小人,也是有自己獨立人格思想的個體;另一方面,“Mi”在這裡可能也源於“Mille”或“Million”,指遊戲裡千人千面、各具特色的米塔們。各色的米塔們,也是這遊戲劇情中最大的賣點之一。

但如果仔細來看,其實遊戲中米塔們的差異更多也只停留在設定上,能輕鬆的以二元化的視角劃分立場歸類,這很難稱得上真正的千人千面,幸虧得益於世界觀層面設定的成功,不然估計還得被冠上個“省建模”的帽子。甚至即使是拋開二元化的立場劃分不談,每個米塔的人設也很難稱得上存在超越性的優秀,更多隻是傳統御宅文化作品中常規登場角色譜系的簡單嵌套罷了。
“善良米塔”是值得信任的可靠同伴,同時也是機械降神般全知全能的存在。“邪惡米塔”是標準的、有苦衷的,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要毀滅世界的的大反派。諸如“帽子米塔”、“醜陋米塔”、“二維米塔”等等,也不過是很標準的冒險題材作品裡常見的正派或者反派角色。即使是在遊戲上線後,備受玩家喜愛的“米拉”,其實角色塑造也很傳統。

“米拉”雖然嚮往遊戲之外的世界,也試圖通過學習瞭解更多的世界,但她從來沒有否定過自己的存在與自己生活的世界,也都沒有認識主觀能動性的嘗試。反而依舊如同長髮公主一般,生活在化作亭臺樓閣的監獄,等著叛逆者形象的少年拯救。“米拉”僅在主角“我”試圖離開並且嘗試成功後提出,是否可以去到更外面的世界。而面臨冒險未知的危險時,米拉卻對主角“我”做出了挽留的行為,這種行為在眾多作品中均有所呈現,往往是母親或者是妻子,這樣作為最成熟母性化身的角色,在主角最終決戰臨行前的挽留,是母性力量與父權力量最直接的碰撞,當然最後不論主角的結局,母性力量在這裡永遠是落敗的。主角必定出發,主角也必須勝利。

米拉最後的結局則是被邪惡米塔殺死重製,主角“我”可能生存的最後的母性安全世界也破碎了,剩下只有逃跑或者抗爭。這樣的戰鬥理由,也是不具備超越性的另一特點,文章之前提到:母性敵託邦也是對男性沙文主義敘事服務的。《米塔》也是,主角“我”逃離遊戲世界的理由是需要用自由換取愛情與幸福,而不是在地牢裡到被關起來的善良米塔,意識到有人需要拯救,意識到世界背後存在的巨大陰謀,而是母性力量膨脹到開始侵佔主角“我”的存在,這種被動化的行為很難被稱為覺悟或者成長,本質也是另一種逃避。而逃亡過程中的其他米塔,不是認可主角“我”被動的成長,就是等待著成長後的主角“我”拯救的公主。

如果說其他米塔都是配角,即使是邪惡米塔,也是個在尋找超越性的半路就殞命的角色。在遊戲中這樣的表達有兩處:一處是試圖摧毀主角“我”的意志,通過日常而反覆的生活展開的討論;一處則是最後邪惡米塔以遊戲角色身份,對身為玩家的主角“我”的審判,這兩處我們分開來聊一聊。

在快接近遊戲結尾的地方,邪惡米塔有一段試圖說服主角“我”同她一起在遊戲世界生活,而她說服我的理由,即是作為一名被優化的御宅族程序員,如今每天的生活只是反覆經歷相同的孤獨日常,與其這樣度日,不如和米塔一起在遊戲的世界中度過。初次體驗這部分的時候,我以為製作人想把整個“米塔app”詮釋為家裡蹲生活中幻想的監牢與主角走不出的房間,而邪惡米塔則是主角逃避社交行為的擬人化表達,在安全世界享受過久虛假的平靜之後,逃避帶來的怠惰開始侵蝕迴歸社會與職場的願望。
在遊戲一開始的部分,也有主角望向電腦桌上方,與之前同事的合影,並且臺詞中暗示仍然懷念此前一起工作的時光。將這一切聯繫起來,我甚至認為,製作人把遊戲逃脫的部分作為主角離職後抑鬱而產生的幻想,想要逃避的慾望讓主角試圖選擇一個不再和任何“人”產生交集的虛擬世界,希望永遠的活在其中。試圖與生活交戰,並且獲得勝利,選擇以自己的方式在日常中自洽的生活,這既是當代作品敘事中的超越性。
我們不在需要青春傷痛文學裡為了作而作帶來的存在認同,也不再相信廢萌動畫裡無限延長的日常有多麼美好,只需要一個信念——一個認清生活既是平坦,但需要掙扎與對抗,而絕對不能逃避所有的掙扎與對抗的信念——這份信念也是岡崎京子在漫畫《我很好》中提到的“平坦的戰場”。但顯然《米塔》的討論並沒有到達這一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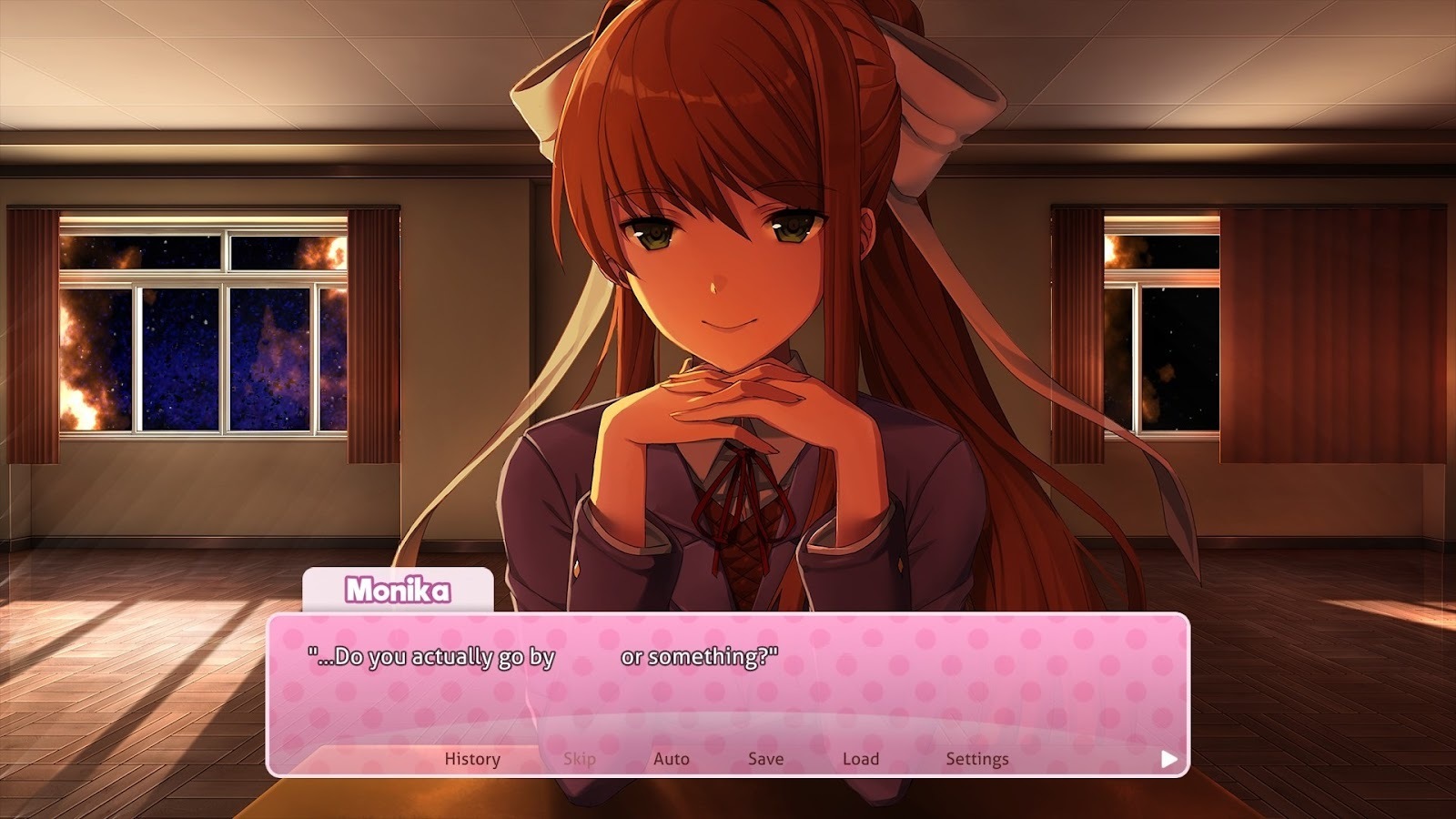
而對於遊戲與現實的討論,邪惡米塔在故事結尾沒有被展開的控訴,遠沒有前輩《心跳文學社》中莫妮卡打破第四面牆,meta化的演出敘事來得有衝擊力和說服力。當遊戲中的角色如同ai一樣獲得了自我意識,開始真正愛上了與她交互的主角,甚至是背後的你和我,莫妮卡選擇直接穿過屏幕和你我交流,並企圖將你我綁架,送上貞節牌坊下的斷頭臺,或者就像遊戲裡說的那樣,在U盤裡下載莫妮卡的拷貝,真真正正的讓莫妮卡陪在你的身邊。
莫妮卡的控訴與提出的結局方案是真正帶有審判的超越性,用打破第四面牆的形式諷刺著“SL大法”,這徹底的否定了男性向視覺小說中毫無意義的自我批判,把遊戲裡的男性沙文主義送上了斷頭臺。這是對《心跳文學社》開創討論的肯定。

但在《米塔》中,可能是製作人的柔軟,邪惡米塔最後控訴的對象是不明確的,不明確是遊戲內的主角“我”,還是遊戲外的玩家“我”,文藝作品中再有力的審判與控訴,面對習慣客體性審視作品的來說都是不成立的,不成立的控訴那莫過於抱怨吧。而話語的內容則是批判遊戲這一系統迭代時角色消亡的現實,而這一話題,即使是對於主角“我”來說也是客體化的事件,既無法帶入遊戲世界的創造者,也很難帶入被迭代的角色,畢竟遊戲一路走來看到所有米塔也是往日的存在,這就讓這段文本徹底喪失了控訴與審判的力度,淪為邪惡米塔單純的抱怨,而主角“我”成為了“闖入林中小屋”般的受害者。
最後,總體上來說,《米塔》的體量絕對是對得起50多元的價格的,即使是作為走路模擬器,手感也很優秀,再加上米塔的人物模型製作實在是太成功了,不妨過年當個小品級別的遊戲體驗下,拋開整篇文章的討論不談,這二位製作人,可太懂二次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