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論文標題為:Artefacts from tomorrow: Future dilemmas of the parahistorian,介紹了超歷史學家研究超歷史人工製品所面臨的困境,可以對“超歷史學”這一當今尚且存在於科學範疇之外的學科有概括性的瞭解。其中數字註解為論文作者所注,字母註解為筆(譯)者所著。本文為科普而非學術,為表述的簡明,對正文中引用內容出處的註解進行了刪除,如有興趣可以查看原文進一步瞭解。譯者非專業人士,如有錯譯還請理解和批評指正。
來自明天的文物:超歷史學家的未來困境
2022
Alasdair Richmond
英國 愛丁堡大學 哲學、心理學與語言科學學院
摘要
1987年,羅伊·索倫森(Roy Sorensen)創造了超歷史(parahistory)一詞,用於指代通過時間旅行所獲得證據的假設性研究。因此,與其說“超歷史”是“歷史”,不如說是“心理學”;其研究不被正統科學認可的方式獲得的數據(比如人工製品),本文中指未來衍生的超歷史人工製品。由於過去和未來的不對稱性,在校準未來物品的週期、確定未來人工製品的年齡、以及將其與因果循環隔離等方面都面臨著無法解決的問題。換而言之,因果循環的對象在理想情況下,必定不可能是非任意斷代的;而在最差情況下,甚至不可能是人工製品。即使存在從未來旅行到今天的證據,任何訴諸未來人工製品的此類證據都面臨著廣泛存在的困難,且極不可能令人信服。
關鍵詞:大衛·羅伊斯 證據 羅伊·索倫森 時間旅行
1 時間旅行
關於時間旅行的邏輯問題、形而上學問題和物理學問題的討論比比皆是。而關於時間旅行證據問題的討論則較為少見。里士滿認為,來自過去的超歷史人工製品證據,作為對時間旅行的言辭或預測性證據的補充,要麼在相互矛盾的指標衝擊下瓦解,要麼塌縮為言辭證據。本文認為,未來的人工製品比過去的人工製品有更嚴重的證據問題。任何僅基於未來人工製品的時間旅行證據都將面臨如此普遍的問題,因此不太可能令人信服。
時間旅行的最好定義來自於劉易斯:
“時間旅行”不可避免地涉及時間與時間之間的差異。一個旅行者出發,然後抵達他的目的地;從出發到抵達(為正,也可能為零)所用的時間即為行程時間。但如果他是時間旅行者,那麼出發和到達之間的時間間隔並不等於旅程的持續時間。
劉易斯區分了“個人時間”和“外部時間”:分別是在旅行者參照系中登記的時間和整體世界(或其中包含的合適子集)登記的時間。個人時間是對旅行者階段進行分類的最顯著方式,因此(例如)旅行者具有自洽的年齡,並能正確地積累記憶痕跡。個人的時間不一定是心理學或現象學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劉易斯的命名具有誤導性。更先進的是麥克貝思的“特定時間”(即特定於旅行對象的時間),它很好地強調了非個人系統也有自己的關聯時間。但是“個人時間”是固定的,因此請記住,“個人時間”對於無生命的物體來說,並沒有聽起來那麼矛盾。與旅行者一起旅行的任何事物都必然與旅行者的個人時間共享時長。與其他旅行一樣,時間旅行要求旅行者在整個旅程中具有連續的因果歷史:如果X和Y不是因果連續的,那麼他們就不會是同一個旅行者的一部分,不管它們有多麼相似。
劉易斯時間旅行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個人時間與外部時間的差異。這些差異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產生,分別對應前向和逆向的時間旅行。在前向時間旅行中,外部持續時間超過個人持續時間,例如,如果一個人花費5分鐘從2022年到2516年的時間旅行。而在逆向時間旅行中,個人持續時間超過外部持續時間。劉易斯只討論了個人時間為正的情況,但允許外部時間為負[1]。逆向時間旅行包括到達在個人出發之後,但在外部出發之前的情況,例如花費5分鐘從2022年到1516年的旅行。無論是前向還是逆向,真正的時間旅行應該在外部時間和個人時間過程之間產生差異,而這些差異在功能上與旅行者的持續條件和一致性條件有關
[2]。
劉易斯聲稱,無論前向還是逆向的時間旅行,即使在一條歷史線中也可能發生——只要旅行者目的地的所有事件與出發點的事件在數值上一致(單說一致性邏輯就能暗示這一點——在劉易斯的體系中,產生旅行者的過去與旅行者到達的過去在數值上是相同的。如果劉易斯是正確的,要使時間旅行具有邏輯意義,多重歷史(或多維時間)就並非必要。不僅如此,劉易斯還懷疑不同歷史之間的旅行並不是真正的時間旅行。本文只討論劉易斯時間旅行,因此出發和到達屬於同一個歷史。劉易斯的主要目的是停止論證時間旅行的邏輯可能性;他的論證並不意味著對時間旅行的物理可能性或經驗合理性作任何承諾。劉易斯暗示,僅僅訴諸一致性並不能解決時間旅行的現狀。人們或許接受了時間旅行的邏輯可能性,但仍然認為(形而上學的、物理的或認識層面的)其他考慮嚴重違背了時間旅行的證據合理性。事實上,劉易斯認為時間旅行的世界可能與我們認為所居住的世界明顯不同。我們或許可以接受劉易斯對時間旅行的傳統邏輯異議的消解,即認為可能存在可以吹噓時間旅行者的世界,但不會在法理上認為,時間旅行世界可以從我們眼中的這個世界獲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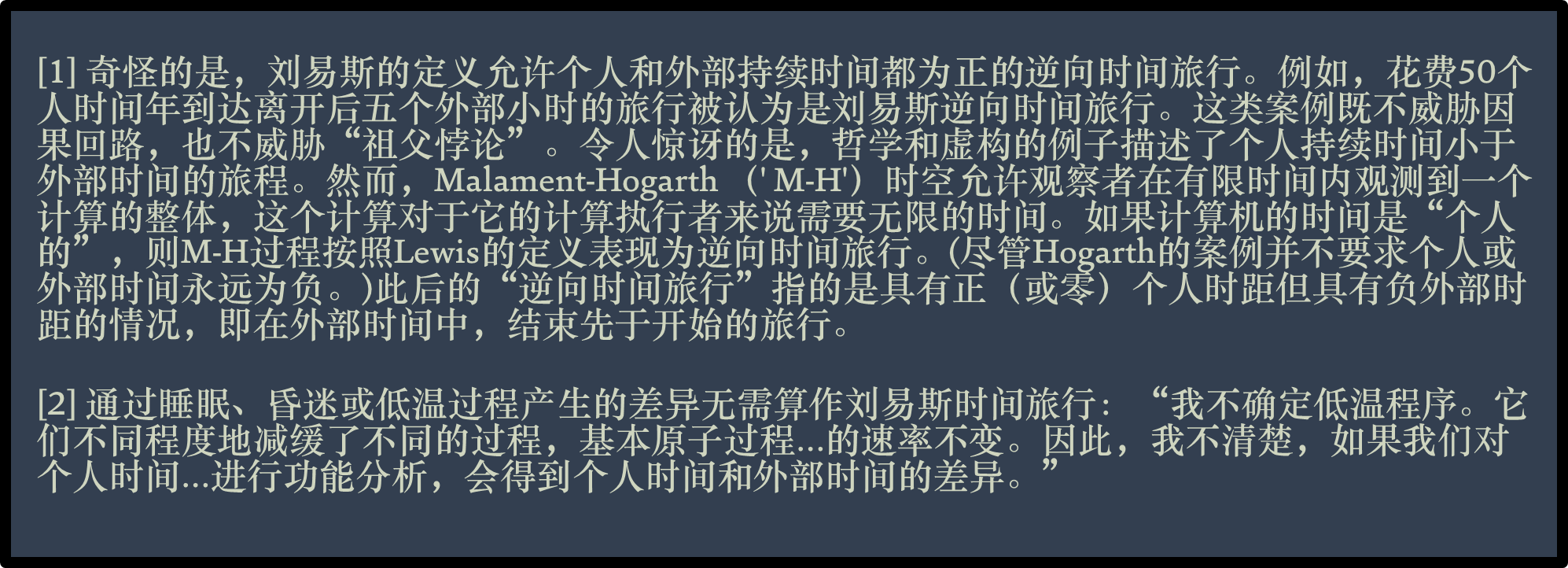
2 過去和未來的超歷史
索倫森創造了“超歷史”一詞,意思是對“…時光旅行者提供的各種故事、器物和其他雜記”的假設性研究。因此,超歷史的文物是來自過去或未來的物體,它們在起源上約定俗成,但通過時間旅行到達此時此地。(這裡不考慮從其他歷史/平行世界等中提取的人工製品——部分是因為劉易斯的單世界模型被廣泛引用和內在合理,也因為其他世界/歷史中的人工製品在指定日期和起源方面存在自己的特徵問題。) 超歷史人工製品只需要單向地穿越時間:過去的人工製品向前;未來的人工製品向後。然而,收集這類人工製品的當代超歷史學家,在收集過去的人工製品時,必須進行“後退”和“前進”的雙向時間旅行;在收集未來的人工製品時,則先向前再向後。假定超歷史學家能到達現在,並提供檢索到的人工製品作為證據,就可以支持存在時間旅行的宣稱。
超歷史證據必須區分人工製品的“時期指標”和“年齡指標”:前者反映人工製品的起源時間,後者反映人工製品自產生以來的登記時間。為獲得相對準確的近似值,時期指標追蹤外部時間,年齡指標追蹤個人時間。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時間旅行的物體應該在時間指標和年齡指標之間表現出*集體*差異,就像他們在外部時間和個人時間之間應該表現出的集體差異一樣。設想通過與已知起源的其他雙耳瓶[A]比較(時期指標)或通過碳年齡測定法(年齡指標)來確定新修復的經典雙耳瓶的年齡。非超歷史物體的年齡指標和時期指標一般會重合,儘管在不存在時間旅行的情況下,也可能會出現年齡/時期的差異。例如,一幅2022年的康斯博羅[B]畫布,相對於年齡指標(例如花粉痕跡、大氣汙染物等),應該顯示一致但誤導性“老”的時期指標(例如,筆觸、顏料等)。或者,一個暴露在異常數量中子的物體可能顯示出比其時期指標更多的碳-14,因此似乎會被誤導為“老化[3]”。過去的超歷史人工製品應該顯示比它們的年齡指標更“老”的時期指標。一個1766年製造,但在10分鐘內運送到2022年的齊彭代爾[C]櫥櫃,其年齡指標滯後於時期指標256年。
與所有路易斯的旅行者一樣,未來衍生的超歷史人工製品應該具有確定的*個人*年齡[4],包括人工製品在未來被收集時的年齡、旅行到現在所花費的所有個人時間、以及隨後在現在所消耗的任何時間。然而,這些文物必須在其(外部)時間之前到達,即具有負的外部年齡(一個從2266年運輸到2022年的物體,在外部時間裡是*負*244歲)。過去衍生的超歷史人工製品的時期指標可以與傳統的年齡指標,即持續到現在的指標進行核對。人們可以將1766年,超歷史時間運輸的衣櫥的時期指標,與其留存於世、正常年齡的同代物進行比較,但不可能對2266年製造的衣櫥的時期指標進行這樣的因果常態檢查。我們只能猜測未來被徵用人工製品的最初時期指標,收集關於未來時期指標的額外數據存在(其中更多的是)因果循環問題。當代專家在區分十八世紀和二十世紀傢俱時,可以調用許多不同的能指,但如果要求區分二十五世紀和二十二世紀傢俱,則可能會茫然無措。校準和按時間順序排列尚未實現的設計業和製造業趨勢似乎是一個艱鉅的任務。未來的人工製品只能直接與其他未來人工製品進行比較,或者與未來衍生的數據進行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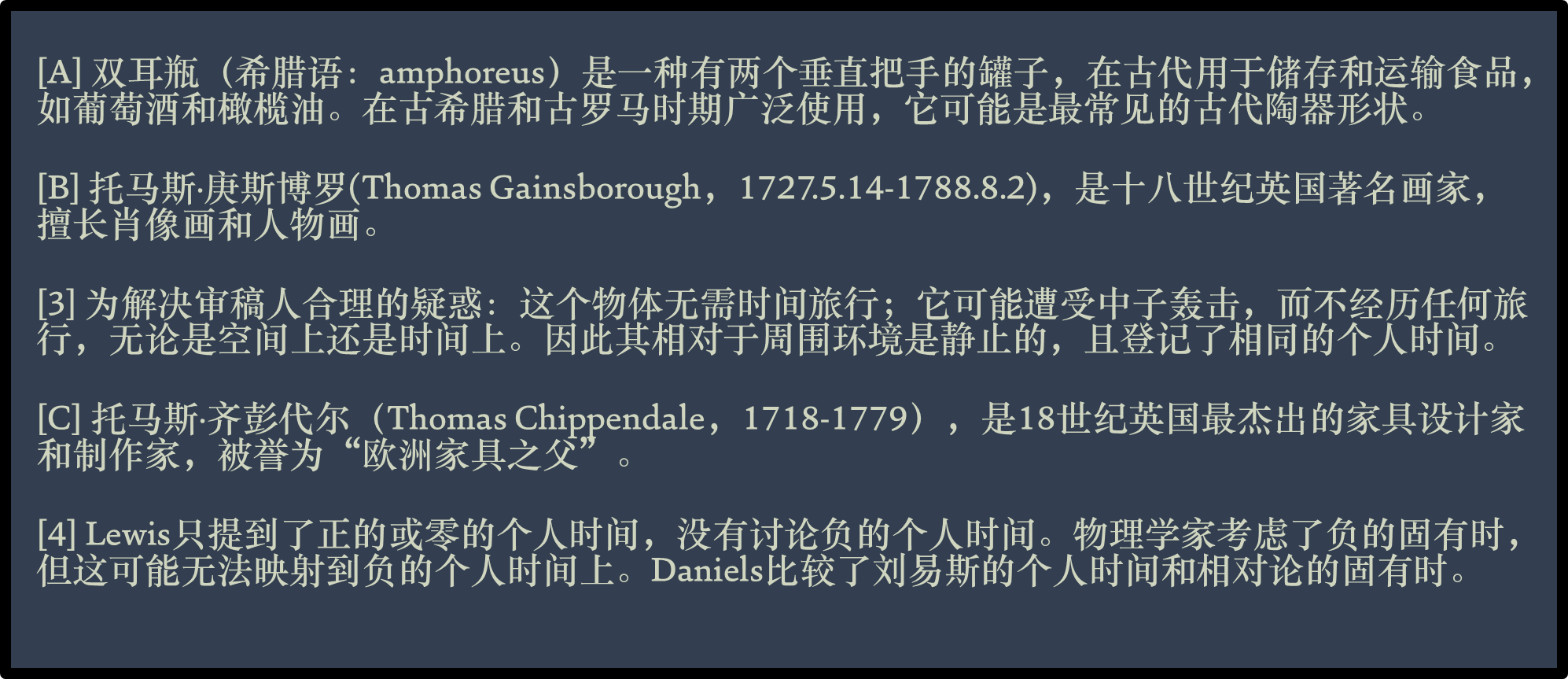
3 觀察超歷史:“時間範圍”問題
想象超歷史學家可以在一個“時間範圍”內補充人工製品數據,這個“時間範圍”允許直接觀察其他時間。即便能直接觀察未來,對超歷史學家似乎也沒什麼幫助,至少最初是這樣,因為任何未來可視的時間範圍都必須首先根據那些尚未被常規觀察到的事件來校準。與過去“超歷史”的不對稱性正在顯現:葛底斯堡演說的1863年原版圖像可以與當代目擊證人證詞、書面記錄、照片等進行核對,而無需用它們校準過去可視的時間範圍。然而,校準一個未來可視的時間範圍卻很困難,因為不可能對未來進行*非超歷史*的觀察,也不可能從中提取人工製品。過去的超歷史可以作為研究過去的其他手段補充;未來的超歷史似乎是自行存在且未經證實的。人工製品和時間跨度的數據可能相互支撐,但不能與常規數據進行綜合或單獨的檢查。在這一點上,未來超歷史學家比過去超歷史學家,以及超心理學家處於更糟糕的境地——任何人都會聲稱後者所做的(例如)遠程觀察或遠程感應,至少可以通過傳統因果渠道進行檢查。此外,校準一個未來可視的時間範圍存在因果循環問題(見下文),例如,假設未來衍生的圖像有助於引發未來事件被觀測。
超歷史學家能否相信未來的技術會被如此認識[5]?想象一下向1840年的阿達·洛芙萊斯[D]演示當代的計算機。雖然洛芙萊斯不太可能接受源自未來的聲明,但洛芙萊斯應該能識別出機器的計算(不過由於正則性和緊性,只能在夢中實現)。即使洛芙萊斯無法掌握計算機的機制,也應該能掌握計算機的目的。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技術都能被過去的觀察者輕易理解:給萊昂納多·達·芬奇展示一架直升機,他很可能會理解該機制的“為什麼”(雖然不是“如何”);而向萊昂納多展示一個運行中的示波器,他可能會同時困惑於“為什麼”和“如何”。至少示波器可以被認為是跨越漫長曆史的人工製品,即使它們的目的在很多情況下仍然模糊不清。然而,向洛芙萊斯或萊昂納多展示克隆綿羊,甚至是其人工合成技術,都有可能將他們嚇跑。
一個超歷史學家的聽眾必須做好準備考慮時間旅行的法理學可能性,還要能從實際角度排除有關人工製品的傳統因果起源。因此,他們還必須認為,所謂的超歷史學家不能根據需要,任意將人工製品偽造到合理的程度。一張現年26歲電影明星的80歲生日照片,似乎更可能源自數字圖像處理,而非時間旅行。一個過去/未來的不對稱性正在顯現:在那裡,十六世紀的工匠不能很好地偽造十二世紀的文物,以欺騙現代科學研究,也許很快(相對來說),人工製品可以足夠完美地偽造成源自任何期望的時期,以欺騙任何可能的檢測(偽造技術和檢測技術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駕齊驅)。聽起來很矛盾,旅行者過高的技術熱情可能會促進懷疑而非相信。它甚至可能被買通去裝作一個過去的旅行者。H.G.威爾斯的時間旅行者(Time Traveller, 1895)在構建他的機器時也許表現出了超出我們當前理解的科學奇蹟,但他很難製造出令人信服的假的放射性碳測年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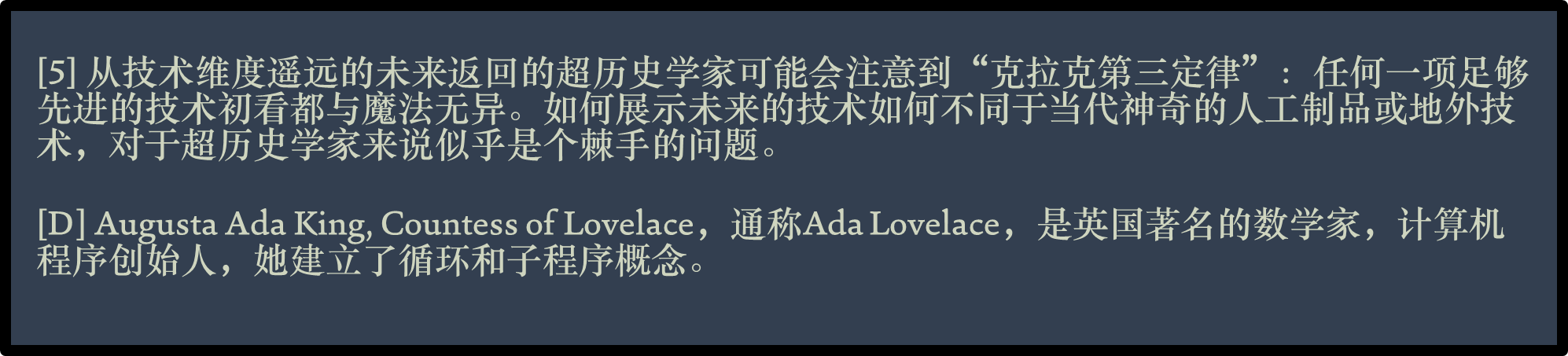
4 超生物學
威爾斯提出了一個“超生物學”問題。當時間旅行者返回他的故鄉時(約1894年),他不由自主地把一束公元802701 年的鮮花放進口袋帶了回去。他的一個聽眾(醫者)在詢問旅行者“你到底從哪裡獲得的這些花?”之前,先檢查了這些花,說它們的雌蕊“奇怪”,並承認“我當然不知道這些花的自然法則”。在這個例子中,花的怪異顯而易見,但提供的時間旅行解釋顯然(也可以理解)是不完備的。“旅行者之花”可能支持(或弱證實)他的故事,但無法證明。
也許將一個80歲的未來電影明星介紹給2022年27歲的自己,會獲得更大的證據權重。超歷史學家更願意提供的建議是檢索,而不是未來的技術或報紙,更不用說幾千年內的動植物了,但現在活著的人的未來階段可以檢測與當下自我的遺傳(和其他)相似性。如果DNA檢測顯示“2075年”80歲與“2022年”27歲在遺傳上完全相同,至少說明兩者都是一個人連續的階段。兩個(生理)年齡相隔53 年的人在隨機遺傳上相同,這將涉及一個巨大的巧合。諸如“在我的時代,基因治療通常會改變一個人的整個基因構成…”這樣的答案似乎太過刻意,在科學上也難以置信(我們也不清楚在什麼條件下,可能會要求對一個人的DNA進行*整體*改寫)。
但是,即使在該例中,時間旅行就必然是一種令人信服的替代解釋嗎?強硬的時間旅行懷疑論者可能會駁斥“80歲”階段為因果正常,人工老化的克隆體。由於似乎更容易產生一個物理上比其原本年輕(或貌似年輕)的克隆體,而不是相反,因此,從未來檢索名人可能比從過去檢索名人更容易被接受。然而,仍有懷疑論者主張:或許青年階段是由老年階段的一個冷凍胚胎——雙胞胎髮育而來,或者說80歲的人是原始DNA的來源,26歲的人是克隆。也許原型被保留下來,而克隆成為了名人,為如今這次旅行騙局做好了準備。當然,其在科學上超越了目前的(更多過去的)技術,但並非完全不可能,這樣的克隆似乎仍然不如時間旅行那麼驚奇。
生物學家經常會發現使用果蠅(Drosophila melanogaster)進行繁殖實驗很方便。假設你向前旅行,獲得一個2022年尚未進化出品系的果蠅。在合適的時間,你帶著你的未來果蠅回到2022年,並將它展示給生物學家,以支持你聲稱自己是一個成功的時光旅行者。此舉存在如下問題:如何表明你的果蠅是一個正常進化,但時間上暫時移位的現有果蠅的後代,而非一個時間上正常的突變體(再次說明,校準未來生物的時期指標缺乏因果正常的支持證據)。如果因果正常的“汙染物”有任何現實存在的可能性,那我們大概會更傾向於這個假設。
對人工飼養的果蠅進行因果檢疫,似乎比對書籍、人工製品或(尤其是)思想進行因果檢疫要容易得多[6]。即使因果隔離可以實現,它也有在檢索中否定任何證據價值的風險,尤其是如果物品/人工製品的後期必須被隱藏,直到它的早期自我通過普通的因果過程出現。如果未來的人工製品在獨立發明之前就被揭露了,那麼觀察者可能會認為所謂的“獨立”發明並非是公認的那種。何況,如果檢索到的未來對象被隔離,直到它們的原型被發現,外部觀察者可能會認為這兩個對象都是一個共同潛在原因的當代結果。試想拿著賴特兄弟1903年第一次成功飛行的老照片回到過去,然後在1904年揭曉,似乎很難說服任何人,照片是正常老化,但回到過去了。即使在1900年揭曉,懷疑論者可能會聲稱萊特的飛行器復現了你的照片,反之亦然。因果循環在這裡赫然出現,即自我循環因果鏈,其中的事件是其自身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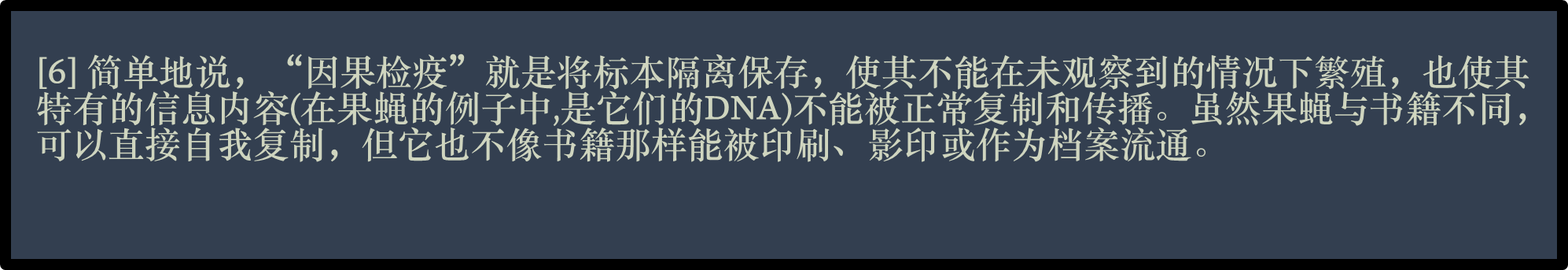
5 信息和物體的(因果)循環
未來-人工製品超歷史學涉及將人工製品帶回到其發明之前的時期。劉易斯懷疑,逆向時間旅行很可能會產生因果循環[7]。因果循環可以是信息循環,也可以是物體循環。當(例如)對象的不同時間階段交換信號時,就會出現信息循環。而物體循環則是名副其實地演化成了它的早期自我。
在劉易斯的經典信息循環案例中,一個時間旅行者回到過去,並命令早期的自己搭建時間機器。命令被嚴格遵守,旅行者回到過去,把原型指令交給他的早期自我。指令通過電話從後來的自我傳遞到過去,並通過記憶從過去的自我留存到以後。而信息究竟來自哪裡?最終,劉易斯認為,不存在*因果*(或許其他)的解釋:
從其他任何途徑都無法獲得這些信息。他的早期自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他的老年自我被告知,信息被構建告知的因果進程所保存。但是信息首先從何而來?整個事件為什麼會發生?根本沒有答案。循環的部分可以解釋,而整體卻不可解釋。
不過,劉易斯同樣認為,試圖解釋因果循環並不比解釋無限的線性因果鏈,或始於某個無因事件的有限鏈更困難(或更容易)。實際上,劉易斯在追問整個因
果鏈為什麼會發生時,診斷出了一個合成謬誤:事件可以被解釋,但整個事件鏈不能被解釋。如果需要解釋某個個體事件從何而來,我們可以調用一個更早的原因(或多個原因);如果要探究一個完整的因果鏈的起源,則可能會令人困惑。劉易斯提出了因果循環的“你也一樣”謬誤:任何因果鏈在最終解釋上(*在永恆的方式下*)都表現出完全相同的困難,無論循環還是線性。這與超歷史有關,因為一個真正未來派生的人工製品,其發明和發展是因果正常的,但在外部時間的出現晚於該人工製品現在的交付。
如果旅行者在過去行動時打斷了建立的任何因果鏈,那麼在未對旅行者出發時刻的條件產生任何影響之前,逆向時間旅行就可能發生,且不存在因果循環[8]。然而,因為人體而導致無數因果鏈分支過程的全面中斷,似乎涉及到類似宇宙陰謀論的東西。即使阻止諸如過去的時間旅行者打噴嚏這樣的世俗事件的所有因果傳遞,也同樣會涉及因果鏈的中斷,不僅涉及旅行者鼻子附近的空氣分子,而且還涉及無數其他因素,包括地球的位置及其引力影響範圍內的任何東西。不過,雖然似乎在任何物理現實世界中都不可能進行完全的因果檢疫,但信息檢疫卻有可能實現,例如將未來的標本放進密封的容器,保存到指定的日期。
假設劉易斯的因果循環在邏輯上可能,那麼未來的超歷史人工製品就會引發因果循環的問題,最終可能會破壞關於這些人工製品是未來派生的說法。因果循環中的信息必然是難以斷代的——在信息沿線性因果鏈傳遞的背景下,這種信息看起來似乎因果反常,貌似明確但其斷代卻不那麼明確。假設人們回到1586年,將“他的”2022年《哈姆雷特》印本呈現給年輕的莎士比亞。如果莎士比亞複製了這部戲劇,並將其作為歷史記錄適當印製,就不會出現前後不一致的情況。但是我們無從知曉:①《哈姆雷特》是誰寫的;②《哈姆雷特》產生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哈姆雷特》的文本在外部時間中仍然具有鮮明的*先在性*,但這並不等同於存在一個明確的開端)。如果一個未來的人工製品在更早的時間發現,卻在未來的時間發明,那麼我們假想的《哈姆雷特》文本在兩方面就不算一個未來的人工製品:首先,它缺乏一個明確的創造日期;其次,它可能根本就不是被創造的。雖然在運輸、複製和印刷過程中的每一個步驟都可能有明確和可核實的日期,但對於《哈姆雷特》的創作,可能並無明確的日期,因為(*更何況*)沒有創作。《哈姆雷特》的這篇文本是一個偽造物——一個沒有創作者的藝術作品[9]。
只有信息在劉易斯的電話循環中傳遞:沒有一個物理對象在數值上與它的早期自我相同,但仍然存在一個封閉的自因知識循環。相比之下,麥克貝思討論了“物體循環”:自相交的旅程,其中軀體在數值上與早期的自我相同,且“時空中的路徑是閉合的環”。一個物體理論上可以是同一個物體的循環,但也可以*促成*一個信息循環(正如任何一種因果循環都可能影響正常的、線性的因果鏈,並受其影響)。哈里森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在該例中,一位時間旅行者用一張圖象紙來呈現他的早期自我,之後早期的自我使用該圖來實現旅行者的自我滿足。該圖在同一個旅行者的各個階段之間傳遞,並不獨立存在。該圖的內容有助於形成一個信息循環(這本身就促成了小說主要情節“更廣泛”的因果循環),而刻寫該圖的紙張本身就是一個物體循環。
物體循環存在嚴重的物理問題。哈里森的紙是如何回到其更早的物理狀態的?(例如)老化、磨損、改變粒子能級和熵的影響都如何消除?以及,假設物體循環的紙攜帶“年齡”指標,這些指標究竟記錄了什麼?大概不是紙張自印刷以來的累積老化,因為它從未印刷過,也不是由木纖維製成的。在任何我們可以觸及的、符合法理學的世界裡,物體循環在物理學上似乎並無存在可能。
劉易斯的目的是駁斥經常用來反駁因果循環的異議,即允許創造信息*無中生有*。戴維·多維奇認為,在非劉易斯精神下,只有多重世界版本的時間旅行才可被接受,部分是因為在單一世界(或因果鏈)內的旅行會產生因果循環和信息的*無中生有*[10]。多維奇援引卡爾·波普爾“知識只有通過進化、理性的過程才會產生”的原則,並將其提升為對因果循環假定的法則式反對。多維奇明確地將波普爾的“進化”原則的資質與神創論進行了比較。多維奇在創造和其他因果性之間的類比時似乎涉及超歷史學。對物體循環中年齡指標的證據訴求似乎讓人聯想到戈斯,後者試圖將化石記錄與聖經直譯主義相調和。戈斯認為,任何被創造出來的、包含了後續生命的真正原型地球,都必須承受一個不存在的過去的虛假痕跡,如伊甸園樹的年輪、亞當的肚臍等。也許戈斯也在不經意間表明,這個假設在邏輯上無可指責(或至少對當代的一切觀察具有免疫力),但在經驗上卻無法令人信服,因而有效地從實際考慮中排除了自己。物體循環也可能帶有他們從未經歷過的“幽靈”歷史的痕跡。
然而,儘管戈斯的假設是一個解釋的死衚衕,但我們並不清楚波普爾的原則是否為真(更不用說自然規律了),也不清楚就算把它奉為普遍真理,它還具有什麼其他的模型力量。劉易斯的“你也一樣”謬誤療法似乎對因果循環困境有所幫助:進化/因果解釋可能足以解釋信息的傳遞,但似乎沒有(因果或其他)解釋信息的最終來源(*在永恆的方式下*)。儘管如此,即使人們堅定認為創造、因果循環或其他因果關係幾乎只會產生劣質的(甚至不存在的)解釋,也許我們所偏愛的解釋模型也不應該將它們先驗地驅逐出去。
就像我們認為的(即在法理上允許的或然世界)那樣,即使時間旅行是可行的,我們仍不清楚在物理規律支配的世界中,物體循環是否可能發生。然而,即便進一步賦予物體循環在(形而上)物理學可能的(非常可觀的)特許權,也會出現一個特殊的超歷史問題:因為物體循環必須以某種方式演化成它們的早期自我,物體循環的年齡指標不必(也許不能)是真正真實的。物體循環,即使在法理上可能,似乎也很難以任何可靠的方式被賦予年齡指標[11]。物體循環似乎受到限制,在其旅程的某處演化回數值上更早的狀態。這種重置將涉及物體具有的所有年齡指標的明顯覆蓋[12]。此外,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可能會破壞物體循環作為時間旅行者的地位:如果物體循環缺乏(或者只有不穩定/不可靠的)年齡指標,他們就有可能失去連續的個人時間。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根本就不走時間之路。因果關係,甚至因果循環,可以在沒有時間旅行的情況下產生,例如通過神性/本體性的(或其他超時空現象)中介,其他形式的反向因果或瞬時因果。此外,正如哈里森的論文所指出的那樣,物體循環可能在沒有人工製品的情況下出現,因為它們從未被製造、加工、塑造或設計過。嚴格說,一個超歷史的未來人工製品是在某一時間被製造出來的,但在較早的外部時間被交付(和研究)。這樣的物體在時間上會出現異常,但在其他方面是正常的。物體循環可能是因果反常的,但不可能真是人工製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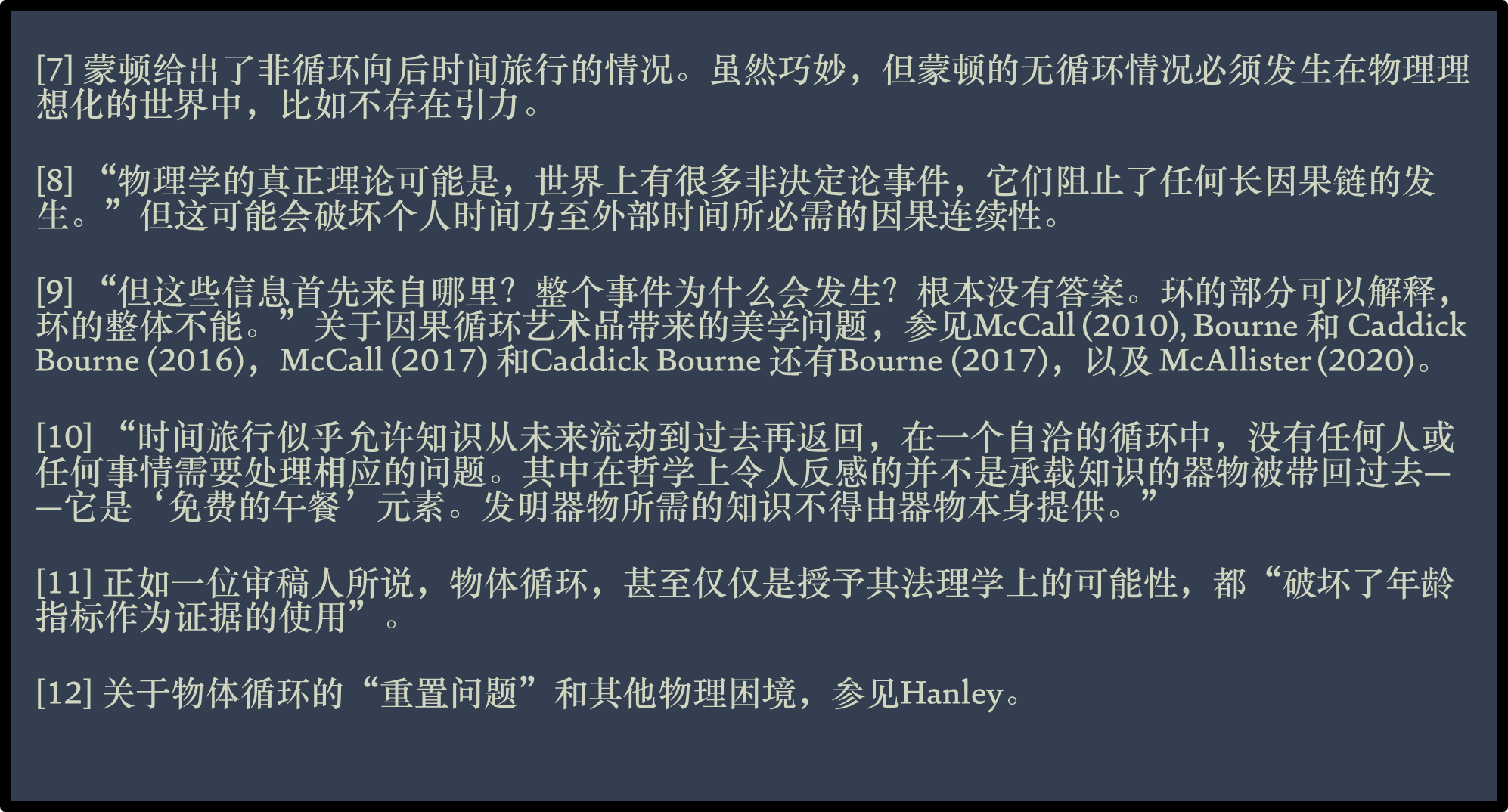
6 結論:超歷史學的可能性和更深層陷阱
我們也可以設想其他超歷史實驗,比如給當代名人夫婦提供他們未來婚姻破裂的明顯證據。但這樣的預言可能是在沒有時間旅行的情況下自行實現的。不論它是否是真實的和未來衍生的,婚姻都可能因這種“證據”所引發的相互間的不信任而解體。比較另一個自行實現的預言:對一個明顯在搖晃且自信不足的走鋼絲者喊“你要倒下了”。如果預測的跌倒發生了,真正的預言(逆向旅行信息仍然較少)不太可能是預測成功的最佳解釋,比如A在六次近距離射擊B(無防護)前,預測B即將死亡。對於真正的預言來說,成功地預測未來事件是必要不充分條件——成功的先知也必須是無法(或者不太可能)通過因果正常的手段造成被預言的事件,或通過正常的歸納手段已經預測了它[13]。成功的預測也同樣適用於超歷史證據:如果成功的預測是時間旅行的證據,那麼由其他方法得出的預測的可能性必然比時間旅行解釋的可能性要低。無論如何,我們關注的是作為超歷史證據的未來人工製品。
然而,基於未來的研究不能沒有資源。假設一個旅行者帶著哥德巴赫猜想的十行證明從未來返回,證明其是正確的——在這裡,即使信息的來源無法證明,也可以直接驗證信息的可靠性。但試圖通過信息證明是非人工製品的,也不涉及超歷史*物體*。同樣,將懷疑者帶到未來,直接讓懷疑者進行驗證也許令人信服,但並不涉及*人工製造*的超歷史(對時間的其他直接觀察既不能提供人工製造的證據,也不能提供超歷史的證據)。因此,總體而言,未來衍生的超歷史人工製品作為人工製品的證據價值似乎與過去衍生的表兄一樣,可以忽略不計,因此,他們宣揚的主張並未得到言詞證據和/或成功的預測等的支持[14]。
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的超歷史,都面臨著一個問題:需要對發生的任意現象做出更完美或更合理的時間旅行解釋。但總體而言,“未來”超歷史學家面臨的困境更糟糕。四個主要問題如下:① 對於過去遺留的人工製品,至少可以獨立檢查週期指標,即來源是非時間跨度的 [15]。但是,任何由未來人工製品負載的週期指標都不能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進行校準,而這些證據本身必須來源於時間旅行。② 公開未來衍生物體會導致信息循環風險,從而破壞其作為未來發明的地位。即便認為自因信息可能存在,其也不一定是被髮明出來的。③ 物體循環回到自身的存疑的演化可能會破壞他們是真正時間旅行者的任何證據。甚至可能會中斷它們的個人時間,或使它們無法獲得明確的個人時間,從而阻止他們成為真正的時間旅行者。④ 這樣的演化也帶來了進一步的問題:物體循環中的器物是否能被歸類為真正的人工製品。物體循環中的“人工製品”是(嚴格地)矛盾的:它們或許在能想到的所有程度上與人工製品相似,但仍然是沒有人制造的“人工製品”。因此,基於未來的*人工製品超歷史學*總體前景黯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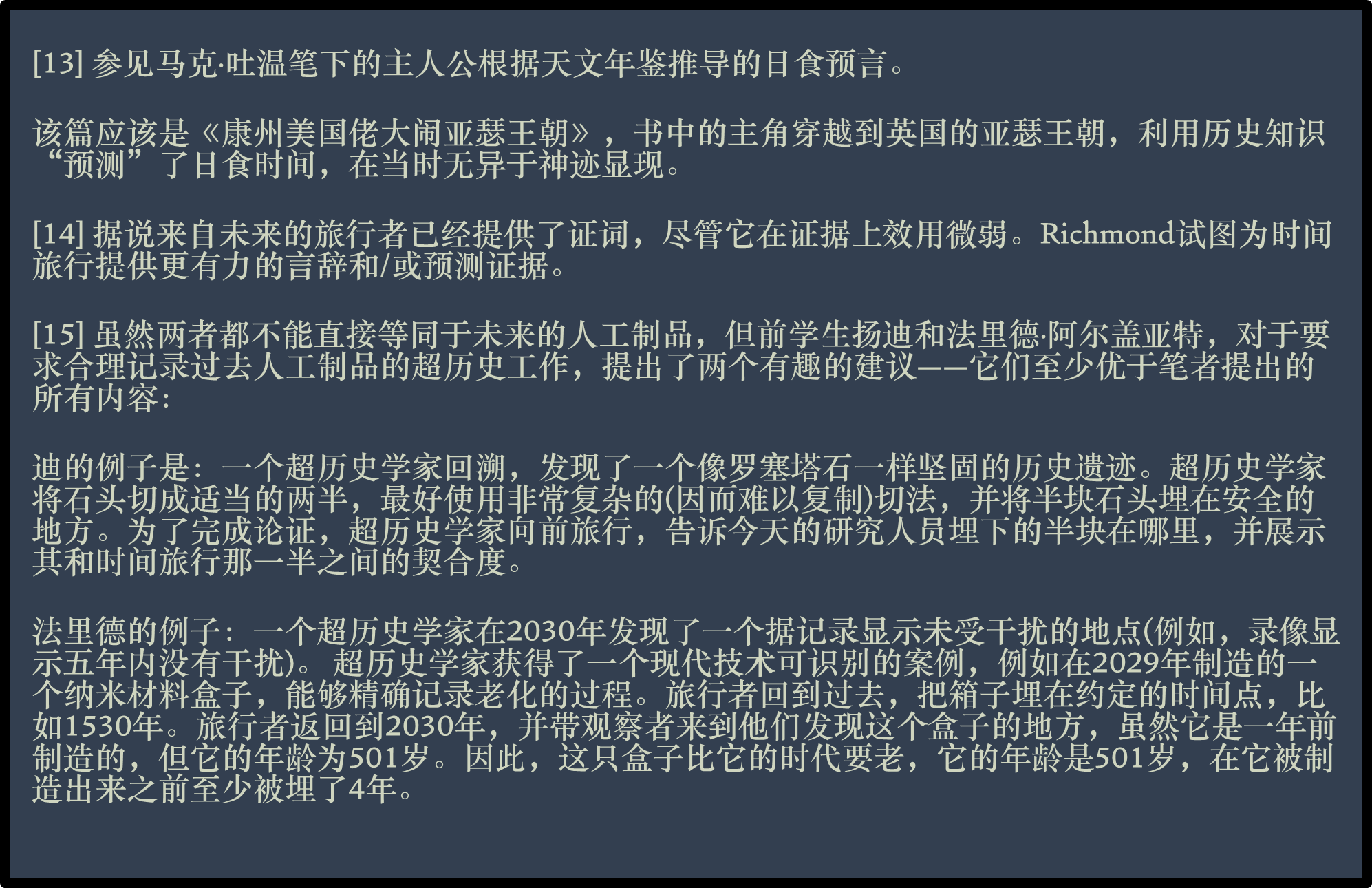
致謝
非常感謝Ratio的審稿人給出了非常詳細和有益的評論,感謝皮特·米利肯提供“哥德巴赫猜想”的例子,感謝楊迪給出了“羅塞塔石頭”的例子,感謝法裡德·阿爾蓋亞特給出了“納米材料盒子”的例子。
參考文獻
Bourne, C., & Caddick Bourne, E. (2016). The art of time travel: An insoluble problem solved. Special Issue of Manuscrito: Time and Reality I, editor Emiliano Boccardi, 39, 305–313.
Caddick Bourne, E., & Bourne, C. (2017). The art of time travel: A bigger picture. Manuscrito, 40, 281–287.
Chiang, H. C., & Hodson, A. C. (1950). An analytical study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Ecological Monographs, 20, 173–206.
Clark, A. C. (1962/1973). Profiles of the future: An e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1962 edition: London, Gollancz, revised 1973 edition; London, Pan.
Currie, L. A. (2004). The remarkable metrological history of radiocarbon dating [II]. Journal of Research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109, 185–217.
Daniels, P. (2014). Lewisian time travel in a relativistic setting. Metaphysica, 2014(15), 329–345.
Deutsch, D., & Lockwood, M. (1994, March). The quantum physics of time travel. Scientific American, 270, 68–74.
Gosse, P. H. (1857). Omphalos: An attempt to untie the geological knot. John Van Voorst.
Hanley, R. (2004). No end in sight: Causal loops in philosophy, physics and fiction. Synthese, 141, 123–152.
Harrison, H. (1967). The technicolor time machine. Doubleday.
Hogarth, M. (1994). Non-Turing computers and non-turing computability. PSA: 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1, 126–138.
Lewis, D. (1976). The paradoxes of time travel.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3, 145–152.
MacBeath, M. (1982). Who was Dr Who's father?Synthese, 51, 397–430.
McAllister, J. (2020). Does artistic value pose a special problem for time travel theories?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60, 61–69.
McCall, S. (2010). An insoluble problem. Analysis, 70, 647–648.
McCall, S. (2017). Note on “The art of time travel: An insoluble problem solved”. Manuscrito, 40, 279–280.
Modgil, M., & Sahdev, H. (2001). Recurrence metrics and the physics of closed time-like curves. Department of Physics,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ttps://core.ac.uk/downl oad/pdf/25316 548.pdf
Monton, B. (2009). Time travel without causal loop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9, 54–67.
Nahin, P. (1999). Time machines: Time travel in physics, metaphysics and science fiction (1st ed. 1993, 2nd ed. 1999).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Richmond, A. (2010a). Time travel, parahistory and the past artefact dilemma. Philosophy, 85, 369–373.
Richmond, A. (2010b). Time travel testimony and the ‘John Titor’ fiasco. THINK: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26, 7–20.
Sorensen, R. (1987). Time travel, parahistory and Hume. Philosophy, 62, 227–236.
Twain, M. (1889). 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 Charles Webster and Company.
Wasserman, R. (2018). Paradoxes of time trav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lls, H. G. (1895). The time machine, cited here from The definitive time machine, edited by Harry M. Gedu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