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劇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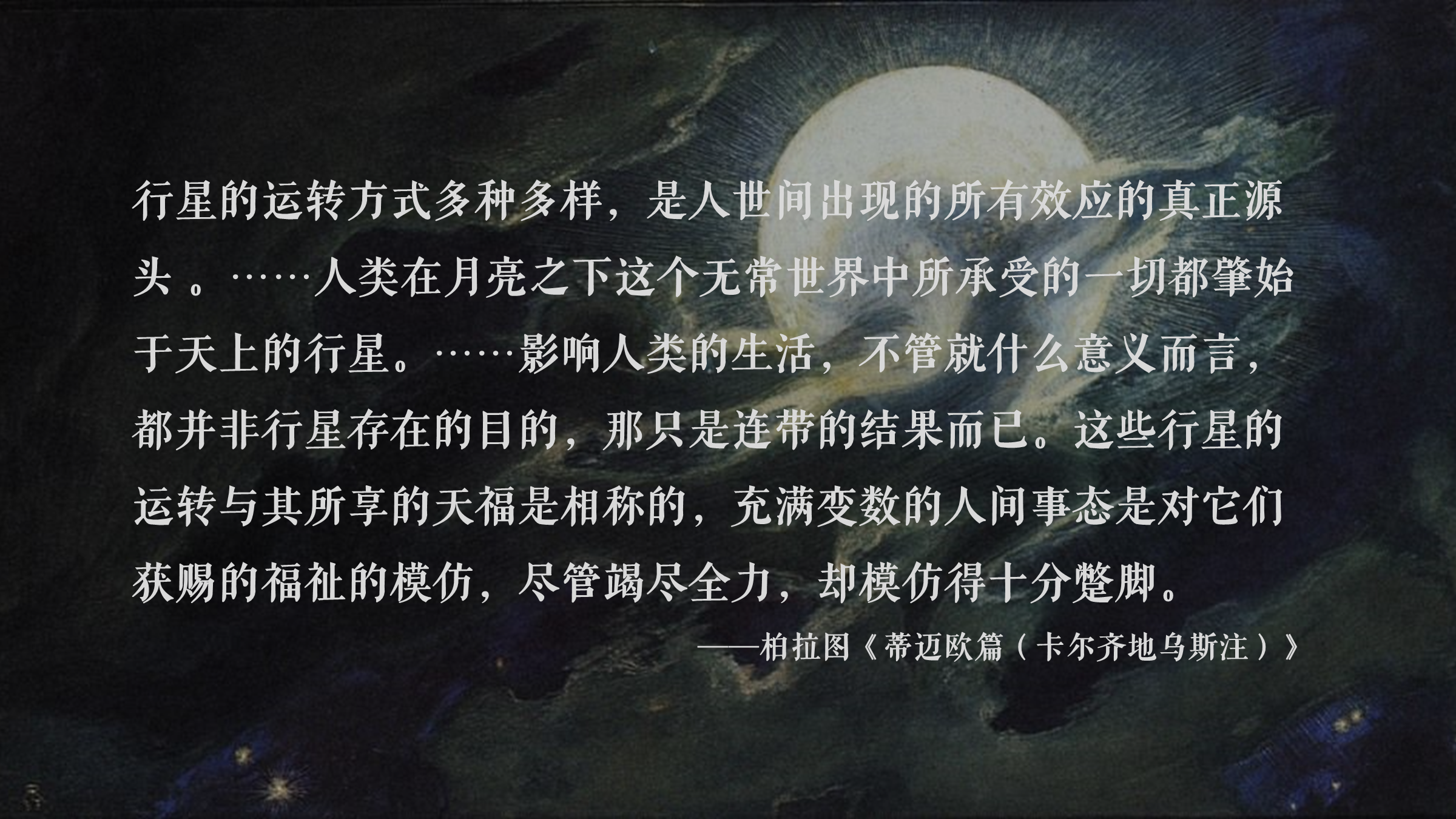
秀盡和月光館的高中生,其實沒什麼兩樣。
不懼框限,打破舊世界的枷鎖;乳臭未乾,儘早學習成人的法則:兩者皆是學生的標籤。(離校後的)青春懷舊與(離校前的)渴望成熟,便是關於學生的永恆主題,或美其名曰“學生氣質”。在這裡,學生不再是一個特定的年齡段、地域群體,而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關於學生的自我幻想,既是(像那位永遠支持美鶴學姐的女同學一樣)(自己)在幻想自己眼中的他人,也是(像順平一樣)(自己)在幻想他人眼中的自己。從這個意義(幻想彼此相向)來說,這些(理應是)最謙遜的狂傲之人,同時也會有一顆自我監視的羞恥心。
1.月下世界的蒙羞:將中途作為開端
羞恥(shame),即在意周圍的(並且往往是異樣的)眼光。可以想到,羞恥的終點就是自己以假想的眼光時刻注視自己,並把在此關注之下的行動內化為所謂的職責或義務,這(結果)也可稱為一種(發生學意義上的)自律或自覺(以區別於義務論意義上的自律或自覺)。
我想,“羞恥的發展”或許是《女神異聞錄3》(以下簡稱“P3”)情節組織的決定性要素,同時也是它和《女神異聞錄5》(以下簡稱“P5”)在此方面最大的不同。
從結果上看,P5的情節本質上就是以JOKER作為原點的。一切人物都因為與他之間的某種瓜葛而得以登場。另一方面,P3的情節原點則是十年前人工島的那場事件(或者說事故),所有出場人物都或多或少是這場事件及其後果的受害者(受益者)。一個充滿了無限可能的少年將帶領怪盜團(激發內心的反抗之魂)化潛能為現實;一個木已成舟的災難將(並不平等地)改變每一個當事人的生活。掀起革命和平息事端之間的差別也是顯而易見的。也因此,我認為雨宮蓮和結城理這兩位主角之間基本沒有什麼直接的可比性。或者說,將十年前的那場事件視為P3背後一切主題的隱秘起點,才是一種更為恰當的比較方式。
但話說回來,這與所謂的“羞恥”又有什麼關係嗎?難道說由加莉的出浴福利動畫,或者在作戰室偷窺宿舍內同學的隱私生活,就是這一點的體現嗎?並不是。羞恥的發展,應該說是一個逐漸抽象化的過程。神出鬼沒、總是在不該出現的時機出現在教室窗戶外的班主任,舞臺下隨時可能笑話你表演的觀眾,更多地應該認為是一種形象化的描述。而發展到可以稱之為性格特質的羞恥感,需要的主要是假定的、預判的、長時間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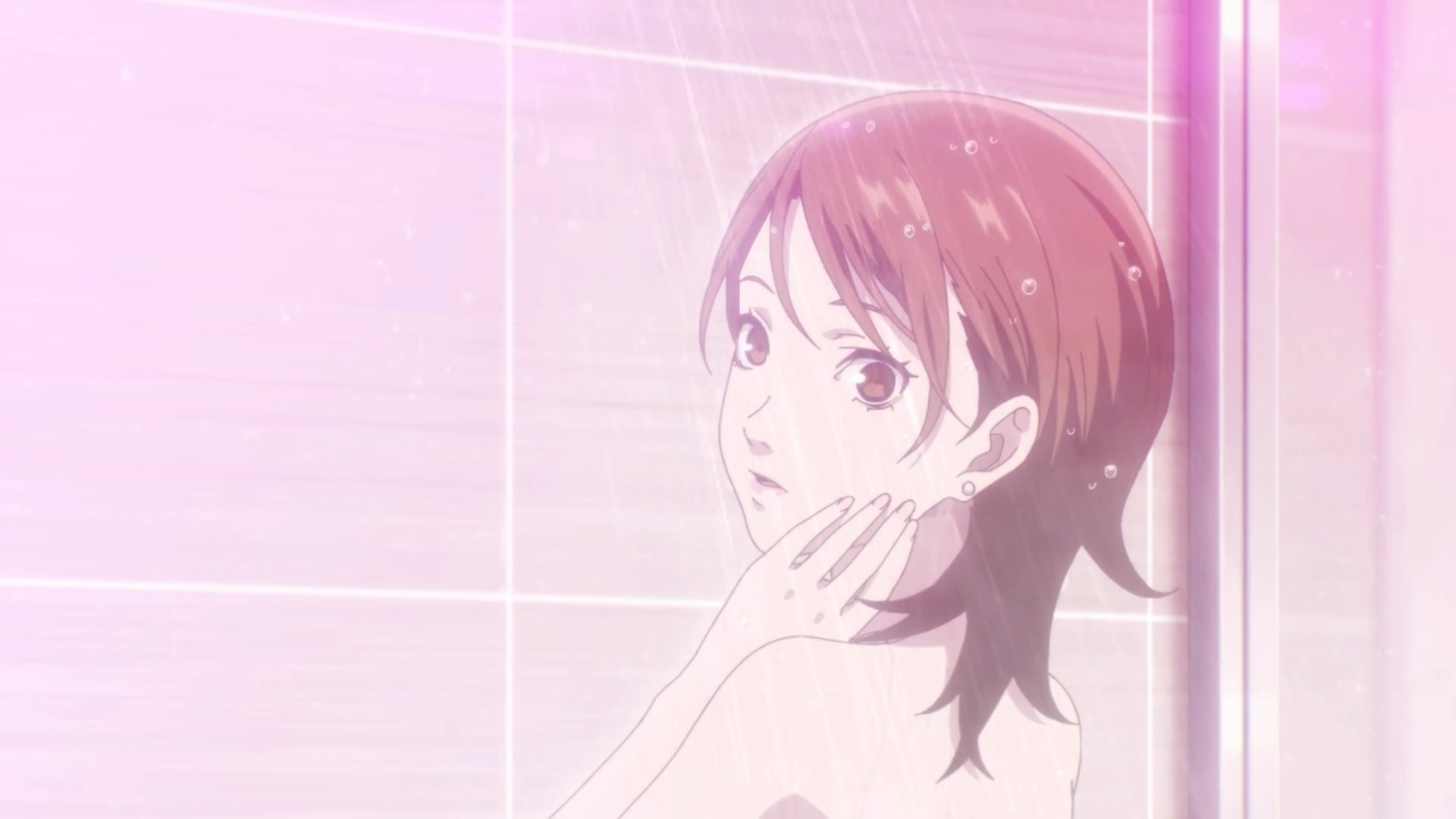
而在P3中,唯一具備這種條件的(抽象化的)目光之源正是十年前的那場事件,它本身就是一個巨型的注視者、環形監獄(panopticon)的中央監視塔。並且如前所述,和同輩、父母、老師的(較為具象化的)注視壓力相比,它將帶來一種高度發達的羞恥(這同時也意味著一種高度內化的自律的成型)。因為,教育而來的(習得的)羞恥反應(即對具象化目光的應激),總歸是扭捏而不自在的;而趨於完成的羞恥,並不意味著這種扭捏的結束,而是以近乎麻木的狀態去
習慣它的常在。
更具體地說,羞恥的完成隱含著某種質變。在完全相同的變量控制條件之下,這樣的羞恥感卻以絕對隱性的方式反映。“自然而然的不自在”這種說法雖然聽著怪異,但卻是對P3中那麼多個不大正常、扭捏、神經兮兮、謎語人的主要角色的最恰當描述。歸根到底,應該問十年前的那場事件後果是什麼呢?詭異的影時間、望不到頂的毀滅之塔“塔爾塔羅斯”(Tartarus,即希臘神話中的地獄)與夜母倪克斯(Nyx,希臘神話中的夜神)……
這場人禍宣告了月下世界的真正到來,拉下了使人蒙羞的夜幕。而被捲入這一核心事件的人物在劇情的不斷發展中逐漸發現了自己與之的真正關聯。但他們從出場的一開始就以自己的方式承受了這樣那樣巨大的恥辱。這樣的羞恥感毫無疑問是早熟的,這也就意味著,P3在兩個方面都遵循著自《荷馬史詩》以來“故事從中間開始”的金科玉律。儘管和P5刻意使用閃回和倒敘的編排操弄相比,顯得相當稚嫩和原始,但更為重要的是,P3提供了從中間開始的人物和從中間開始的故事。
這也要求,(從劇情的編排來說,)P3的人物塑造要在其個性的發展中重新確立真正的開端,結束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恥狀態,呈現真正的人物自畫像。也因此,特別課外活動部(以下簡稱“SEES”)每一位成員的人格面具二次覺醒,與其說標誌著他們精神成長的新階段,倒不如說是向本心的迴歸。
即便如此,難道P5就不具備所謂“羞恥的發展”嗎?恰恰相反,P5對羞恥的理解相當到位。碎片化、印象式的東京地域切面,擁擠而忙碌,或許只有(生活在東京都市圈的)日本人才能憑自己的真實體會設計出來。最關鍵的是,它確實還原了在擁擠的公共空間中逃遁到(或尋找到、甚至說是創造出)舒適的私人領域的這一體驗,並且這同時也是它對Galgame主人公-對象的二元孤立(私人)世界侷限的改良和敞開。
但是,P5對羞恥感的恰當把握(同時也是對現實的生活方式的扼要表現)始終停留在日常活動的展開中。劇情的展開則依賴於怪盜團不畏強權、掙脫桎梏的正義信念,以及在關鍵時刻總能化險為夷的(並通過特殊的遊戲玩法機制表現的)聰明才智。這也是一個經受了無數的網絡文學、電視劇集優勝劣汰後被當代消費者普遍接受的金科玉律。
反過來說,P3(以現在的眼光來說並不流行)的蒙羞之恥,將它自己推向了一個情節發展的極點。月下世界,如同行將沉沒的泰坦尼克,拉著所有乘客一起下水。故事的重點並不在於某些眷侶可歌可泣的羅曼蒂克,而是眾生屍沉大海前的掙扎。
宗教寓言式的末世氛圍構成了月下世界的陰面;偶然介入的邊緣人物(實際上所有人都是邊緣人物)構成了月下世界的陽面。從這個意義上說,P5和P3的主旨昇華路徑是相反的:前者從個人的德性通向了對全人類集體潛意識的謳歌,後者把握住了使人蒙羞的命中註定之下個人的寂滅。
當然,這只是一種相對淺顯易懂的理解。我的真實看法是,P3實際造成了宗教寓言和人格刻畫之間的矛盾,並且在處置這對矛盾的過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在本文的餘下部分我將主要就這對矛盾的兩方面分別展開聊聊。
2.宗教寓言:邪教還是異教?
P3給人的初步印象是,神神叨叨的。課堂上保健老師(實際上應該說是神秘學老師)數倍於其他任課老師的對話文本量,也絲毫不掩飾創作者對神秘、靈脩話題的宣揚(含貶義)。或者說,在這個雜糅的原創塔羅牌體系之下,萬物的秩序都得到了安排,我們要做的僅僅是正確地認識其寓意。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社群系統,本質上要對這一神秘秩序負責。也因此,不僅玩家不應該對大阿爾卡納牌的秩序產生積極影響,相反,這秩序應該反過來抵制玩家對其神秘寓意的曲解。
老實說,這樣的社群系統很難不是無趣的。原因實際上已經包含在上一段的陳述中:一方面是內容(在實質上)的無所不包,或者用更專業的術語來說,周延性太強;另一方面是形式的嚴格,要求在規則之內給予詮釋。這樣的結果就是,在無論如何都能自圓其說的前提下,作繭自縛。也因此,P3社群系統的樂趣(如果確實存在的話)不在於內容和形式之間的巧妙(和恰當)關聯,而只能在於形式之內自顧自的較勁。
從另一個角度說,這樣的社群系統勢必會造就許多缺乏血肉的人物,因為它需要的正是形式極端的提線木偶。儘管人們一般會同意,社群系統的精髓一直都是,用相對獨立短小的篇幅,剖開角色的生活橫切面,與他們(冰山一角的)酸甜苦辣共情,又或者說,是在尋求一種不尋常的日常感。然而,極端的形式遮蔽了他們自然地享受日常生活(並超越預定的神秘秩序)的可能。
公認最出彩的太陽社群,講述的是一個垂死青年生命燃盡前的故事。在太陽社群完成COOP之時,他的生命也隨之走到終點(甚至在此之前已經終結)。神木秋成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寓言式的人物,這其中的悖論正在於,我們需要反抗整個極端形式所支持的神秘寓意(這是P3社群系統的樂趣所在),來獲取日常的樂趣。又或者說,日常即使確實具有樂趣,也不是P3的社群系統所推崇的。
為什麼P3的社群系統要如此彆扭、如此苦澀?或許神秘主義愛好者能從中提取出更多的樂趣。但至少我不是一個神秘主義者,很多玩家都不是神秘主義者,甚至當代遊戲的流行趨勢就是拒絕過分的神秘主義。但就此而論,P3鐵了心要講述一部宗教寓言,(暫且不考慮它對某部著名動畫的致敬)甘心讓絕對秩序或是超越強力接管整個月下世界,誤打誤撞也好,故意為之也罷,社群系統似乎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甚至可以說,社群系統的不明所以與微言大義,強化了我們對這個未知秩序的敬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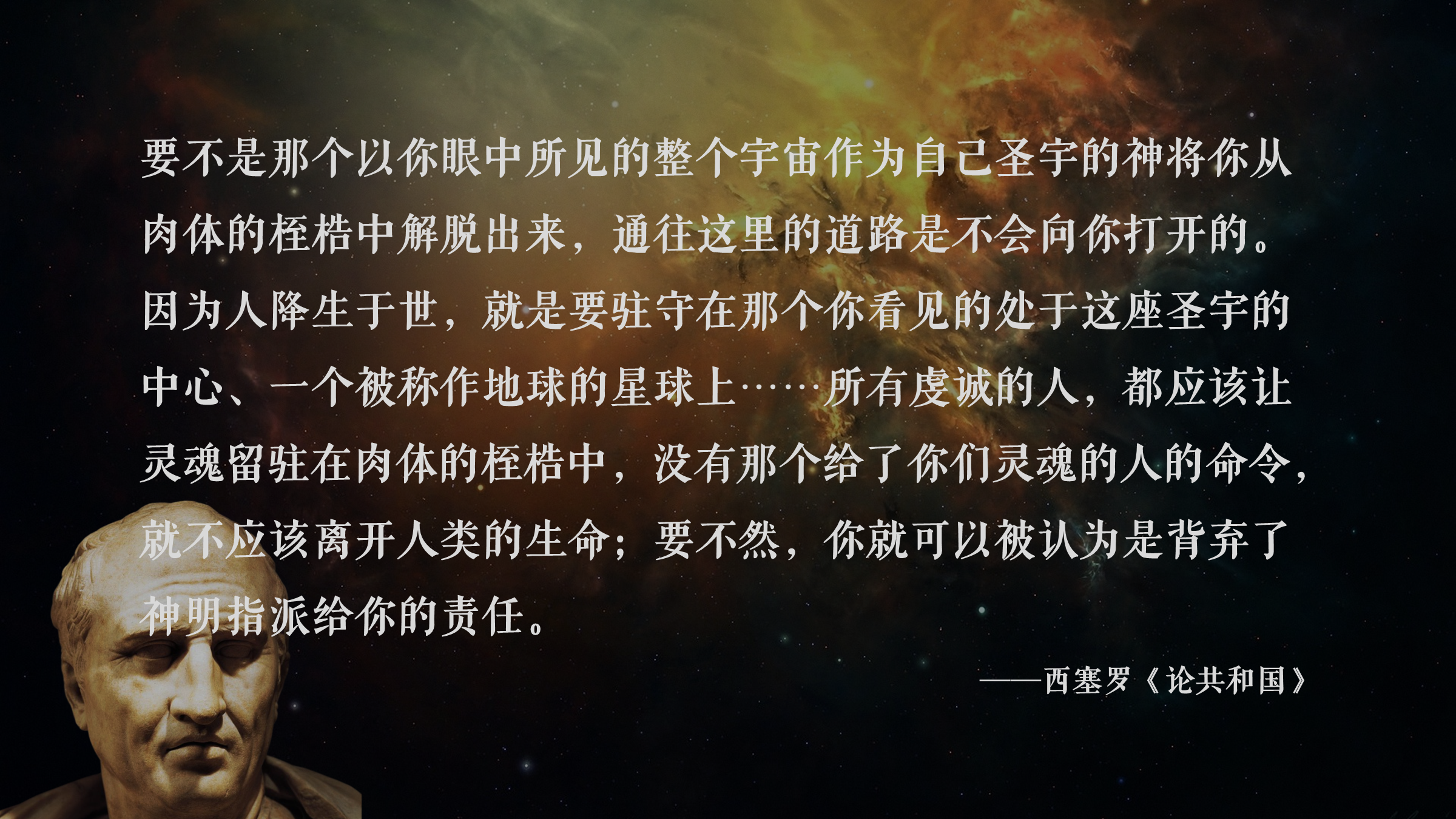
月下世界的蒙羞(作為來源)可以發展成責任。而在西塞羅看來,神明的指派禁令也可以決定責任。儘管從字面意思來看,這種責任只是在強調人類對肉體生命的正當處置,但在主流的寓意傳統(以及諸多基督教學者的努力)之下,這是一個更體系化的(先成的)責任觀的一部分,這種責任觀有“天職”“罪責”等關鍵詞。不得不承認,高度發達(如前所述)的責任與先成的責任在形式上是相當接近的,那麼,隨之而來的將是體現在整部宗教寓言中的迷惑性。
作為對比,P5中的“異世界”是一種怎樣的存在呢?怪盜團的口號之一是:“Life Will Change(生活會改變的)”。更嚴格地來說,應該是:“(Real) Life Will (Be) Change(d)(現實的生活將被改變)”。在P5中, “夢是被掩蓋的慾望的表達”這一精神分析慣用的論點強調了夢境(或者說心靈世界)對於現實的延續。也可以說,心靈世界只是一個相對意義上較難以達到的“某處”,它是現實的預備或者啟示(revelacioun),進而也是現實的一部分。
而另一方面,P3的影時間並不具備上述特點,它是蒙恩者們的樂園,反過來說也是未蒙恩者的地獄。處於影時間的月下世界,實際上只生存著兩類脫離棺材而自由行走之人。儘管他們都享有獨一而無法向他人傳達的記憶,但現實生活的改變不是(如P5中)心靈世界對現實世界的影響,而要麼是蒙恩者們自相殘殺留下的惡果與遺骸,要麼是未蒙恩者遭受的暗影(Shadow)吞噬,即無氣力症(Apathy Syndrome)。也就是說,它是從否定的意義上,強調“(現實的)生活不應該被(影時間下的世界)改變”:現實世界相對於影時間的月下世界具有獨立性,反之亦然。
你可以從中體會到一神教對異教者進行惡毒詛咒的慣用伎倆。同時,和一神教樂於塑造的彼岸世界類似,影時間從本質上說是不可到達的、超驗的非現實。與這樣的超驗影時間相稱的,是某種程度上的預定得救論(Predestination)、對倪克斯頗有否定神學意味的描述、以及滲透著神秘旨意的月下世界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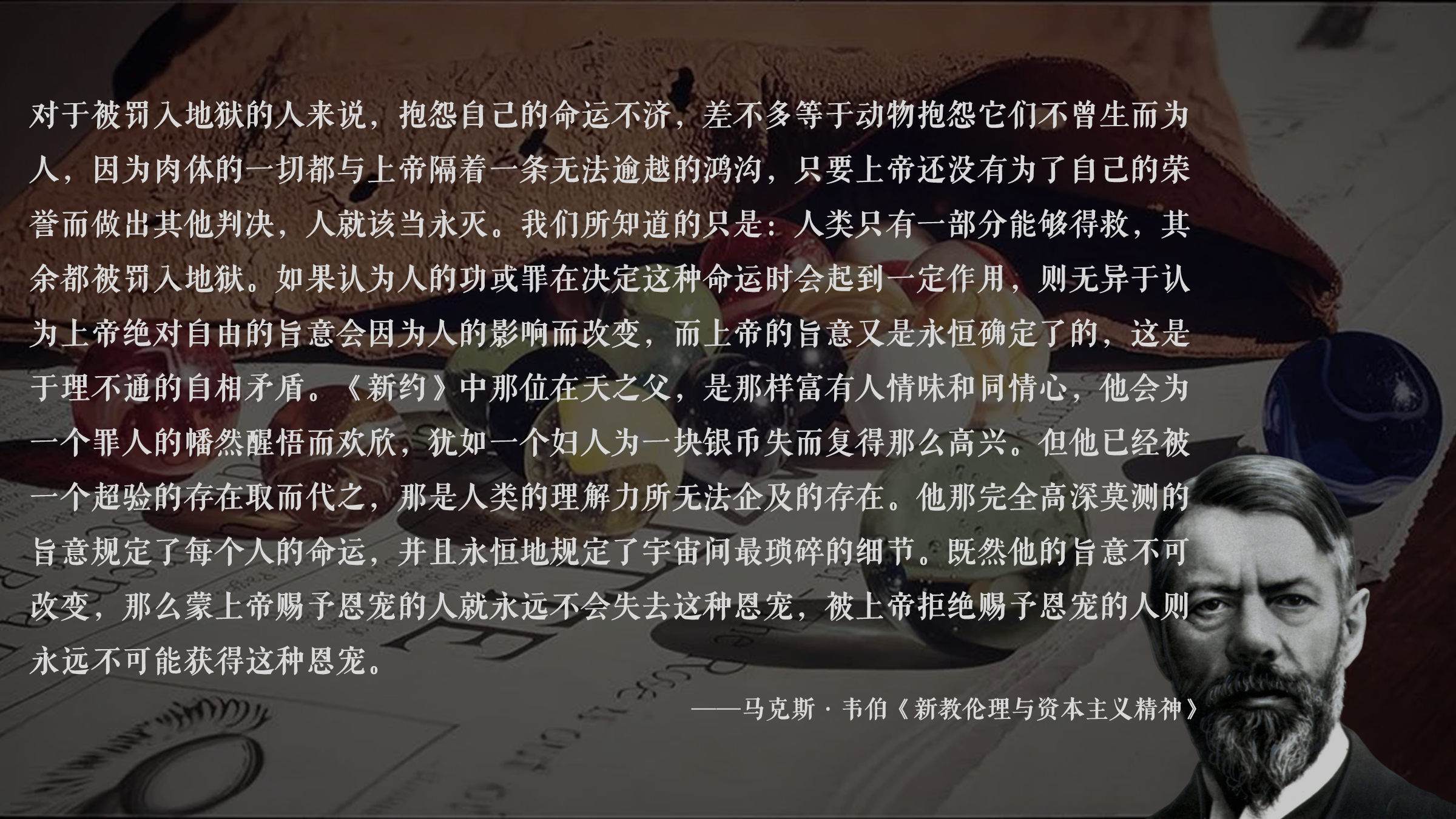
我想,韋伯這段對加爾文主義核心思想的著名描述,對P3的月下世界來說也是契合的。雖然宗教寓言的所有構件實際上已經齊全了,P3還是描述了一個被稱為“邪教”的思想來強化(反襯)我們對這部寓言的印象(不必多說,這也是一神教攻擊異教進而標榜自身的慣用伎倆)。這些描述主要見於反派團隊史特雷加、月亮社群末光望美的經歷,以及主線劇情的正月時間。簡單來說,聖域得救、入會斂財、末日來臨:一切關於基督教(更準確的來說應該是天主教?)精華或糟粕的刻板印象在此集結。臭名昭著(各種意義上的 (¬、¬))的美食大王,還有SEES絕大多數成員對其的明確抗拒態度,都強烈地左右著我們對所謂“邪教”思想的定性。這又造成了一個迷惑的假象:P3的劇情走向處於邪教的完全對立面。
事實則是,P3沒有在任何意義上否定末世論與預定得救。更準確地說,它只是一種不滿於邪教表述的殊途同歸。對於根本無法參透影時間的凡夫俗子,末日前的期待不過是自作多情的操勞;即使存在末日的解決辦法,也是人格面具覺醒者——倪克斯討伐隊的責任,而不是這些只是藉機斂財、實際上愚昧無知的非蒙恩者的任務。
如果P3算得上是一部要素齊全的宗教寓言的話,這便是它(必須)隱含的弦外之音。這是對日常(俗世)的強烈拒斥:儘管末日前的月下世界已經失去了以往
的色彩,最終的目標也是恢復俗世的原本秩序,但唯一可行的救贖之道在於,遁入絕對神秘的超驗世界(影時間)中,完成末日的審判。
總而言之,P3對宗教寓言呈現的迷惑性一方面體現在,SEES的各個(人類)成員在劇情的關鍵處,終結了(早熟的)羞恥姿態,反向地溯源回了某種(存在主義式的)本真,但與此同時他們先前的(因為羞恥的終結而缺失的)責任也被替換為了(形式上接近的)由宗教命運所指派的另一重責任。另一方面則是,SEES在重新集結成倪克斯討伐隊後,儘管宣稱對消極末世論的抵制,實際上自己已經深陷入另一種神秘主義傾向的末世論之中。
簡言之,P3在整體順利地講述出一個命運感、神秘性越來越強的宗教寓言的過程中,出現了若干(細微的)小插曲。如上文所說的,導致這些插曲的原因不是別的,正是P3面臨的巨大矛盾的另一方面。
3.人格面具:將開端作為中途
P3召喚人格面具的方式毫無疑問是非常酷的,畢竟開槍自盡這種強烈的視聽衝突是反常識的。我想作為玩家不應該首先代入明彥或美鶴這兩個老油條的視角,也不應該代入結城理這個“影時間的寵兒”的視角,而應該代入作為新手的由加莉的視角。

可以假想一種更溫和的召喚方式(消耗自己的靈魂之力?),但SEES的槍型召喚器要求召喚者用絕對的暴力結束(而非消耗)自己的生命,並且在成功召喚前,永遠無法知道自己的結局。簡言之,這就是零與壹之間的信仰之躍。在P3劇情的開場動畫中,由加莉自己在房間裡嘗試扣下召喚器的扳機。重點不在於她失敗了(膽怯了?),而是她正處於一個絕對密閉的空間之中獨自上路。
實際上,任何(原始形式的)召喚儀式,都或多或少地具有這樣的瞬時超越性以及絕對的隱秘性。這些(一開始令常人感到驚悚的)召喚儀式,隨著隱秘性的逐漸消失,也會慢慢變成(在認知上無害的)象徵符號。很多玩家不滿於P3初次召喚人格面具時的草率刻畫。但其實換個角度想,這種召喚方式根本就是難以表現的:它不是(如P5那樣)對潛藏於內心的人格心理的喚醒,而已經算得上是一種神秘的宗教體驗(儘管遊戲中可以用桐條科技解釋召喚器的機理)了,再多的細節刻畫就此而論都是跑題的。
所以在劇情前中期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槍型召喚器都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存在:要麼把它當成“扣扣扳機蹦著玩”的象徵性掛件,要麼把它當成一種大象無形的神蹟。直到人格面具的二覺,這種情況才有了改觀:它是召喚者獨屬記憶的寄託(每次順平二覺神通法看到千鳥逝去的背影我都鼻子一酸吶╥﹏╥),也見證了SEES隊員間不斷的磨合。
這樣的話,以開端作為中途的人格面具覺醒,就與整部宗教寓言產生了實質的分歧。儘管SEES仍然在按照著寓言已經安排好的秩序,催生著從愚者開始發展的死神,但他們同時也在寓言之外獲取了“生活的領會(verstehen)”。這種領會的標誌在於由十年前事故引發的(羞恥)責任的消失。換言之,造成羞恥的目光實際上已經(往往是突然地)消失了:千鳥耗盡了自己的生命復活愛人、由加莉父親未被篡改的生前錄像第一次揭秘、風花的同班同學夏紀即將轉校、天田的殺母仇人在影時間為天田犧牲……
這些關乎生、死、離、別的沉痛領會,將SEES的每位成員推向兩難的歧路:一邊是對新的(可以作為替代的)責任天職的頓悟,另一邊是(以某種方式)接受目光消失之後的月下世界。前者已如上文所述構成了宗教寓言所揭示的選擇。後者則是決定這些(從中間開始的)人物個性刻畫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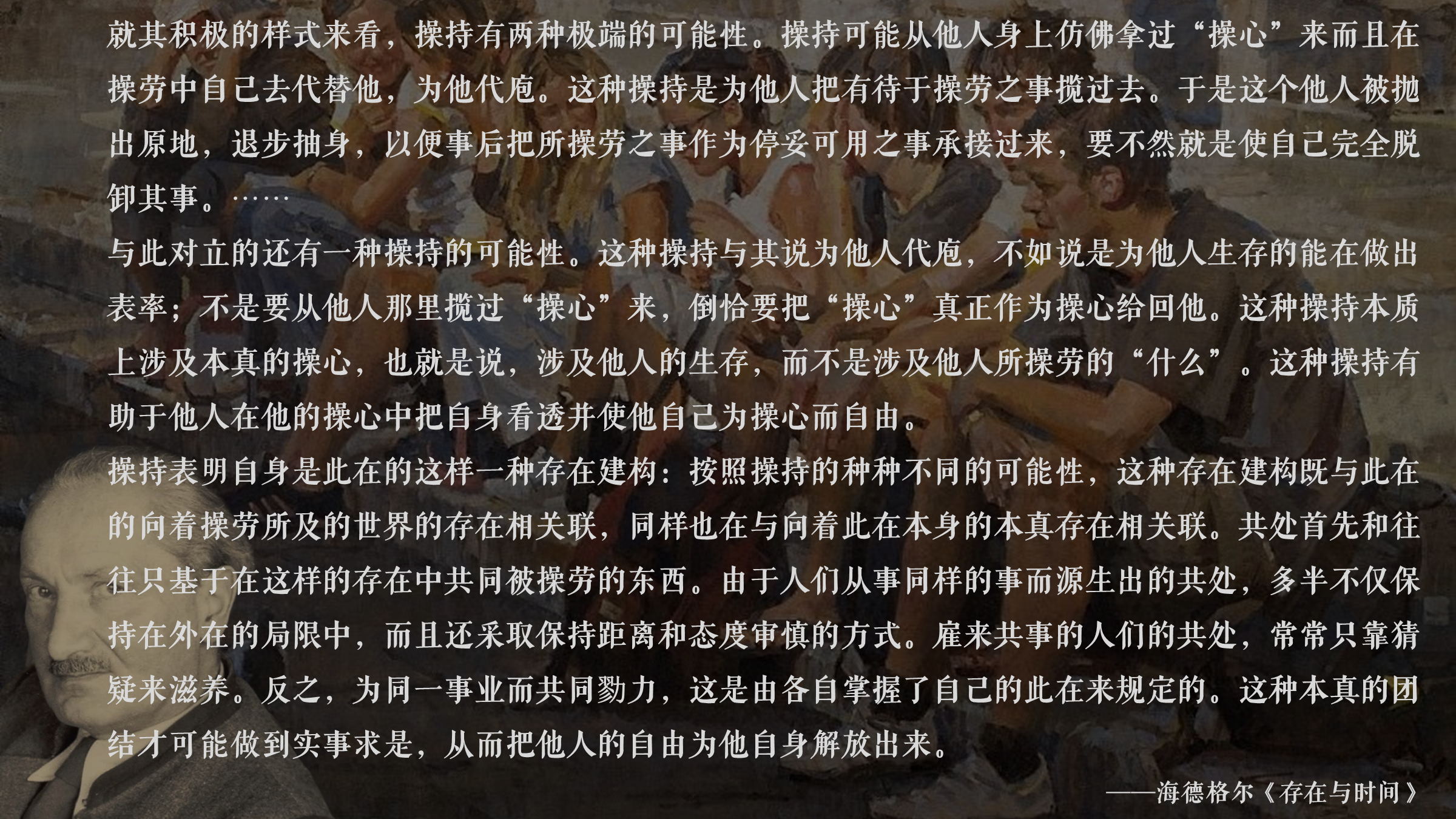
(作為一個出色的現象學家,)海德格爾精確地描述出了此在與他人照面共處的情形。操持(Fürsorge,也譯為“煩神”“憂神”,詞根Sorge相應地譯為“操心”或“煩”)的兩種極端形式:代庖控制(einspringend-beherrschende)與率先解放(vorspringend-befreiende,也譯作放手解放),一個是指完全地為他人所是所煩(操心)的東西而操持(憂神),一個是指完全地為他人自身而操持(憂神)。“平均的日常相處”則是極端形式的可能性混合。更具體地說,是一種有距離(而非親密無間)的共在,稱為“共處同在”(Miteinandersein,也譯為“相互共在”“雜然共在”)。海德格爾認為,真正的團結需要的不是操持(乃至搶奪)他人煩憂的“代勞”,而是協助他人為自身負起責任而獲得他自己的自由。
那麼,羞恥目光的消失就是這樣的一個契機:究竟將要把他人的志業(以某種方式)傳承過來,還是要尊重目光的自由但又把他人的關切交還給對方?荒垣之死對於SEES來說是一個危機。這不僅僅是因為他本身就決定了SEES眾多成員的去留,還因為在人設上,荒垣是一個外冷內熱的十足暖男,玩家更能從支線任務的點點滴滴中感受到他對生活的熱愛與其人生經歷的沉重。他的死將激發我們對這樣一位(從各種意義上來說的)好人的(本能式的)同情。這也就是在暗示:不(化悲傷為力量地)繼續前行,我們難道對得起他嗎?還是說,我們已經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過?
這種“對不起”可能是基督教式的罪責(guilt)邏輯,但不會是SEES團結起來的真正需要。如果擋槍的是順平,我們還會有如此強烈的觸動嗎?進一步說,為什麼我們會對順平如此幸災樂禍?為此,SEES或許可以選擇以所謂的“冷酷的熱情”應對危機,但如果天田乾的重新歸隊只不過是下一輪的贖罪、如果每一位成員面臨兩難歧路時都選擇承受新的天職,SEES終究還是一群烏合之眾的雜糅。為了更好地探索塔爾塔羅斯而投以的關心並非真正的關心,或者說,淡漠的、虛偽的“溫馨大家庭”,以及現實中每個人所處的稱之為“公司”的囚籠,儘管降下了一條神聖使命、或曰“企業文化”,但也從根本上剝奪了我們自己對自己負責的責任。
於是,同P5收容無家可歸者逐漸升溫的怪盜團不同,SEES雖然同樣有著成員的出走又歸隊,但這一方面證成了宗教寓言的必然性與絕對性,另一方面又瓦解了現成隊伍的集置:沒有一個絕對穩固的隊伍,成員的離開不意味著士氣的消散、成員的加入(或迴歸)也不意味著共同體的凝聚。在宗教寓言與人格刻畫的較量之中,SEES這條修修又補補的忒修斯之船(倪克斯討伐隊),究竟將駛向何處呢?
4.飛往月上世界:怎樣才算“偉大的封印”
說來也奇怪,受人盛讚的太陽社群(神木秋成),一方面被認為劇情表達的主題最契合P3主線(暫且假設生死宿命就是P3的主題),另一方面又被認為具有力透紙背的生活真實感。但其實,神木秋成同結城理的對話方式,很難稱得上接近生活。至少在COOP前期,他並不相信結城理(還有其他人)能夠理解他的感受。再後來,他開始創作那篇故事。一來他還是會偶爾透露出自己承受病痛時所產生的即時情緒,但很快他就鄭重其事地調整狀態,專心向結城理彙報自己的創作進度。
相比之下,一種更為自然的聊天方式,是把生活的苦悶(或歡樂)融入經歷的講述之中(組織成聊天所需的故事):P3社群最慣用的套路,就是在COOP不斷加深的過程中,讓對方出於一些契機,順便把自己的難言之隱袒露出來。但和五味雜陳的袒露不同,神木秋成在自己的感受與故事創作之間劃了一條更嚴格的界線。也可以說,他從一開始就是袒胸露乳的。也因此,象徵了他對“生命的意義”全部理解和過往人生總結的那篇故事,更顯得神聖和純粹。
或許這才是太陽社群與P3主線最相似(契合)的一點:通過承認情緒(人格刻畫)與故事(宗教寓言)之間的水火不容(自然地來說根本不是這樣的),突顯轉瞬即逝的絢麗交融(這就是所謂的物哀美學嗎(⇀‸↼‶))。
再說到太陽社群的結局:神木秋成寫完故事,羽化離去,兩者在邏輯上並沒有先後,而是上述兩條線索最終的(也是最蔚為壯觀的)重合點。這一點對我們理解P3的結局相當重要。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P3最後超越了對某部著名動畫致敬的爆種展開,確實很容易讓人把結城理放在一個很高的位置上。但反其道而行之的解讀,也並無大礙,甚至使得整個結局沒有那麼唐突(至少不用說是“為了這碟醋包的這頓餃子”(─.─||))。
埃癸斯的漸通人性、望月綾時的友情/死亡宣告,當然可以視為結城理最後抉擇的醞釀。這其中的邏輯是,十年前結城理只是個一般路過月光大橋的小朋友,但出於某些機緣巧合,他承受了遠超他自身身世的命運之重,甚至託付著全人類的靈魂。他將隻身飛向月球,做擎舉月下世界的阿特拉斯(Atlas)。

這樣的話,3月5日的畢業典禮,就是為這位垂死英雄安排的謝幕。在眾星拱月的襯托之下,一個閃耀而完整的人物弧光似乎得以呈現。然而,我更願意將結城理看作是與埃癸斯、望月綾時三位一體的人物。
第一個區別在於,日曆推進的自然時序並沒有揭示結城理由生入死的垂暮始終。結城理的命運在望月綾時誕生的同時也就宣告了:他將完全成為宗教寓言的最後一環,即無論如何,末日終將來臨,由死神宣告,同時由彌賽亞封印。
要知道,望月綾時在12月份為SEES提供的兩個選擇都沒有否定寓言的必然性,只是建議說遺忘記憶(徹底陷入矇昧)安樂地等待滅世;另一方面,望月綾時對SEES的其他成員是在宣佈末日的到來,但對(死神社群MAX的)結城理來說就是在宣佈末日的解決辦法。
也就是說,結城理的犧牲並不會決定寓言的偏離或成真。真實的情況是,做出最後抉擇的是玩家,而不是結城理。儘管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是由我們玩家來扮演結城理,但在主線劇情的末期,兩者實際上已經分離了:結城理飛往月上世界,和神木秋成一樣同時地為自己的生命(故事)和寓言(故事)收尾;我們(玩家)則從月上世界重返,恢復自然時序以延續由生入死的垂死體驗。 我想強調的是,直到結局,就角色本身而言,結城理依舊沒有太強的特殊性:和SEES的其他成員一樣,他還是一個邊緣人物,一樣受到宗教寓言與人格面具兩方面的掣肘與框限。結城理的結局是封印,但就其本身來說,結城理自己絕不會使得這封印變得偉大。
有了這個前提的話,第二個區別就在於,結城理、埃癸斯和望月綾時是本質上相同,而非互補反襯的三者。我並不是指性格(或者說人設)的相同(也無意去仔細剖析他們的性格特徵),而是指三者在P3的主線劇情中處於相同的位置。他們都對自己的大阿爾卡納牌以堪稱可怕的態度宣誓效忠,同時又以絕對非人的姿態(而不是有性格缺陷的凡人)來表達他們嘗試理解人性的渴望。我們(玩家)實際上難以捉摸三者對死亡(或降生)的具體態度:當宿命到來時,他們突然地現身(或消失),讓人不明就裡。但(矛盾的是)我們也不可能忽視他們(像人一樣)尋找生命答案的熱忱。這種介於冷酷與熱情之間的羞恥態度,可以稱之為挽留。
總而言之,太陽社群的確可以稱為是P3主旨的濃縮,這就是我所謂的“挽留”,即因(對方)去意已決的暗自神傷。誰要離我而去?為何離去?我為何獨自傷悲?這裡的“我”是指玩家本身。3月5日的天台枕別製造了一個假象:好像結城理和玩家依舊是尚未分離的一體,埃癸斯(還有SEES的其他同伴)正在挽留快要閉眼的結城理。
然而,我的理解恰恰相反,埃癸斯還是結城理都沒有特殊性,真正特殊的只有玩家自己。在結城理完成自己的寓言使命以後,他就從自身中脫胎出我們。(我們)玩家不再是結城理,而是獨異的挽留者。
P3的整個主線都充斥著彆扭的、相悖的宗教寓言與人格刻畫之間的矛盾(我也並不認為它逐漸地得到了克服),但唯獨在結局的這一刻出現了轉瞬即逝的重合。這其中並沒有什麼奇蹟,而是因為玩家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去挽留、去目送SEES的每位成員(包括隊長結城理)、那些社群角色(3月4日的後日談)的離別。只有這樣,情感衝動的強烈抒發才是沒有中介的。我們(玩家)不需要去感受、去揣摩、去想象雙方的告別,因為我們自己就是這惜別依依的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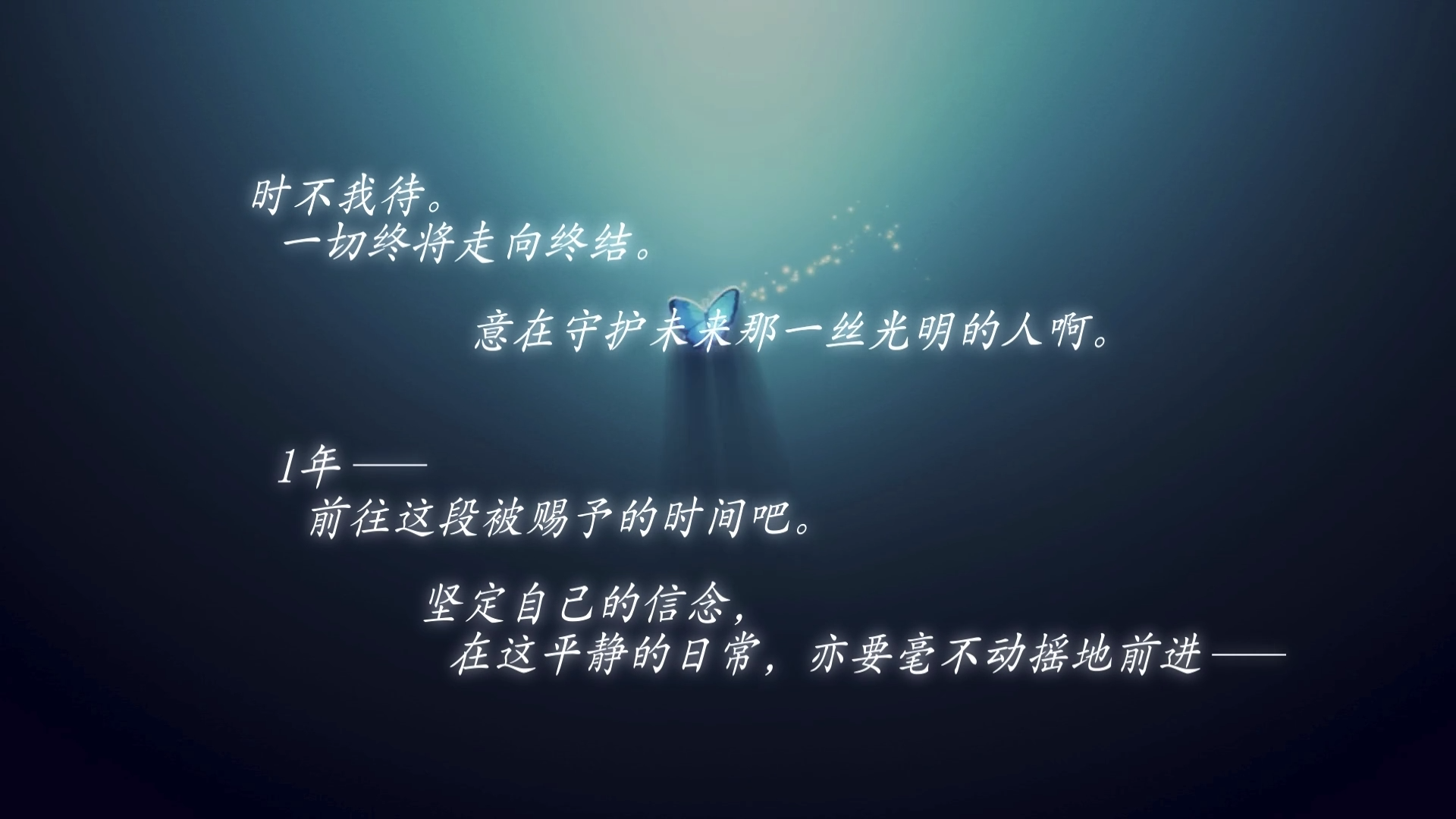
那麼,開場動畫的這段文字並不僅僅是JRPG開頭鋪陳的慣用定番,而恰恰暗含了模糊指代下的詭計。它同時表明了結城理不可能擺脫的寓言式宿命以及我們玩家挽留的剎那,只不過要直到兩者徹底撕裂之時,這一詭計才將揭曉。
也因此,影時間下的記憶是否留存,根本不是什麼重要的問題。就算記憶真的消失不見,我們還是會滿懷熱淚地挽留。P3主線劇情的最後一個選項分支:閉上眼還是沉默,並不是結城理在挽留埃癸斯,而是我們在挽留SEES的各位,挽留這些如春天般易逝的記憶,不是嗎?生命的答案也許無處尋找,但生命的偉大業已親眼見證。現在,閉上眼睛好好休息一下吧。

5.尾巴
正月事情實在太多,這篇雜談是在老家、火車、機場、酒店等七七八八的環境下完成的,外加一點深夜昏昏欲睡的改了又刪、刪了又改。雖然更簡陋、更淺嘗輒止、更零碎、更乏味,但好在還是一點一點擠完了;也好在自己沒有半途而廢,趕在通關的激情和感動消散之前,把它寫完、分享了出來,謹留作難忘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