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結局的意義在於通過作者與玩家的同質化,故事本身從二者手中獨立出來。對於故事裡的時間,作者並不比玩家知道的更多,敘述中的故事因作者與玩家身份的毀滅而結束,真正的故事卻因此得到新生。這便是最重要的啟示——隨著作者和敘述的毀滅,玩家將要面對真正的故事。

如果你完整地遊玩了《尼爾·機械紀元》,你的屏幕最終會停留在一切開始的地方:屏幕的正中是“NieR:Automata”,i上面的點呈現為齒輪的形狀,e和A中間的一橫都是斜的,這兩個小設計很容易讓你聯想到過去幾十個小時裡發生在工業廢墟里的故事。標題的背景彷彿是一片黑夜裡的星空,在畫面右下的高亮部分裡,你看到一把刀斜插入水裡,刀柄上掛著眼罩。只有new game和license,沒有load game,你玩過這個遊戲唯一的證明就是成就室裡的獎盃,這個獎盃的名字似乎取決於你的平臺。我在這個遊戲上花了近36個小時,換了一個叫做“the mind that emerged”的成就。
或許每一個衝著《尼爾·機械紀元》鼎鼎大名前來體驗的玩家都多少被劇透過,但我在屏幕回到開始的畫面時還是無法迅速平復。如果這部作品將會被遊戲史所記住,那一定不會是因為它愚蠢的銷售策略和慘白的畫面調色,可能也不會是因為出色的配樂以及2B的眼罩和大腿。
至少在我看來,《機械紀元》有三個具有開創性並且引人深思的地方:
首先是開放世界裡攝像機與遊戲玩法的交互。對於開放世界應當如何吸引玩家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了許多創意,例如散落在世界地圖各地的收集品、謎題和隨機事件;例如設計線索複雜交錯、碎片化的支線劇情,例如增加怪物種類、提高怪物難度,使玩家在探索時學習戰鬥;例如每個月丟一個新角色到up卡池裡;又例如將釣魚、烤肉等融入開放世界,像《巫師3》裡的昆特牌,玩家可以在世界各地收集卡牌並且和各種NPC打牌。雖然總的來說,《機械紀元》的開放世界和整個動作系統得設計並不那麼亮眼,但《機械紀元》通過簡單的固定攝像機,在開放世界裡加入了橫版動作、彈幕等元素,戰鬥方式的變化為玩家提供了多樣的戰鬥體驗。
這種攝像機與玩法的簡單互動設計具有鮮明的日系風格,且還有許多可供挖掘的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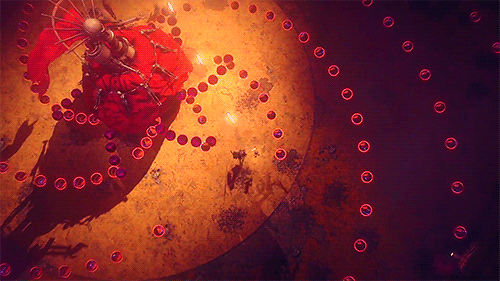
其次是《機械紀元》中的元遊戲元素,往常在提到metagame時,玩家想到的通常是《心跳文學部》或者《史丹利寓言》這類勝於劇情表現而疏於遊戲樂趣的小眾作品, 《機械紀元》則將元遊戲元素融入了一部大作,不僅是在最後一個著名的E結局裡,在其他各處也有所體現,比如通過芯片改變遊戲HUD等。當然,《機械紀元》無法像《心跳文學部》一樣讓玩家在文件層面進行編輯,將metagame貫徹到底,但它依然提供了一個將metagame與大型RPG相結合的巧妙設計。
最後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E結局了。
想必每個遊戲愛好者都對其有所耳聞,《機械紀元》探索了單機遊戲與網絡遊戲之間界限,用幾十個小時的體驗和共情建立起了陌生玩家之間的羈絆。我不知道小島秀夫是否也曾受到了E結局的啟發,在單機遊戲的聯機元素上進一步思考開發了《死亡擱淺》,這不需要什麼技術上的更新迭代,需要的是對遊戲本身理念的深入思考。可以看到,優秀的製作人們將關注點共同集中在了通過多個孤立體驗的孤獨感造成玩家的共情與深度聯合。如果若干年後這種居間的遊戲形態發展成了一種新的遊戲設計類型,《機械紀元》或許將會作為這種設計思想的先驅之一被人記住。
然而,這些並不是本文的主題,或者不僅僅是本文的主題,畢竟《機械紀元》最重要的啟示之一就是形式與內容的合一。長久以來,人們喜歡在文學作品中尋找作者,人們往往認為一部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無論其有幾分虛構幾分真實,都體現作者的觀點或情感。作者真實得呈現故事,而隱藏自己供讀者猜測——其極端的形式就是自傳或回憶錄,在這種形式中故事與作者合一,並將這種衝突推到了極致,以至於如今人們提到戈爾巴喬夫或葉利欽等富有爭議的名人自傳時往往會有這樣矛盾的感覺:這部自傳是他為自己言行的辯護,但又有誰能比他自己更清楚自己的過往呢?
作者在其中的突出地位,可能跟文學本身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文學為讀者呈現的是已經完成的故事和人物,也就很可能是單向的,雖然在此之外我們也看到了將作者與讀者呈現在故事中的文學,例如布托爾的《變》、卡爾維諾的《寒冬夜行人》等等。遊戲作為形式為作者與讀者(此刻應該叫做玩家)的關係展現了新的可能。
在一些遊戲裡,例如在洛聖都,選擇做一個好市民還是一個罪犯完全取決於玩家自己,R星或許會在玩法或機制上鼓勵人們採取行動,但本質上講它並不會關心玩家到底做出了怎樣的善惡選擇,並因此給予玩家肯定或批判,一切取決於屏幕背後的人;而在更多遊戲裡,玩家只是跟著主人公看完作者已經寫好的故事,這與傳統文學沒有區別,但顯然《尼爾·機械紀元》就是那少數做出了嘗試因而值得被認真對待的遊戲之一。
在整部《機械紀元》裡,玩家在幾處能夠看到遊戲角色彷彿打破“第四面牆”與玩家直接對話,讓人印象深刻的,例如一是在反抗軍基地裡的兩個戴著橫尾頭套的抵抗軍,在與他們對話的時候玩家可以看到諸如“遊戲太難了怎麼辦”、“暈3D怎麼辦”之類的對話選項,兩個NPC會對這類元問題為玩家提供建議,二是在E結局的結尾,兩個pod與玩家進行了直接對話,詢問玩家是否願意接受其他玩家的幫助和幫助其他玩家。除此之外,整個故事都在舞臺上呈現,角色不與玩家直接產生交集。因此,關於玩家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在整個故事裡玩家到底是否在場?
我們當然可以認為玩家的出場是設計的疏忽使然,或者只是作者靈光一現的彩蛋。然而,考慮到pod與玩家的交流構成了整個遊戲最重要的一部分,最好還是將玩家的在場認為是遊戲的一部分。實際上,整個遊戲都透露著一種刻意否定玩家在場的氣息。例如遊戲的HUD顯示,玩家可以通過為角色安裝不同的芯片改變遊戲內的顯示內容,也有角色視覺系統受到干擾時整個畫面表現出現顏色失真、花屏等,可以說是一個巧妙的meta設計。然而如果玩家在場,就意味著玩家並不是人造人,人造人的視覺系統崩壞,顯示失常的應該是遊戲裡角色的感官,這樣遊戲必須給出玩家如何與角色共享視覺的說明。
在一個對攝像機運用出色的遊戲裡,作者不應當忽視,如果想要玩家徹底地扮演自己所控制的人造人,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將第一人稱貫徹到底,在視覺上採取第一人稱,在故事敘事上將視角固定在一個主角身上,由他的故事開始,到他的故事結束。然而《尼爾》的作法是在視覺上採取第三人稱,在敘事上,第一、二週目保持了唯一主角的視角,第三、四周目則頻繁得轉換主角,每一次轉換主角時都有pod出場,不安得喚醒沉睡在舞臺上的玩家:你要選擇9S還是A2?

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深入遊戲的文本和結構。整個遊戲中有兩種對話,一種是沒有對話者名稱的對話,是遊戲向玩家提出的對話;另一種是有對話者名稱的對話,是遊戲角色之間或角色向玩家提出的對話。而整個故事裡能夠與玩家直接對話的,除了橫尾頭、pod,還有一個不明人物,在E結局中,它提出選項:“確定要允許來自輔助機的停止請求嗎?”在其他地方,對話者都會在對話框中提示姓名,而在這個選項裡,對話的提出者被表明為“???”,是全遊戲中唯一以此面目出現的對話者。
這段對話多少有些突兀,因為在這個選項之前,對話都是以pod的彙報和請求進行的。而在這個選項之後,對話在一種奇怪的氛圍下進行,看似是兩個pod之間進行交流,但實際上全是說給玩家看的。因此,這個強行改變了對話的人必然是一個pod也無法控制的機制(後文稱為“規則被底層系統保護”,必須要指出的是,雖然我對簡中的漢化組十分感激,但這一處被錯譯成了“低等系統”),顯然處在這一層的只能是玩家本人和遊戲作者,這一點隨後被最後的彈幕關卡所證實:玩家需要面對製作組名單。
至此,我們來到了遊戲故事的第二層,在此玩家將戰勝作為角色的作者,然而玩家戰勝作為角色的作者幾乎是被作為故事創造者的作者所註定的。在幫助人造人們保留了數據後,最後一段動畫演出裡,pod也無法否認,即使人造人們重生,也不一定能夠逃過被設定好的命運:9S會再次接近關於人類禁忌的真相,而2E再次揮刀處死9S。這段動畫演出標誌著被遊戲所敘述的故事結束,雖然它沒有講完結局:對於一個開放式結局,作者與玩家是同樣無知的。這便是開放式結局的意義,它完成了作者與玩家的同質化,並使故事本身從二者手中獨立出來。對於故事裡的未來,作者並不比玩家知道的更多,故事因作者與玩家身份的毀滅而結束。留給玩家的是整個遊戲結構中的最後一個層次,玩家迎來了真正的故事。
在這裡,重要的不是玩家回答作者的問題,而是玩家要直接面對其他玩家。最後的選擇就是是否要在別的玩家面前將這個不確定的未來繼續維護下去。這段動畫被安排在刪檔選擇之前是給玩家的重要提示:玩家無法讓舞臺上的故事圓滿,而是隻能讓它原樣繼續。
這樣,《機械紀元》呈現出了一種三重結構,而我更願意將其視為三個人與其造物的故事:外星人和機械生命的故事,人類和人造人的故事,以及遊戲作者與玩家的故事。
機械生物在殺死自己的造主外星人後向人類演進,為保衛人類而生的人造人被下達禁止探索人性的禁令後要獨自面對人類已經滅亡的事實,而玩家在打敗了自己的創造者和阻礙者——遊戲設計團隊之後,最終要面對其他的玩家。但不同於那個精神分析者喜愛的詞語,這不是“弒父”的故事,而是弒父之後的故事。在《機械紀元》裡,我們看到了各種各樣的形象,低級機械生命口中喃喃那些從人類處聽來的語詞卻不知其意,高級機械生命在臨死前終於體會到存亡鬥爭的意義,人造人2B壓抑內心的溫柔含淚履行處刑的使命,人造人9S則被真相喚醒了人性更深處的禁忌,仇恨與絕望——我個人不太喜歡認為結局裡9S被病毒感染,或者不如說我不喜歡將其認為是病毒的方式,這是一個被生物學式簡化了的福柯主題,玩家被不斷提示人造人被禁止擁有人類完整的感情,而病毒則是將某些感情的解禁與放大。就此而言,“為了人類的榮光”與憎恨相同。9S最終克服了忠誠和虛偽的希望,但他並沒有最終解放自己,而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以及A2、21O、帕斯卡、抵抗軍等許多支線任務和配角。
還有最後的主角,玩家自己。對其他玩家付出善意並不需要多少決心,真正的問題在於自己付出了決心所維繫的那個未被講述的未來里人造人們可能也未被從無盡的輪迴裡拯救出來,如此自己的善意是否幫助維持了一個更大的陰謀,就像帕斯卡一樣好心做了壞事。這些故事都講述了不完滿的人自我解放的過程,亞當從好戰中解放,帕斯卡從保護的義務中解放,9S從禁忌中解放,A2從仇恨中解放,而2B,每一次執行處決的人,最終為了保護處決對象而死。
站在所有故事的盡頭的,是一個並未揹負遊戲設定因而超越了每一個角色的、真正的人,他將以人的方式去面對這一疑問,並非是否奉獻,而是我們是否已完全明白自己的奉獻,進而,是否通過這種奉獻到達了從他對這個故事、他對其他玩家所揹負的聯結中解放的盡頭?
或許相信“all to be nice”是一個不錯的答案,但聽從答案並不是人解放的方式,這也正是A2和9S,兩個得知真相的人以戰鬥迎來各自結局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