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原創電臺節目《電塔守靈夜》的文字稿。如果想看視頻,請在B站搜索“電塔守靈夜”。
人類在建起城邦之前,只能無奈面對充滿危險的大自然。野生動物和自然災害威脅著人類的安全,人類試圖理解尚且無法理解的災害、動物、疾病和厄運,於是有了神話。可以說,神話故事中封存著人類集體意識深處的原型,其中也包括恐懼的原型。
例如民俗故事中常常會有“不能進入的區域”。主人公原本的日常生活很安穩,看護人一再告誡“不可以去下面的房間”,主人公某天按捺不住好奇,踏入了禁忌之地,窺見了恐怖的秘密,顛覆了日常生活。安穩被打破了,理性能認知的世界中出現了巨大的空洞。
我認為,這種“不能進入的區域”源頭是孩提時代父母的告誡。孩子從母親腹中誕生,在母親的懷中獲得安全,以母親為“據點”去周圍的世界冒險。母親會鼓勵孩子外出探險,但也會給孩子設下規則,“絕對不可以靠近xxx”。原本看起來沒什麼不同的日常景觀,在母親的厲聲告誡中搖身一變,成了恐怖的景觀。平靜黑暗的水塘下隱藏著什麼呢?母親說的話就像魔法,激起了孩子的想象力,也激發了恐懼,而這種恐懼一代傳一代,最終藉由民俗故事這一琥珀,永遠地封存了起來。
而封存在琥珀中的恐怖,也分為不同的類型。如今比較流行的恐怖,莫過於克蘇魯了。
我們常常能在跟克蘇魯無關的視頻裡看到有人刷克蘇魯。誠然,刷彈幕的人很可能只是聽說過克蘇魯,對克蘇魯的印象是“大觸手怪物”“怪異的東西”,這種不可名狀的產物在人們的腦海中留下了輪廓不太明晰,但卻深刻的印象。他們無法說清楚洛夫克拉夫特筆下的宇宙恐怖到底與其他的恐怖有何不同,只記得那種模糊的恐怖感,於是看到有宇宙、哥特、觸手怪物等關鍵詞出現的地方,就自然聯想到了克蘇魯。
未曾見過全面,卻被迷得神魂顛倒,在任何帶有影子的地方都會想到克蘇魯……神秘的洛氏恐怖到底有什麼魅力?
馬克·費舍在他的著作《怪異與陰森》中提出了“怪異”(weird) 和“陰森”(eerie) 兩個概念,並且將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劃入了“怪異”的範疇。何為“怪異”?怪異是“超出我們理智認知的東西”,也是“不該在這裡”的東西。怪異是無所歸屬之物,是讓理性認知的地圖出現巨大空洞的罪魁禍首。那麼何為“陰森”?陰森與施動性有關。不該在場的東西存在,該在場的東西卻不存在,陰森感就會隨之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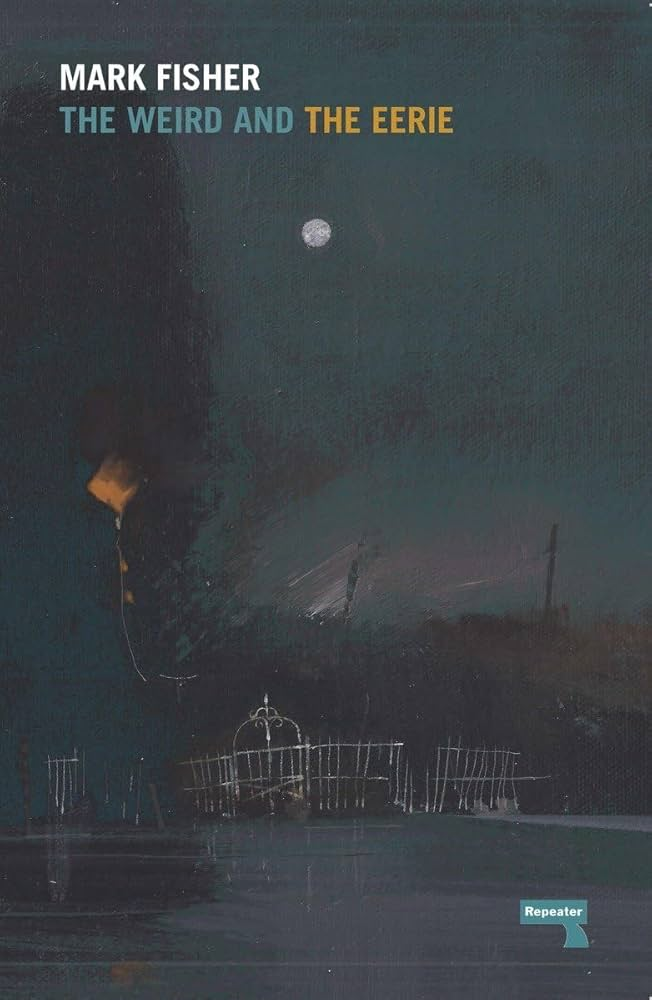
“怪異”與“陰森”的概念看起來似乎還有些相似,都能讓我們脫離平靜的日常,感受到某種異常。這兩者有什麼比較具體的區別麼?
陰森與怪異的不同在於前者會引起“懸念”,在我們認識到背後的施動者之後,陰森的感覺也隨之消失了。怪異則不然,怪異是超出理性認知之物。那麼,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為何屬於“怪異”也就顯而易見了。洛夫克拉夫特常常將故事設置在我們已知的世界裡,又在裡面引出另一個不可知的世界以及不可知之物對這個世界的侵入,來自外部的恐怖侵蝕主人公的認知,最終導致主人公發狂。他的故事幾乎都遵循這樣的套路,不存在什麼懸念,純粹靠怪異來吸引人。
那麼除了洛夫克拉夫特之外,還有什麼作品稱得上“怪異”呢?雖然在這裡很想說大衛·林奇……這位被稱為鬼才的導演留下了不少傳世之作,最出名的有《內陸帝國》《穆赫蘭道》,每一部都善用了夢境的嵌套,用各種意象反覆呈現出“怪異”這個概念本身,像《雙峰》就是其中翹楚……不過既然是亞文化大冰的小屋,那還是上點私房菜吧。
《Who's Lila?》這款遊戲稱得上是對大衛·林奇酣暢淋漓的模仿和致敬。大衛·林奇的作品都是影視作品,而《萊拉》是電子遊戲,開發巧妙利用了電子遊戲的互動性,用了更多的方式去呈現“怪異”這一主題。
遊戲一開始,主人公就對著屏幕獨白,說自己不擅長做表情,每天出門之前都得去對著鏡子練習一下,由此牽出遊戲最關鍵的捏表情決定劇情走向玩法。後來故事告訴我們,主人公威廉認識的女同學譚雅·肯尼迪失蹤了,她的尋人啟事海報貼得到處都是。威廉來到學校後,又從他人口中得知譚雅的男友在到處找自己,而自己似乎也與這一切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不是一起普通的失蹤案……光看這個介紹,是不是有點《雙峰》的感覺?不管是劇情展開還是遊戲玩法,都透露出十足的“怪異”。
大衛·林奇的《穆赫蘭道》和《內陸帝國》都在不斷打破夢與現實的界限,甚至作品本身就是個沒有謎底的謎團。《萊拉》作為大衛·林奇作品的出色模仿者,也呈現出這樣的特質。不管是遊戲過場動畫的摩斯密電碼,還是詢問威廉輪得到的回答,都在不斷重複“萊拉就是萊拉是誰這個謎本身”。怪異的特徵之一便是“越是試圖理解,就越是無法理解”,越是解讀就越是迷茫,因為劇情和設定都不是重點,作品本身即是一座龐大的迷宮,是兔子洞一般的安那其建築。《萊拉》就像重複著自己的謎,一個嵌套式的結構,一齣戲中戲,一場或者好幾場夢,一個幕簾套著另一個幕簾。可是,這個夢是誰做的呢?這場戲又是誰導的呢?拉開幕簾的究竟是誰?這幕簾後面到底有什麼?

大衛·林奇作品中一個重要的視覺元素就是幕簾,而《萊拉》裡也有幕簾出現。玩家在天台被邁克推下去之後,就會在醫院醒來,走過一層又一層,目睹自己跟萊拉對話的記憶碎片,最後來到一個幕簾面前。旁白說這幕簾無風自動,讓人心中湧起一股懷舊之感。穿過幕簾,玩家的視角一下從第三人稱切換到了第一人稱。用WSAD操作,四處探索,就會看到兩臺幻燈機在放著不同的人格膠片。
幕簾在這裡就跟《雙峰》中紅房間裡的幕簾一樣,隔斷了這邊的世界和外部的世界。玩家穿過幕簾,就像走出了現實世界,進入了那個神秘的外部世界,在這裡,遊戲沒有用上meta要素,卻已經完成了“在遊戲中打破遊戲的第四面牆”。
至於迷宮,除了遊戲本身呈現出的迷宮感外,遊戲中也多次出現迷宮和螺旋狀的結構。比如學校裡“走進去就不知道通往哪裡”的門,還有必須聽音辨位,隨機刷新的鍋爐房,以及鍋爐房盡頭的那個螺旋狀的樓梯……《萊拉》本身宛如無數螺旋和謎組成的巨大的結構,不管是放大還是縮小,它都在向人們展示著“謎”本身。多重夢境的拼接,另一世界對這一側世界的侵入,即是“怪異”之美。
說到侵入,最近玩的另一款遊戲也正好是這個主題。它或許符合怪異的定義,但給我帶來更多的是陰森的感覺,所以我把它分在了“陰森”這一列。
《This is not your house》是一款短篇像素視覺小說,共有10個結局。故事一開始,主人公羅傑剛開車回到家,遊戲就通過第三人稱的描寫,帶出一種濃濃的焦慮和陰森的氛圍。羅傑總擔心會有誰埋伏在附近,他懷揣不安走到家門口,把鑰匙插入熟悉的鎖孔,卻怎麼也擰不動。這時,家裡傳出了奇怪的聲響,他抬頭一看,發現自己家裡竟然有個古怪的陌生女人,聲稱屋子是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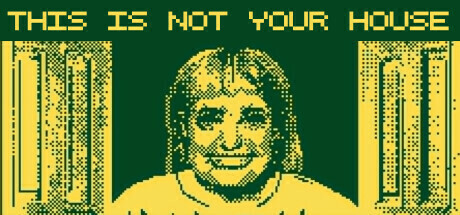
玩家在這裡可以選擇是否讓羅傑奪回房子。如果選擇奪回房子,根據後續選項,可能觸發兩個結局:一個是被古怪女人殺死,另一個是成功奪回房子。後者或許還算得上好結局。羅傑奪回房子後拼命打掃,想把一切恢復原狀,卻發現屋子裡到處都是那女人留下的痕跡,自己的東西都不在原來的位置了,而且越打掃,發現的古怪就越多,他不由得捫心自問,自己真的是這家的主人嗎?那女人在這裡住了多久?羅傑想起那女人消失前說的“誰在房子裡房子就是誰的”,他害怕自己的房子再次落入他人之手,嚇得能不出門就不出門,有事都找別人辦,就算出去也不敢離開太久。
玩家如果在之前選擇不讓羅傑奪回房子,那麼羅傑的車和身上的一切都會被這個女人奪走,他只能顫顫巍巍地跑去找人求助,想辦法奪回房子。後續的結局也都差不多,羅傑哪怕奪回了房子,也是建立在殺死那女人的基礎之上,他會遭到逮捕,會被打成殺人犯,任由他如何辯解“我只是為了奪回屬於自己的東西”也沒人聽
馬克·費舍說,陰森的條件之一就是讓人脫離當前的依附。依附是讓主體獲得安全感的依賴對象,它在場時我們會感到安全,不在場時則會焦慮。而家毫無疑問就是我們獲得安全感的來源。我們為何會將一個地方稱為家?那必然是我們熟悉的,也是屬於我們的地方。外部世界很危險,可是家是安全的。遊戲偏偏就在家上做文章。先是細緻描寫插入熟悉的鎖孔卻擰不動鑰匙,再是看到自己熟悉的家落入陌生人之手。遊戲到結局也沒有說明那女人到底是什麼,她就這麼忽然地出現,奪走了羅傑所有的依附,以及他的自我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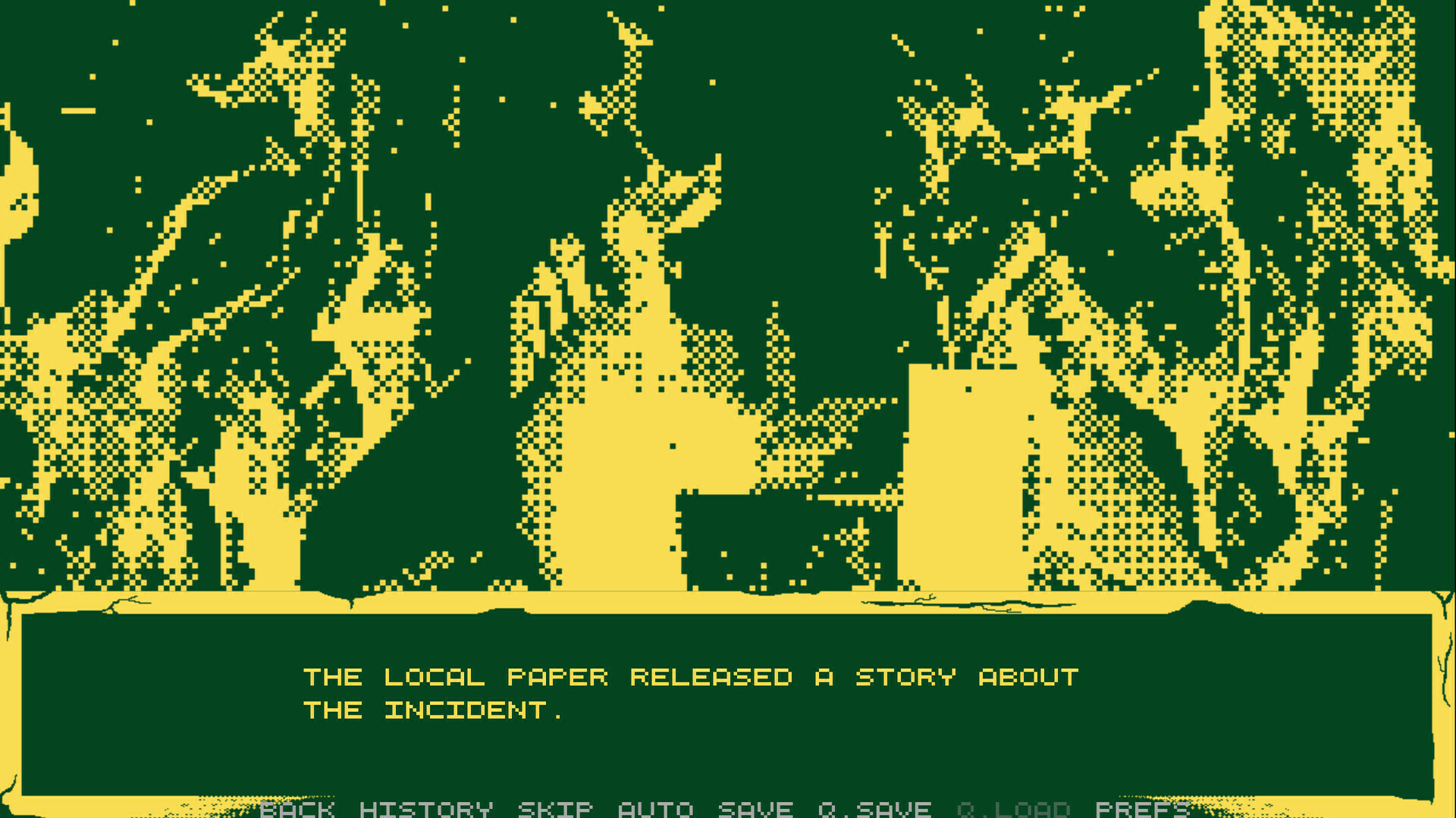
原本日常的一切被忽然地剝離了日常的屬性,變成了陌生之物。我們獲得了另一個陰森的視角,從外部重新窺探習以為常的內部世界:這裡的所有權概念是否是社會捏造的?如果是的話,那還有什麼是可以相信的?腳下還有堅實的地面嗎?我們究竟可以相信什麼?到底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應該存在的安全感,社會規則不存在了,不該存在的超自然現象,否定已有法則的東西卻大大方方地存在。這裡沒有幕簾,沒有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但設定和劇情本身通過抽走玩家熟知的東西,從內部崩壞,翻轉內外,讓我們從內部轉向外部。這種翻轉帶來的陰森感揮之不去……
本來還想再舉幾個例子,但馬克·費舍對“怪異”和“陰森”的分類實在是不太嚴謹,有太多東西可以既是怪異又是陰森了。就連馬克·費捨本人都說,像宿命啊命運一類的,都可以涉及到這兩者。 比如剛剛提到的那款遊戲,那超自然的存在本身是人類理性無法認知的東西,應當屬於怪異,可是抽走依附,讓不該在場的東西存在,又給人帶來了陰森的感覺。有時候,很多作品不一定能粗暴地分成這兩類,重點在於他對這兩個概念的探討。
“怪異”和“陰森”這兩個概念的討論和分離又是由何而起呢?這就不得不提到弗洛伊德之前寫過的暗怖這一概念了。
弗洛伊德1919年發表過一篇文章,提出了暗怖這個概念,我們有時也說是非家幻覺,也就是在熟悉之物中暗藏著陌生感。如今流行的夢核等多少也有非家幻覺的影子。明明是熟悉的場景,卻給人一種陌生感……但馬克·費捨本人恐怕會將其分類為陰森而非非家幻覺吧。常見的夢核往往帶有“令人懷念”以及“熟悉的場景中沒有人”的要素。為什麼其中沒有人的存在?施動者去了哪裡?更重要的是,那個不該在場的東西像幽靈一樣存在了,那究竟是什麼?我們猛然發覺,那就是集體創傷。夢核也好中式恐怖也罷,這些藝術作品能喚起我們的不安和焦慮,很大程度上依託於“集體創傷”。你看到熟悉的家,半開的門,想到父母緊張的關係,會忍不住想父母是否又在吵架?看到空無一人的熟悉的房間,又會想起童年時被孤零零扔在家裡的恐懼。創傷是超驗的,僅憑一個熟悉的符號就能把它喚回,這就是讓我們不安的真相。
正如一開始說的幾個故事,原本平靜的水塘在母親的告誡之下好像忽然變得陌生了,這就是“陰森”。主人公沒有聽從看護人的告誡,去看到了不可以觸碰的領域,從而導致理性的區域出現了巨大的黑洞,這就是“怪異”。“陰森”讓我們從日常事務中抽離,換了一個視角去看待原本習以為常的事物,進而產生毛骨悚然的感覺。那是種平靜的恐懼。“怪異”則不然,“怪異”未必會喚起強烈的恐懼感,也可能是令人著迷。怪異的事物本身也沒有什麼問題,它自有一套存在的邏輯,只是以我們目前的知識和大腦,不足以理解罷了。
——今晚的電波如何?您還喜歡這次的電臺節目嗎?什麼,您問那麼這裡是怪異還是陰森之所?不,這裡是家。只要待在有電塔標誌的區域,任何東西都無法帶走您。那麼,晚安,祝您在詛咒……不,祝福中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