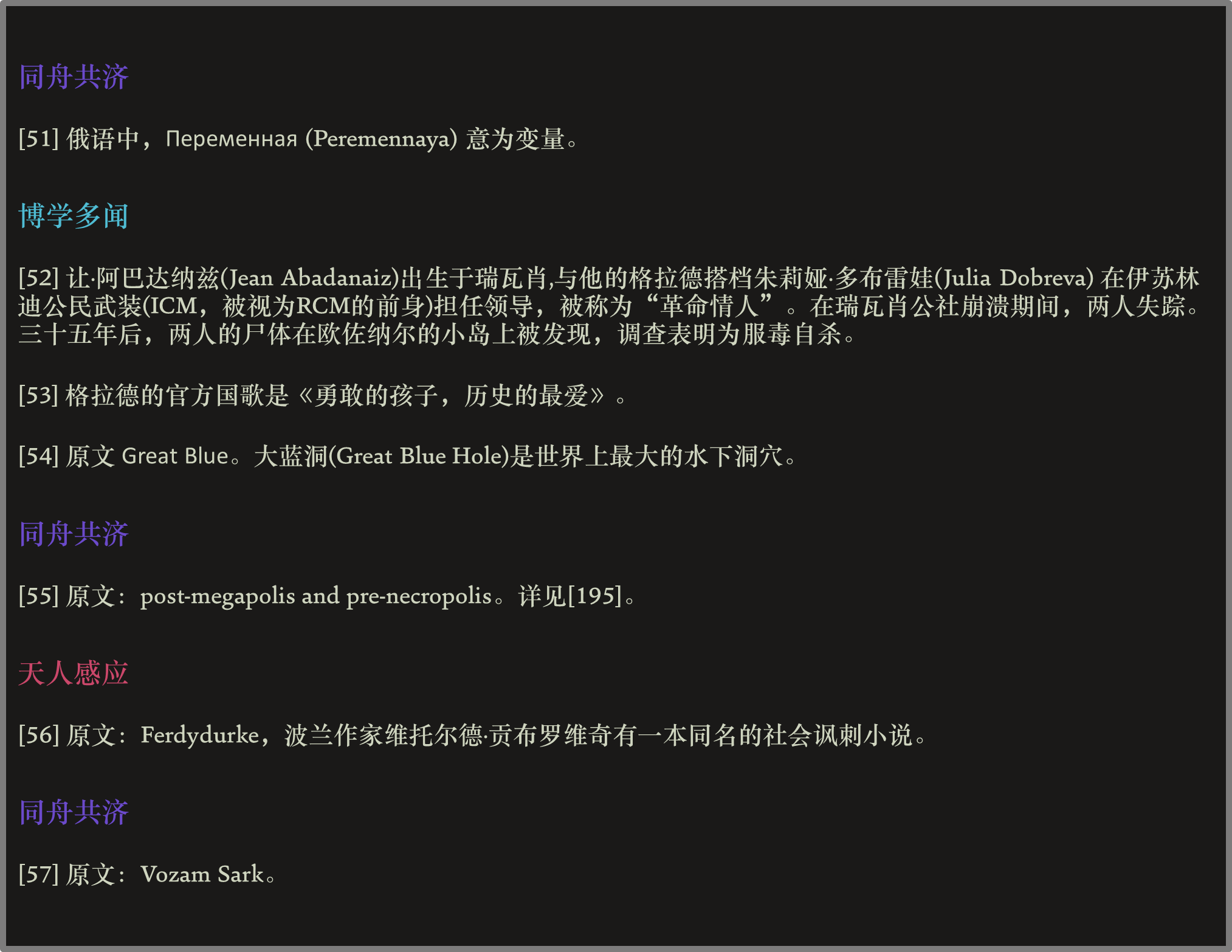有時,最令人悲哀的失蹤是那些仍然成謎的消失。在變成水力發電站之前,佩雷門內亞[51]·維拉還只是維拉河,流向處於人氣頂峰時的輕歌劇明星娜佳·哈南庫爾的投身之處。本可以繼續保持那樣的狀態:在一場驚心動魄的演出後,娜佳直接消失在一個秋天的夜晚,她天籟般的女高音還在劇院中迴盪。聲稱看到她身著晚禮走過橋樑的那個老人,是事實嗎?還是那個堅稱一年前在瑞瓦肖偶遇她的狂熱粉絲是真的?或許在偏執的通俗小說家的故事中存在某些真相:娜佳其實是梅斯克間諜,虛無主義者,末日先知。誰又能下定論呢?
但是有一件事是確鑿無疑的。沒人需要看娜佳身著晚禮服,仍然在水庫的泥漿裡掙扎。沒人想看她眼窩中的淡水貽貝棲息地,金牙咧出的死亡笑容,或是水電站施工隊的驚訝表情。
徒勞。徒勞塑造了世界。歷史是一個徒勞的故事,進步是一條徒勞的序列。“發展!”未來學家說。“迷失。”反叛者說。“宿醉!”後排的道德家喊道。“失敗!”憤怒的反叛者說。“時間是灰色的。”他說。締造者的失敗就是對時代的介紹。卡拉·馬佐夫飲彈而亡,阿巴達納茲與多佈雷娃在歐佐納爾島飲鴆自盡[52]。棕櫚樹下風捲殘塵,枯骨沉沙,誰該知道呢?來自全世界的善良人們齊聚一堂。教師、作家、蜷縮在戰壕裡的移民工人…年輕的士兵拋棄了他們的部隊。他們的歌聲多麼美妙!因此對他們來說,勇敢的孩子是歷史的最愛[53],他們揮舞著繪有銀色角冠的白色旗幟。
然後他們失敗了。
政變被粉碎。無政府主義者堆積在偉大藍[54]的亂葬坑裡,康米主義者從格拉德的大洲發起反攻,然後撤退到薩馬拉,變成一個由官僚統治的墮落工人國家。革命情人失蹤案在接下來的三十五年裡懸而未決,直到裡奇·勒波姆八歲的兒子尤金,在歐佐納爾的一個無名小島上進行週六晚間郊遊時,在岸邊發現了阿巴達納茲和多佈雷娃相擁的白骨。他穿著短褲,拿著蝴蝶網站在那裡,困惑地看著骨頭,他們似乎在舊日裡緊貼著。光滑且褪色。一個人從哪裡開始而另一個又在哪裡結束?時間如同洗牌一樣將它們混在一起。後來,裡奇在那裡打造了一座酒店,以及一個如今舉世聞名的健康中心。
但是最偉大的失敗,並非馬佐夫的全球革命如何在流血中結束,以及隨後被如何摧毀,也不是今天,革命情人的骨頭被如何放在芳香療愈候診室裡展示。內部動亂被鎮壓後,格拉德成為了世界勢力,一個巨型國家,它的城市欣欣向榮,這股從軌道起,增長中的耀眼光芒連成了閃耀的網絡。多個國家完全從世界地圖上消失。那些曾經有著無數馬佐夫支持者的國家。類似齊姆斯克的國家。人民被蔑稱為“克吉克”的國家。而這種稱呼持續如此之久,最後他們甚至用它自稱。
特雷斯·馬切耶克七歲了。他的父親是模範克吉克,一位外交官,一個見風使舵的篡奪者,到現在仍未送他去瓦薩上學。整個城市就是個生態災難區,處於發展階段的倒數第二段,後巨型都市期和前廢墟都市期[55]的人類聚居區。聚合材料製造技術傳播到齊姆斯克和雨果的邊境地區。怪獸吞蝕了齊姆斯克的歷史中心——費爾迪杜凱[56]的皇家老城區,以及蘭卡的松樹公園。夏季到來,在昏暗的地窖裡,低語著一個名字。孩子們則在住宅的庭院裡喊著它。街道靜謐無聲,樹葉簌簌飄落,只有那個名字在格拉德民兵的耳朵裡迴盪。
“勇敢者弗朗索瓦…”
克吉克里中勇敢的人。一個電影明星,一場革命。直到最近,春季的暴亂才被殘酷地鎮壓,如今已經兩個月沒有他的消息了。據說他蟄伏在遙遠的雅庫特保護區的針葉林裡,從原住民祭司那裡汲取特異功能。奇妙的東西!他的草原鷹顴骨和渴求的目光,溫暖的笑容,如同在針葉林上空冉冉升起的太陽。他嚴肅的眉毛因為憂慮而緊鎖時,他只為極少的場合保留的微笑…他意氣風發的臉龐出現在澤西工廠的禁片中,那裡的女人十分勇敢,把他縫在背心和內褲的白布上。不,弗朗索瓦在薩馬拉!談判中。他和人們共和國的勢力一同降臨!別幼稚了,弗朗索瓦在遠離此地的科拉,在冬季軌道內,伊格努斯·尼爾森的小屋裡。他們永遠都找不到他!安靜!勇敢者弗朗索瓦不會躲藏!就在昨天,有人看見他在排隊買肉,他現在裝扮著假鬍子,穿著屠夫的圍裙,自稱烏佐馬·斯拉卡[57]。倒著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