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一座濱海的偏遠城市,它位於高緯度的北境,那裡冰厚到車可以在上面行走;它擁有著巨大的港口,名字叫馬丁內斯(Martinaise),曾經是一個偉大公國的首都,然而在幾次大規模社會運動後,國外資本、傭兵、甚至連毒品都連番蹂躪這塊土地。馬丁內斯破敗不堪,漏出鐵架的破敗雕像,泥濘的道路,甚至連打漁小村都宛如鬼鎮的。這是一座被上帝遺忘的角落。
在馬丁內斯濱海區的的一個廉價旅館裡,一個全身赤裸、打破了玻璃、還喝到失憶的男人醒來了……這就是我們主人公哈利(Harry Du Bois)登場時的場景。
這種喪氣的開場,與其說是一個失敗的中年人生,不如說是具象化的前蘇聯百姓的精神寫照:我甚至懷疑,主創人員在編寫劇本時,應該人人手拿白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二手時間》。又或者,他們身邊充斥著類似的聲音:老年人抱怨著,說以前的生活雖然很難,買不到足夠的食物,但工作住房至少是國家分配,而人們也不會因生存壓力去放棄他們喜愛的詩歌;中年人則從支持改革的熱血青年,轉變成痛感被欺騙、被剝削的中下階層。不論學歷高低、有無重大科研貢獻,到最後大家都只能在路邊擺攤。青年人陷入強烈的虛無主義,否認蘇聯歷史上的衛國英雄,甚至有的人還認為當年納粹要是能佔領蘇聯就好了。當然這些年輕人可能不知道,納粹曾在烏克蘭肆意屠殺斯拉夫人、希特勒的目標是把整個莫斯科給剷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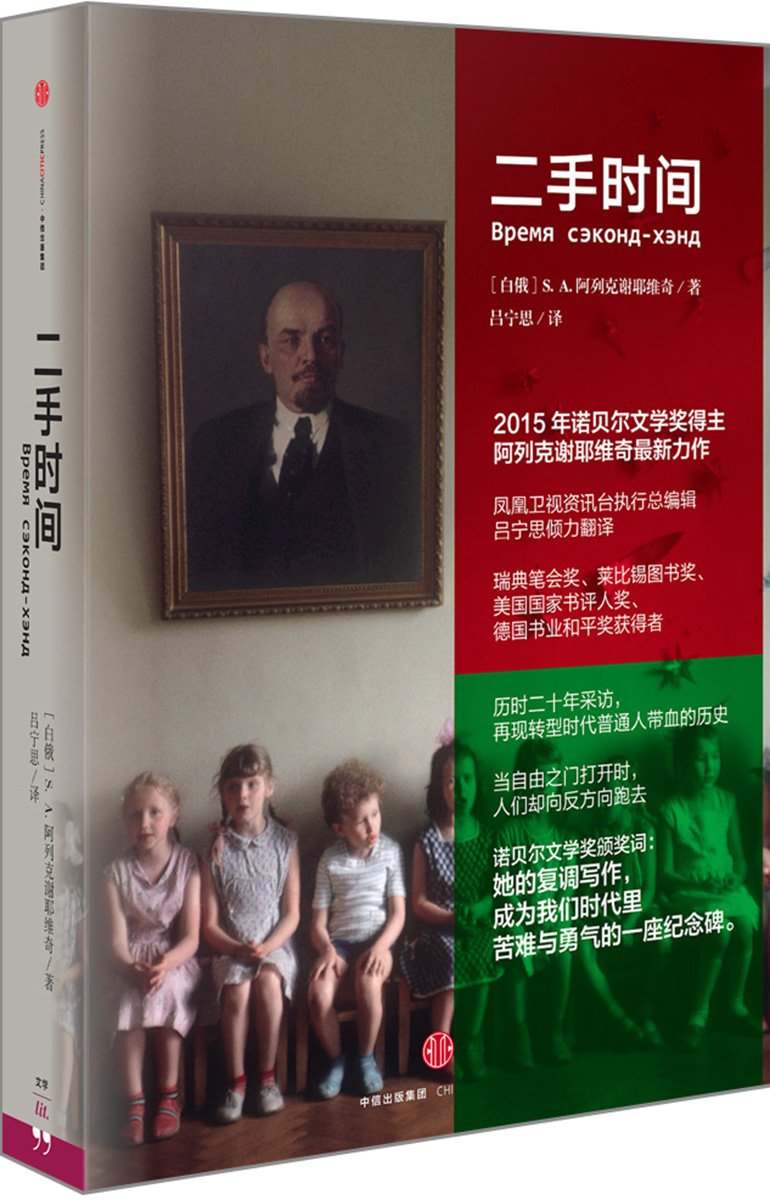
迷惑、憤怒、無奈、怨恨,這些都是那個時代前蘇聯人大部分的精神面貌,也是我們主角哈利的精神狀態:在面臨愛人離去,事業碰到瓶頸時,他直接選擇喝個爛醉,喝到肝損傷,甚至還喝到失憶;對於那些快速丸興奮劑他來者不拒,因為他不去想明天的事情,即便自己曾獲得警局頒發的最高榮耀,甚至還能當上警長……
《極樂迪斯科》與其說是一部破案小說,不如說是一幅素描,一種關於前蘇聯人的精神素描:這個成立僅僅六十九年,卻改變半個世界的政權,在鐮刀斧頭旗底下生活的老百姓,他們是怎麼看待生活,看待世界。
你知道他們為什麼會用油畫去描繪遊戲的人物與世界嗎?因為印象派捕捉的,是穿透表面後的真相。
三個地點
我聽人們講瑞瓦肖(Revachol)如何對應俄羅斯(Russia)時,總會覺得這座城市就是以聖彼得堡作為原型。作為俄羅斯前首都,聖彼得堡是一座建立在泥濘的沼澤地上的城市,人們傳說,聖彼得堡的地基下,埋藏著大量打地基時隨地掩埋的屍體(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類似孟姜女的故事)。即便如此,今天的聖彼得堡依舊光彩奪目,即便它經歷過納粹的圍城、大量的人吃人事件等。
遊戲裡的馬丁內斯,其實是一種混合物,它有著聖彼得堡的歷史,包含列寧格勒的一些特性,卻雜糅許多衛星國家都市的現實:破敗、坍塌、野藤爬滿了牆壁。以前的它有多光輝,現在的它就有多破敗。當然,這是除聖彼得堡以外衛星國城市的現況。
在《極樂迪斯科》裡,每一個區域都是一段象徵:一個埋藏在書店後面的破敗商業區(依我看來,這裡原來應該是座商場),往東去就是盤根錯節的碩大港口,西邊則藏有一座破敗不堪的漁村,裡面除了老太婆伊澤貝爾·沙蒂外就是一拾網人莉莉恩帶著三個小孩:西北邊有座無人禮拜的教堂。再往西走則是菲爾德大廈的遺址,甚至連行刑彈孔都被人們保留下來……

《極樂迪斯科》最先吸引我的,是旅館旁邊的破敗商業區。當你按門鈴時,會出現混亂的雜音,彷彿裡面正在發生什麼事:但當你爬上頂樓與骰子製作人交談時,會發現這裡早就沒人了,你聽到的聲音有可能是錄音。
這種時空錯亂的寫法,我最早看到是出現在《靜靜的頓河》:一個死亡的士兵的家書被敵方收刮,在閱讀這些書信時他們還在踢死者的屍體。事實是,這個商場已經徹底死亡,而人們只能在往日的錄音和遺蹟中去猜想當年在這棟樓裡,有多少個青年,想用瘋狂的主意去賺錢,去改變世界。所以他們添置了無線電臺、開辦了健身館、甚至添購了一臺以熊為外殼的冰箱。然而事實是,這些商業計劃付諸東流,最後人們離開這個商業區,只留下一段都市傳說:受詛咒的商業區。
事實是,在蘇聯解體時,許多知識份子在面對一個全新的社會與資本環境後,他們手足無措,被狠狠地打在地上。這些“前蘇聯人”,早已習慣政府安排一切:政府根據一個人的學歷去安排工作,並配置相對應的房子。但在蘇聯瓦解,外國資本進入的初期,那些“所謂的”蘇聯中產階級,發現他們的積蓄一夜之間蒸發,原本可以買汽車的盧布最後只能買一包煙。工作也沒了,科研單位收編甚至倒閉。而大量倒賣外國貨的“倒爺”開始發家致富。同時俄羅斯黑幫也不再掩飾,除了大量的軍火走私外,他們還會把很多住在莫斯科的人的房子透過詐騙的方式騙到手,而那些失業的人只能流落至鄉下,有些人不堪屈辱選擇自盡;然而當初也是這些人,支持葉利欽的改革,並在改革後痛罵自己被騙……二次大戰結束時他們騎馬揚鞭地走進柏林,蘇聯瓦解後他們只能祈求外國人多給點美金。
當然,蘇聯已經瓦解三十一年了,俄羅斯憑藉其資源和科技在慢慢恢復,但它以前所創建的許多東西到現在都無力維持。比如它在堪察加半島的許多軍事和科技觀察站,就因為常年疏於守衛而逐漸荒廢。西伯利亞的許多城鎮甚至需要政府補貼,才能維持一個基本局面。所以那個荒廢的商業區,與其說是針對哪棟真實存在的倒閉商場,不如說是對蘇聯瓦解後加盟國各國的經濟情況做一種影射(這麼說的話,那頭北極熊冰箱就更富有黑色幽默)。

既然聊到了軍事遺蹟,這就不得不提馬丁內斯和他北邊的那座被棄守的軍事據點了。
首先是那個玩球的皇家龍騎兵雷內·阿諾克斯。在歐洲近代史上,除了拿破崙外,沙皇的龍騎兵也是出了名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沙皇的龍騎兵很多是哥薩克人,所以遊戲裡的老兵刻意弄了個黑人形象的,或許也是另一種隱喻。
遊戲裡還特別提到兩個殘存大兩軍事遺蹟的地方:西邊的菲爾德大廈舊址和北邊的荒島。先聊北邊的荒島。要知道喀琅施塔得就是一座位於聖彼得堡以西的一座島嶼,有著看守這座城市的重大任務。一九二一年二月,因反對“戰時共產主義”,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開始集結抗議,公開並反對蘇維埃政權。當時列寧派軍事委員會負責人托洛斯基去負責鎮壓。這些水兵全部都沒投降,部分戰敗者跑到芬蘭,並在蘇芬戰爭後被抓回來處與極刑。
地理上的位置可以相對應,那老兵伊索夫本人呢?在《靜靜的頓河》裡,主人公格里高利曾經躲在一個小島上,去躲避紅軍的追捕:雖然他戰績卓越,但因為當時情況混亂,格里高利在紅白兩軍陣營裡反覆橫跳,最後為了躲避大鬍子將軍布瓊尼——順便一提,這位老哥薩克可是在衛國戰爭時提出保留騎兵來對付納粹——的追捕,跟一個白軍軍官守在島上。最後因為互相猜疑,再加上布瓊尼逐漸收復頓河南岸一代,所以他們分別離開小島。當然,一位是革命遺老,一位是裹挾在時代裡身不由己的哥薩克騎兵,但他們都是被時代所遺棄,最後因某些事件而被迫放棄他們固守的小島,回到那個他們已經無法融入的新時代。

關於教堂,我覺得有兩點可以談。
第一是俄羅斯的宗教觀。我們都知道,斯拉夫人的主信仰是東正教,那是一種脫胎於拜占庭帝國、偏希臘化的天主教。但蘇聯是強調無神論的,整個蘇聯曾經發生過類似英國宗教改革時的事:士兵衝進教堂並收刮昂貴的禮器,神職人員全部抓起來送去勞改,甚至連斯大林同志把莫斯科地標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給炸了,用來改建蘇維埃宮的(但沒蓋成)。本來在西方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教堂,被人荒棄,甚至變成癮君子聚集搞派對的地方去了。

陽極音樂(Anodic music)的原型可能就是八零年代流行的電子舞曲,也就是我們統稱的“迪斯科” 。這種音樂的特性就是用大量的合成器,用類比音訊(Analog)和濾波器(Filter)去雕塑各種聲音,然後用鍵盤演奏。
這種音樂首先是從德國的發電機(Kraftwerk)開始,爾後由英國的新秩序(New Order)開始推廣,然後在八零年代紅遍全世界。現在很多人追捧的蒸汽波,很大一部分就是當時玩迪斯科的日本音樂人的作品。

其實早在搖滾樂(七零年代)時,西洋音樂就開始滲入蘇聯。除了捷克地下音樂大佬宇宙塑膠人外,俄羅斯搖滾教父柳拜(雖然他們的出線已經是蘇聯解體後)也是早在蘇聯時期就開始接觸並學習西洋搖滾。但這些我們現已習以為常音樂,當時蘇聯官方的態度是反對和打壓的。宇宙塑膠人早期的演出非常地下,很多都是靠口耳相傳來通知演出場地;而外國唱片的管道也非常難得,就跟蘇聯時期買條牛仔褲一樣,需要透過大價錢和硬關係才能獲得。
當然,當蘇聯瓦解,人們的精神活動開始解放後,本來被強力打壓的東正教捲土重來,很多老黨員在臨終前也開始上教堂(俄國有句俗話:你在四十歲前可以胡作非為,四十歲之後就只剩祈禱了)。而西洋音樂也毫無限制的傳入俄國,那些紅軍歌曲變得如古董般被年輕人排斥,大家都用最新潮的樂器去譜寫俄羅斯流行樂。原來那些被視為不可撼動的正統被人屏棄,似乎俄羅斯一直就跟西方緊密融合。
不過您可以找找歌曲“再見,莫斯科”(До свидания, Москва),將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民族

報刊亭旁的種族歧視者,他歧視任何非白人、非瑞瓦肖本地人,於是乎他對金的不客氣激怒了金.同時他對跟他同一情況(都在路邊擺攤),但僅僅是外國裔的席勒表示對這種人的不屑。然後就是那個著名的測顱先生了,根據他的身型還有口音(新版本的配音),可以看得出他基本是黑人,而這也是為什麼,他會說主角原來的種族(白人)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但如今他們只能沉溺在毒品和酒精裡。當然還有因亂說話而導致艾佛拉想給他一個警告的蓋裡,欺軟怕硬最後還被主角“懲罰”了一下。
蘇聯的民族問題一直是一個難以解決和定論的存在,這也是為什麼列寧會選擇斯大林去負責剛成立的民族委員會。爾後在紅白內戰時期,高加索地帶因期複雜的民族關係(哥薩克、斯拉夫、格魯吉亞、阿布哈茲、亞美尼亞等),所以列寧派斯大林去負責蕩平這裡的問題。爾後在斯大林與布瓊尼的合作下,蘇聯把最後一位白軍的將領鄧尼金趕出蘇聯國境,並用軍事的力量鎮壓這一帶的反動組織(斯大林的格魯吉亞老家也曾發生動亂,斯大林直接派兵鎮壓)。爾後這一帶的民族問題在“蘇維埃”的大旗下被暫時擱置,大家都認為自己是“蘇維埃”人並開始慢慢融合。
然而在蘇聯瓦解之時,南俄發生了嚴重的暴動事件。格魯吉亞人開始四處追殺生活在那裡的斯拉夫人和亞美尼亞人,大批難民逃到莫斯科並飽受虐待和汙辱。在莫斯科,除了正統俄羅斯人以外,還聚集了大量前蘇聯加盟國的百姓或難民: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哈薩克斯坦、甚至部分白羅斯人。我們或許覺得這些國家脫離俄羅斯就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獨立:但事實上這些“前蘇聯”人普遍都是講俄語,他們已經習慣了與斯拉夫人交往(尤其是中亞四個斯坦國,會脫離俄羅斯部分是因為俄羅斯不願意在供養他們),所以他們的百姓也願意去莫斯科去尋找更好的機會。但也因為過往的歷史(比如蘇聯在烏克蘭徵糧徵到那邊發生饑荒),所以俄國的民族問題並不比美國好處理;同時他們處理問題的辦法,也比美國更血腥、暴力。

踢他一腳!
“沒有國家是為了別人來享福而去建設的”,俄羅斯的民族問題,遠比遊戲裡提及的複雜且棘手。遊戲裡你可以痛斥報攤小販,懲罰蓋裡讓他賠錢,甚至猛踹測顱先生一腳。但不幸的事,現實往往是反過來的。
灰域

灰域壓縮機
我不瞭解齊澤克的哲學理論,所以對“灰域”沒有什麼很專業的意見。但根據我對蘇聯史淺薄的瞭解,覺得“灰域”也可以解讀為“每個人心中的斯大林主義”。
大家都知道古拉格,也讀過很多關於古拉格管理時許多駭人聽聞的故事。然而勞改營之所以恐怖,不光是它極其殘酷且無情的管理機制(比如索爾仁尼琴指出的“按勞分配”制度),事實是在斯大林時期,整個蘇聯都活在監控與告發的狀態。
關於契卡抓人的事蹟,我可以大約舉兩個:在蘇芬戰爭結束後,很多被釋放的戰俘在簡單的審問後直接被丟到古拉格去勞改。而這種戰俘被丟進勞改營的事情一直持續,從蘇芬戰爭到衛國戰爭,不論勝負,不管理由,很多老兵回來後就直接丟到勞改營服刑。更有甚者,因為衛國戰爭時缺人,很多服刑人被暫時放出來參戰,然後戰爭結束後再回勞改營繼續服刑(然而你可能想不到的,許多勞改犯因為沒能參與衛國戰爭而懊惱悔恨不已)。敵佔區的東歐也是同一情況。在蘇聯紅軍解放東歐後,很多服務與納粹的烏克蘭人、白羅斯人被槍斃外,許多平頭百姓也是直接被審被抓(契卡說:你們為什麼沒有逃往蘇聯或者加入游擊隊?)。甚至還出現被告人請審問者指定他叛逃那個國家這種荒唐事。

Isaiah Berlin
在戰爭狀態如此,在平常日子也沒好過到哪。著名的英國學者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曾在戰爭結束後拜訪莫斯科與聖彼得堡(當時斯大林還活著)。他與《齊瓦哥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Пастернак)、白銀時代詩人代表之一的阿赫瑪託娃(Ахма́това)私下見面,互相分享文學心得外,伯林也表示了從腳踏莫斯科的那一霎那,監視就開始了。而且伯林與兩位作家的見面,基本都是私底下偷偷見,因為他們害怕被人舉報。要知道當馮·勒布圍攻列寧格勒時,阿赫瑪託娃跟列寧格勒城民堅守在這座城市裡;然而戰爭結束了,他們的生活卻比戰前更加的緊張,尤其是對她的指控曾差一點把她抓進古拉格。
講到這,我想指出我對“灰域”的看法:與其說它是一種高度抽象的哲學世界觀,不如說它暗指斯大林主義下人們內心的陰暗面:除了四處安排監聽器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外,人們常常會因為互相告發而打入大牢。很多人可能因為一句玩笑話就直接被丟到古拉格。然後等他們回來後,卻發現告密的居然是跟自已的平常頗為交好的鄰居,甚至是友人。於是乎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蕩然無存,所有人都在想保住自己,而他們公認的最好辦法,就是先出賣對方。這種瀰漫整個蘇聯的冷漠與無情,讓斯大林主義激發出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邪惡。所以他們都說:每個人都是受罪者,同時也是加害者。在這種“灰域”底下,沒有人是無辜的。
當然,在斯大林死後,這種濫抓犯人的情況收斂很多很多,但是契卡依舊器而不捨地監控人民。於是乎百姓發明了“浴室密談”:兩個人跑到浴室去聊天,聊的過程中開著水龍頭,有些時候甚至直接對著天花板喊:您好啊,警察先生。
當然,這一切都在蘇聯瓦解後煙消雲散。但並不是這個監控過程取消了,而是採用更隱秘,而且全球通用的辦法:互聯網。
伊蘇林迪的“幽魂”

《共產黨宣言》開頭就說:“一個幽靈,飄蕩在歐洲的上空” 。這個“幽靈",可以視為傳說中的伊蘇林迪竹節蟲:一直存在,但不是人人可見。它的存在可能比人類歷史還要古老,且世界各地依舊有不少人依照這種精神過活。早期創造美國的清教徒、生活在極寒之地的愛斯基摩人、甚至選擇遠離紛爭的隱士團體,都選擇這樣的共存生活。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中國就出現一個類似蘇維埃的團體:墨家。他們強調“兼愛”(愛無等差,眾生平等)、非攻(天下大同,不分國界)、節用(反對浪費,拒絕裝飾)。曾經這個團體被視為顯學,並針對強調等級之分的儒家發起強而有力的攻擊。然而到商鞅、韓非子等戰國末期,墨家聲勢已經大不如前了。等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墨家基本已經銷聲匿跡,一直到民國重新審視儒家以外的學術時,才被人提及和重視。
對大部分的人而言,愛無等差、無私奉獻、屏棄裝飾這些原則,太苦、太難、也太單調。它否定人性中對“好”的渴望與需求,打壓了人們對改善生活的積極與動力。蘇聯或許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出現人類歷史上第一位外星人、甚至連“網路”都是他們發明的:但他們沒辦法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更無法激發老百姓去創造更大財富的慾望。人們常說,蘇聯可以生產大量的飛機坦克,但他們的工廠連一臺烤箱都生產不出來。事實證明,如果再給俄國人一次機會,他們依舊會選擇放棄蘇聯這種制度。最好的明證就是,其實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並未解散,他們依舊參與大量的政治活動,甚至包括競選國家杜馬。然而有趣的是,沒有太多人願意給俄共再一次機會,他們在杜馬議會的選舉一年不如一年,且沒人知道這現象會不會繼續下去。
當然,只要世界還存在不公,存在剝削與壓迫,就總會有人秉持墨家的俠義精神,出來帶頭反抗這些“人性之惡” 。但當被壓迫者翻身上位後,就像那隱喻《動物農莊》豬老大的艾佛拉特那樣,成為一次又一次的無限循環…
“一個隱秘的幽魂,遊蕩在伊蘇林迪的大地上…”
參考書目
《靜靜的頓河》:肖洛霍夫
《蘇聯的心靈》:以賽亞.伯林
《先知三部曲》:伊薩克•多伊徹
《古拉格群島》:索爾仁尼琴
《古拉格:一部歷史》:安妮·阿普爾鮑姆
《耳語者》:奧蘭多·費吉斯
《二手時間》:阿列克謝耶維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