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為什麼在設計敘事前我們需要武裝頭腦?
2024年六月底,我在學習了媒介社會學相關的知識後,受視野被開拓的熱情與靈感所驅動,開始寫作雜談《從媒介的視角看遊戲文案的困境與出口》。我先後發佈了涉及“困境”的上、中兩篇,但唯獨最關鍵的探討“出口”的下篇卻難產了。在寫下下篇的大綱後,我看著大綱,忽然意識到這可能只會是一篇偽學術垃圾。越是從媒介學的視角探討,我們便越能看到遊戲在成為複雜的綜合藝術之前,先是一個精密運轉的現代文化產業的產品。我當然可以高屋建瓴地大談特談行業可能的出口,但最後能落到實際而對閱讀文章的大家真正有意義的,恐怕只有“遊戲文案該怎麼做”這一小部分了。
而遊戲文案該怎麼做呢?
從入行開始,我便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但若我真正將這部分作為文章的核心內容,以我的實踐經驗和理論儲備,真的能回答好這個問題嗎?在2024年中旬的我還沒有這樣的信心。而隨後的2024年下半年,也算機緣巧合,我為兩個項目快速地從0到1搭建了比較完整的虛構層框架。雖然它們的體量都不算大,但最終的效果讓我對自己長久以來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積累的方法論有了一些自信。所以正值2025年的新年,我希望將它們分享出來,作為《從媒介的視角看遊戲文案的困境與出口》真正的下篇,為去年的理論探索收尾。也用作拋磚引玉,來和大家一起探討,在新的一年裡為成為更好的遊戲文案的奮鬥作開篇。
同時在上面兩個項目的開發過程中,我再次意識到,只探討遊戲文案怎麼做往往還不能真的導向一個敘事優秀的遊戲。正如我在《從媒介的視角看遊戲文案的困境與出口(中)》裡面提到的:
理論上的文案策劃的職能在實際開發中被分化出去了,這是遊戲這種媒介的經濟模式和市場需求所決定的。如果相關崗位的從業者對遊戲文案、虛構層包裝都有著比較全面、系統的認識,能夠在此基礎上密切配合,最終一起實現一套優秀的包裝,想來也不會有文案策劃有怨言。但這卻偏偏是現階段業內的文案策劃們比較無奈的事。
所以,最終這篇文章會不只是面向遊戲文案,而是面向所有對遊戲敘事設計有興趣的遊戲開發者。我希望儘可能從遊戲敘事的底層出發,去幫助大家達成上面提到的“對遊戲文案、虛構層包裝都有著比較全面、系統的認識”。這篇文章的核心便從“遊戲文案該怎麼做”,轉為了“在設計遊戲敘事前,設計者應該做好哪些認知上的準備”。
在開始之前我們先再次確認一下進行認知準備的必要性:
- 玩家審美迭代加速
- 回顧遊戲敘事的發展史,如今遊戲設計者的總體敘事水平無疑是高於兩千年初的。但在我們心中,當今稱得上敘事經典的作品湧現的頻率似乎並沒有提高。這側面反映了我們作為玩家的審美水平也在提升。且玩家對遊戲敘事的要求只會越來越高,直到遊戲不再能滿足玩家對故事的需求,他們便轉向別的媒介來滿足這種需求。
- 工業化生產需求
- 遊戲規模的擴張帶來遊戲開發團隊的膨脹,工種越分越細,而知識區隔使溝通成本膨脹。而對遊戲敘事較統一的整體認知能極大減少策劃、美術、音頻團隊在產出敘事方面內容時的溝通成本,也能保證大家在團隊合作中能在充分理解需求的前提下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從而提升產出質量。
- 敘事媒介特殊性
- 遊戲敘事有著它獨有的特點,在實踐中不能將其他藝術門類的敘事理論簡單套用過來。先跳出文學、影視的敘事理論,從交互性的根本來理解遊戲敘事非常有必要。
而在建立正確的認知之前,我們還需要澄清幾個常見的認知誤區:
(以下案例皆由我真實遇到過的情況改編,但其實我對我可愛的同事們沒有不滿,畢竟術業有專攻,此處只是舉例說明常見的誤區)
- 敘事≠寫故事
- “敘事就全部交給你(文案)了,放心,我作為製作人/美術/音頻不會太乾涉故事的事情。”
- 敘事並不簡單地指講述一個故事。在敘事學中,敘事有著更廣泛的含義,它指通過某種結構來傳達一些信息或者體驗。也就是說,從廣義的敘事的定義來看,所有遊戲都需要傳遞信息和體驗,也就都繞不開敘事。而遊戲敘事當然不只是文案需要考慮的事情。遊戲為敘事所建立的結構又叫做虛構層,它包含著美術、音頻,而又被遊戲的交互規則——玩法深深影響。團隊中每個人的每個選擇幾乎都會影響到敘事最終的效果。因此,想要創作出優秀的遊戲敘事,團隊的每一個參與者都應該朝著共同建立一個優秀的敘事結構而努力。
- 世界觀≠設定集
- “我想給這個角色面部加個防毒面具/頭上加一對貓耳不可以嗎?只是加一個小設定,又不會影響什麼。”
- 世界觀是經由遊戲所表現出來的敘事符號所搭建的一個可信的,因此才可沉浸的虛擬世界。他是人為設計的敘事符號之間的關係與意義,也是設計者人為創造的文化語境(別擔心,後面會細緻解釋這句話)。它並不是簡單的設定堆砌,它需要在一個邏輯嚴密、核心明確的框架下層層展開。有時一個小設定的更改會像改掉一棟樓的承重柱一樣,對世界觀最重要的可信性帶來巨大影響(比如在一個本沒有獸人設定的世界觀裡給主角加個小小的貓耳)。那如何判斷設定能不能改、能不能加呢?這裡有一個原理可以用來幫助判斷:某個設定需要展現出對玩家關心的事情——信息的呈現、故事、角色的有邏輯的影響,才會被玩家採信,它才能融入世界觀當中去。因此,對信息的呈現效果、對故事的講述、角色的塑造有益則能加能改、能加,反之則不能。
- 共情≠煽情
- “我們對主角的想法很簡單,可愛就行了。我們沒有打算寫有深度的或者煽情的故事,所以本來還沒有考慮讓玩家對角色共情的。”
- 如果敘事的主要目標只是為了準確地傳達信息(《俄羅斯方塊》),或者給玩家提供簡單的代入感、沉浸感(《堆疊大陸》),那麼在設計時可以拋開共情的問題。而如果遊戲敘事的主要目標涉及到塑造一個角色,或者換句話說,涉及到講述一個故事,那麼讓玩家共情便自然而然地變成了最關鍵的一步。玩家要關心遊戲的故事,關心遊戲角色的成長變化,他才不會想要在對話或演出時點擊跳過按鈕。而建立關心也就是要建立玩家對角色在當前故事發展中的當前困境、當前感情、當前選擇的感同身受,也就是所謂的“共情”。共情是講述故事、塑造角色的大前提,煽情只是達成共情的一種手段。
前言的最後,我在這裡列一個文章的目錄:
- 我們可以怎麼看待遊戲敘事?
- 遊戲的敘事內容包括哪些部分?
- 遊戲敘事的“好”有哪些維度?
- 如何落地遊戲敘事設計?

一、我們可以怎麼看待遊戲敘事?
一切都開始於這一個問題:遊戲是什麼?
如同其他學科的本體論問題一樣,這一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我堅持認為遊戲製作者在製作某一遊戲時,他對遊戲的認識會充分體現在製作的過程和結果上。如果認為遊戲是藝術,那麼製作者往往會更重視藝術性與個人表達;如果他認為遊戲是娛樂,那麼遊戲的玩法和樂趣會被放到設計的首要位置;而如果他認為遊戲是產品,那麼大家便總會聽到他用“賽道”“競品”一類的詞彙表述自己立項和開發的歷程。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推薦過一個更全面的視角來看待遊戲,即媒介的視角。遊戲在成為藝術品、娛樂方式、商業產品之前,它首先是一種能夠用以傳遞信息的媒介。
- 媒介被生產出來的目的,在於它能傳遞承載的信息,以達成傳者/受者的目的。而遊戲這種媒介區別於其他種類的媒介,有著“交互性”這一獨特的特點。
- 遊戲這一媒介的發展是以各種媒介技術為基礎的。技術的發展會極大地帶動遊戲的發展。
- 而這種媒介現在是在一個龐大、複雜、精密的現代文化產業中生產的。這個產業既受制於外部的政治、經濟環境,而又由產業中每一個活生生的人組成。
媒介的視角能夠包容我們前面提到的一些視角,它也能包容一些遊戲未來潛在的發展方向。例如教育遊戲、醫療遊戲、公益遊戲等功能遊戲,無法被上述的藝術品、娛樂方式、商業產品的視角所容納,但它們能很好地放入媒介的視角內。
從媒介的視角來看:
- 首先,遊戲的敘事內容是遊戲這一媒介產品所承載的一部分的媒介信息,這一部分往往又包含了兩個模塊的內容,一是對遊戲交互的虛構包裝,二是對遊戲流程的故事包裝,它們往往作為遊戲這一媒介串聯和傳遞信息的核心,且能賦予玩家的遊戲體驗以更豐富的意義。
- 其次,主要負責遊戲敘事的文案策劃(理論上的,實際常由別的崗位兼任,有專職文案策劃的項目反倒佔少數)處於遊戲行業這一媒介產業當中,其產出會深受項目內的崗位要求、權利分配、工作流程影響。在項目之外,遊戲敘事也會受到整個行業的行業規範、商業模式,乃至上下游產業鏈的影響。
- 再次,遊戲敘事的設計與敘事相關的技術聯繫密切。像articy:draft一類的文案管理軟件的發展促成了《極樂迪斯科》等具有極其複雜的分支對話的遊戲誕生。此外,在理論技術方面,我們也能看到近十年來影視寫作技巧的引進與成熟,使得《美國末日》《荒野大鏢客》等作品在敘事上大獲成功。
- 而後,遊戲文案面對著遊戲玩家這一受眾群體,玩家的需求與過往的遊戲產品塑造著玩家對於遊戲敘事的期待,這種期待會間接影響到文案策劃的產出。而如今在平臺時代,遊戲在各種平臺上的玩家社區幾乎決定了遊戲的“生命力”,社區氛圍的營造更加需要被納入敘事設計的考慮要素之中(《碧藍檔案》的成功離不開這一點),社區的輿論反饋往往也會直接影響到敘事內容的修改。
- 最後,遊戲文案還受到上述眾多因素之外的外部社會世界的制約,包括各種政治、經濟因素。大家感受最為直接的大概是版號制度,以及最近歐美遊戲中愈發盛行的政治正確內容。
而當我們以媒介的視角來看待遊戲,遊戲敘事內容又起到怎樣的一個作用呢?
首先,媒介的核心功能是傳遞信息。而遊戲這一媒介的特點是交互性,它本質上只是玩家與一段程序進行輸入與輸出的信息交互,原始的信息是以二進制的形式存在的。人類當然無法直觀地理解二進制信息,而將這些二進制數據轉化為玩家能夠理解的內容,這就是遊戲敘事的開始了。例如玩家按下鍵盤的A鍵,程序使一張圖像根據某些參數往位置座標軸x軸的負方向移動,並在屏幕上反饋出來,而遊戲敘事便將這個過程用圖像、文字、音頻符號包裝為玩家操縱一個角色,向遊戲場景的左側移動,或者包裝為玩家以上帝視角在拖動場景中的某個物件向左。這樣對遊戲程序的反饋信息進行“包裝”,其實就是我們常提到的機制層上的虛構層設計。它賦予了遊戲體驗基本的意義。想象一下完全沒有虛構層的遊戲,玩起來恐怕就是程序員測試代碼一樣的體驗吧。
同樣的遊戲玩法也可以使用完全不同“包裝”,就像我上面提到的那個例子。他們可能會導致反饋信息呈現的效果截然不同,從而影響到遊戲風格和玩家體驗。而玩家深惡痛絕的“換皮遊戲”之所以存在,也正是因為虛構層“包裝”有很強的可操作性。
當然,如今大家開始設計一個新遊戲,肯定不會先從程序邏輯的角度思考,再尋找合適的敘事包裝。遊戲設計的發展經過多年的積累,在虛構層包裝上已經有了一些慣例,他們被統合進了遊戲題材、遊戲類型的定義裡。即使對一個遊戲毫無瞭解,別人在提到類銀河惡魔城、魂類、格鬥遊戲、西幻這些遊戲的標籤時,我們腦海裡也會浮現出一些常見的包裝元素,或對整體的敘事風格先有了想象,這就是慣例的力量。但我認為了解這樣的底層邏輯是沒有壞處的,在題材和類型的框架下,我們仍可以繼續探索更加貼合遊戲玩法的虛構層包裝方式,更換慣例的虛構層設計,也能為玩家帶來新鮮的體驗。
其次,無論是出於藝術表達的、商業的,或公益的目的,所有的遊戲設計者都希望玩家在上手遊戲後,能持續地玩下去,直到設計者達成了他們的目的。從玩法(機制層)的角度來看,心流理論能為我們達成目的提供指導;而從敘事(虛構層)的角度來看,我們已經通過虛構層構建好信息認知的框架了,而吸引玩家持續遊玩,實際是需要基於玩家意義的反饋,進一步影響到玩家的情緒,再進一步塑造玩家與遊戲的情感聯結。用通俗的方式來講,這其實就是配合玩法建構代入感、沉浸感、共情的過程。遊戲達成了與玩家的情感聯結後,還可以更進一步向玩家傳遞價值觀,在虛構層賦予的基本的意義之上,為玩家的遊戲體驗賦予更深刻的意義。
反過來看,最糟糕的情況是遊戲無法影響到玩家的情緒,玩家會覺得遊戲無聊,自然會放棄繼續遊玩。其次糟糕的情況是當一個遊戲的體驗過程激起了玩家在設計者意料之外的情緒,例如突如其來的NTR情節帶來的憤怒,持續出現惡性bug帶來的噁心,這些都有極高的讓玩家棄坑的風險。
在媒介的視角下,該怎麼定位遊戲文案策劃這一崗位呢?
我在前言中提到,這篇文章是面向所有對敘事設計感興趣的遊戲開發者的,但這裡我仍舊想分享一下我理解中的遊戲文案策劃核心的工作責任,以幫助大家更好地與文案策劃合作,或判斷自己的項目需不需要一個文案策劃。
我平常向同事們介紹文案策劃的職責時,往往會這麼比喻:設計和製作遊戲的交互規則/玩法像是在搭設骨架、安排內臟。而理想狀態下,我們文案策劃的工作便像根據骨架和內臟來統籌安排串通全身的血管,從而幫助美術、音頻設計直接表現在外的皮肉,讓遊戲的外在鮮活起來。而我們安排的血管裡,流淌的是意義的血液,它們使玩法的心臟一次次搏動,讓玩家的情緒也隨之波動,從而使玩家能感受到,這是一個活生生的、協調且有魅力的藝術生命。
在實際的開發流程中,敘事設計的工作肯定會分散,完全由文案作為上游給美術、音頻非常細緻的設計需求,會限制美術、音頻的創造空間,往往也不現實。因此,我認為文案策劃在一個團隊內最恰當的位置是敘事顧問。在承擔最基本的設定、故事、文字工作以外,文案策劃還應該積極主動與其他崗位的同事們溝通,為敘事元素的設計提出建議、反饋,為敘事設計的前進的方向掌舵,努力使大家對項目敘事內容想要達到的效果有著統一的認識,並在此大前提下,尊重各個崗位獨立的創造空間,盡力將大家的靈感納入到敘事整體當中來。
對於文案策劃,乃至所有遊戲敘事的設計者來說,什麼是媒介的視角呢?就是既要尊重敘事理論,也要尊重開發實際,尊重團隊創作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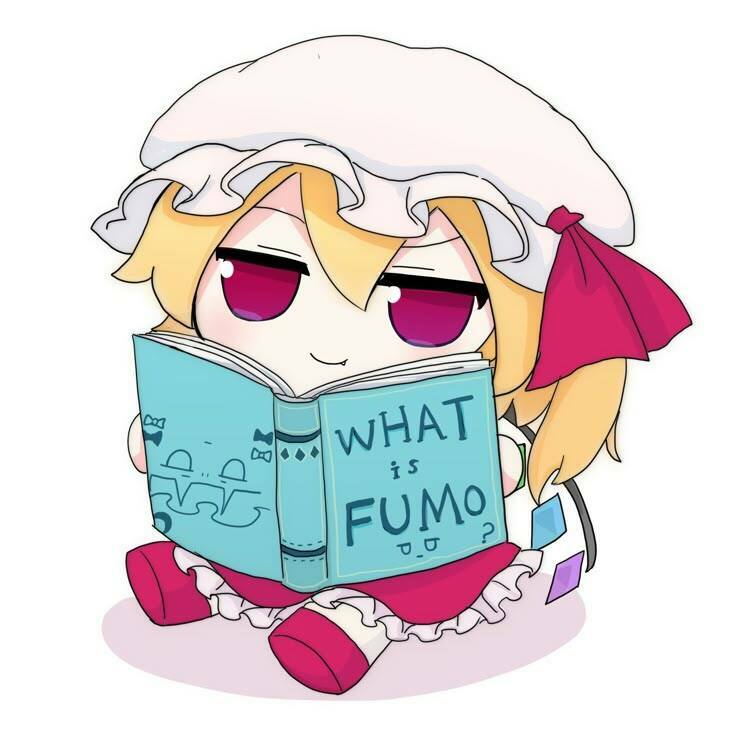
二、遊戲的敘事內容包括哪些部分?
上一個部分中,我們探討了該如何看待遊戲敘事。但這樣的基礎認知還不足以指導我們的實踐。為了排佈設計敘事時的優先順序,審視各個部分的敘事元素達到的效果,我們需要對遊戲的敘事內容進一步進行劃分,並細緻討論各個部分的原理與作用。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從中國的遊戲文案策劃這一崗位的發展史中總結過現階段文案策劃的工作:
理論上,文案策劃需要配合其他崗位橫向地為遊戲中相互關聯的系統建構符號體系,賦予玩家與遊戲的交互以意義,同時需要縱向地為遊戲流程在這套符號體系上搭配相符的敘事,讓玩家的體驗過程在玩法樂趣上增添審美價值。因此,現階段理論上的遊戲文案指代著一個統一的符號體系,它由兩個互為表裡的部分組成, 一是對遊戲交互的虛構包裝,二是對遊戲流程的敘事包裝。
而現在,拋開了崗位歷史的視域,我們已在上一部分的探討中已經從作為遊戲根本的“交互性”中再次推導出了相似的結論。我們在這裡可以更新一些表述方式,讓它更加細緻準確:
- 遊戲的敘事內容其實是一個複雜精密的球體,但我們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角度將它切開來看。
橫向——虛構層:
- 橫向切開,我們便會看到在某個遊戲的時刻或者片段,設計者將遊戲的交互信息由程序語言轉譯為了另一套相匹配的、成體系的符號語言。
- 這套符號體系讓玩家能理解遊戲當前的狀態,瞭解遊戲的交互規則,並賦予了玩家與遊戲的交互以意義。
- 我們將這套符號體系稱作“虛構層”。這是遊戲敘事的基礎。
縱向——故事層:
- 縱向切開,我們便會看到在遊戲整個遊玩流程中,在虛構層的基礎上建立的敘事過程。
- 這個過程將零散呈現給玩家的意義逐漸聯繫成一個整體,並將這些意義延伸成情緒體驗。
- 配合精妙的符號體系與此起彼伏的情緒體驗推動玩家沉浸到遊戲的世界中、與故事角色產生共情,並最終接受設計者試圖傳遞的價值觀。
- 我們可以將這個敘事過程稱作“故事層”。故事層是一個敘事過程,往往會講述一個故事,但並不一定需要講述一個故事。
- 在編劇的劇作理論中,一個故事成立需要有五個要素,主角、目標、阻礙、失敗代價、為什麼故事開始於此。這五個要素往往天然地存在於遊戲玩法規則之中。
- 例如,象棋並沒有講述故事,但基於象棋的虛構層,我們也能從兩個玩家對弈的過程中提取出上面的五個要素,這會是一個指揮官操作士兵運籌帷幄消滅敵軍的故事。而即使是俄羅斯方塊,我們也能在一定的腦補下想象出遊玩過程代表的故事。
- 也就是說,在合理的虛構層之上,玩家與遊戲交互的過程會自然形成故事。理解了這一點,也就能理解為什麼遊戲能實現湧現式敘事了。
注意:你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虛構層”指的是所有敘事內容,其實包含了這裡所謂的故事層,而我為了更好地將理論落地,在這裡將它們拆開來了。
當然,上述的橫向與縱向只是兩種觀察遊戲敘事的視角,在做橫與縱的切分的時候,我們也應該牢記遊戲敘事是一個複雜的動態過程。縱向的故事層肯定離不開橫向的虛構層的支撐,而橫向的虛構層中各個符號的意義,往往也需要在故事層展開的過程中逐漸聯繫成一個整體,而才能為玩家所理解。
現在,我們再更加細緻地討論虛構層:
我們已經瞭解了虛構層是一套符號體系,而這套符號體系是如何傳遞意義的呢?
符號學告訴我們,符號傳遞出意義有著這樣一個過程:符號→結構→敘事信息(意義)
- 符號指的是承載著意義的事物,它是傳遞意義的最基本的單位。
- 例如,一個字即是一個符號。
- 符號的概念最初來自於語言學。語言符號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能指,二是所指。能指是符號本來的概念和對象,例如漢字“花”的能指是字形“花”和字音“hua”的結合;而所指是符號具體指代的對象或意義,例如漢字“花”的所指是被子植物特有的生殖器官。
- 當符號的思維發展到了更廣泛的人文社科領域,便出現了文化符號學。文化符號進一步地在語言符號的所指之上探討符號衍生出的文化含義,例如在文化符號學看來,文化符號“花”的能指是被子植物特有的生殖器官,而文化符號“花”的所指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可能是美好、生命、青春等象徵含義。
- 符號的意義是在語境當中傳達的,文化符號的意義也是在文化語境當中傳達的。這意味著傳遞意義的不是符號本身,而是符號之間的組合關係。換句話說,在一個作品中單獨的、與其他符號無邏輯關聯或文化隱喻關聯的符號沒有實際的敘事意義。就像在艾爾登法環中突然放入一個哆啦A夢只會讓人困惑,或被解讀為某種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的藝術潮流。
- 承載著意義的符號會組成結構。
- 結構的概念來自於學術界與藝術界的結構主義思潮,而從結構的思潮中進一步發展出了現代敘事學。結構可以進一步解釋符號如何在與其他符號的組合中,或在文化語境中運作。
- 結構主義者認為,文化意義實際是通過二元對立的符號構成的結構來傳達的。例如,一個故事讓正義的勢力與邪惡的勢力對抗,這便構成了一個簡單的正義與邪惡對立的結構。通過正義最終戰勝了邪惡,作品能傳達出邪不壓正的意義(奧特曼)。當然,絕大部分作品為了追求敘事深度,結構都不會如此樸素,往往不止一組對立,是多組對立交織,即使是同一組對立,也可能有幾重的內涵。
- 那麼在藝術作品中,美如果沒有與醜對立,那美便無法傳達出美的意義嗎?實際上並不會。人類對符號有天然的敏感,一個作品中若只有代表美的符號,沒有代表醜的符號,那受眾也會無意識地將代表美的符號與自己的認知經驗聯繫起來,在作品外尋找與之相似的符號和與之對立的符號,來嘗試解讀出信息(只是符不符合作者的意圖就是未知數了)。這是因為人類天生追求意義,會難以接受無意義的事物。因此,個人的認知經驗對符號的解讀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設計者讓符號承載的意義貼近該符號在現實的文化語境中的意義,也會降低受眾解讀符號的難度。
- 我們每個人早已置身於社會生活的符號的海洋中。所以,無論設計者是否有意,符號與作品內外的其他符號組成結構是自然而然的事。只是有設計目的的更清晰的結構會帶來更簡單的接受難度,使受眾有著更清晰準確的理解。
- 而綜合我們上文的探討,結構便是一個由相似或對立的符號組成的聯繫密切的符號體系。視它囊括的符號的多少,它可大可小。它在一個一個簡單文化意義基礎上傳達出更深遠的意義。因此,構建結構需要精巧地選擇文化符號,編織它們的關係,來表達結構中相似或對立的各個元素,便能搭建起虛構層的地基。
- 虛構層是一個宏觀的結構。
- 遊戲中的所有有意義的元素都是符號,它們共同組成了虛構層這一個宏觀的敘事結構。
- 虛構層的結構中基本的對立是遊戲規則中玩家與阻礙之間的對立,而以此為基礎可以排布出代表玩家/主角的符號、代表目標的符號、勝利相關的符號、失敗相關的符號、代表友方的符號、代表敵人的符號等,所有的符號都會有一個初步的位置。遊戲玩法的不同可能會使符號在這個結構中排布的方式不同,但為了構建遊戲自己的語境,這些符號在規則之外一定還需要用某種邏輯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們往往會藉助現實的文化語境,以及遊戲世界觀設定。
- 如果這些符號的之間的聯繫與對立關係清晰,並且在作品內外的文化語境中的聯繫與對立關係也足夠清晰,並且這種聯繫與對立非常契合遊戲規則中的聯繫與對抗,那這樣的虛構層便非常易於理解。例如象棋。
- 好的虛構層會呈現給玩家一種簡潔、準確、又似乎能包羅萬象的優美,這是一種近似於氛圍的整體的美感,你無法用任何單一的元素描述出這種美感,它是遊戲中每個符號的合力,存在於遊戲的每時每刻,每個角落。例如《Gris》《動物井》《艾爾登法環》。
我們繼續更細緻地討論故事層:
在現代的電子遊戲中,虛構層中的符號不會在遊戲一開始就全部都呈現給玩家,玩家也沒有一本規則書,讓他能在遊戲一開始就理解所有符號的聯繫與意義。從本質上看,故事層,即所謂的敘事過程,其實就是將虛構層中的符號按某種順序、以某些方式逐步展示出來。
- 敘事順序與敘事方式
- 在故事層這個敘事過程中,遊戲的符號會在某種敘事順序下呈現出他們的聯繫與對立關係,也就傳遞出了他們的意義。敘事順序需要與之相匹配的敘事方式,但敘事方式更多在交互規則的範疇,且根據項目需求可以千變萬化,我就不討論了。
- 我認為最好的敘事順序便是玩家按遊戲規則自由體驗的順序,即玩家在遊玩遊戲時符號緊密圍繞著遊戲的規則,也配合玩家的交互過程自然地呈現出來。符號的關係、意義不用設計者用額外的信息來解釋,也在玩家遊玩的過程中能逐步被玩家領悟到。所謂的環境敘事是這種敘事順序的一種體現。而在這裡我還不得不提到《巴別塔聖歌》,它彷彿就是為了解釋這個理論而誕生的。
【《巴別塔聖歌》介紹:基於文字學和符號學的優質解謎遊戲】
- 而其次的敘事順序是按照一個故事敘述的順序。遊戲敘述一個故事,塑造一個或多個角色。而我們從劇作理論中引進了激勵事件、進展糾葛、高潮、結局的故事展開順序,在玩家遊玩遊戲的過程中插入對話、演出呈現信息。這樣也能通過角色和故事的邏輯串起大部分的符號,符號的意義也可以在故事或者對白中得到進一步解釋。
- 再次的敘事順序就是按照設計者設定的順序。簡單來說就是在玩家遊玩到某個節點時,會彈出額外的信息來解釋遊戲中的符號的具體意義,以及它和其他符號的關係。我並不排斥這種方式,在不影響玩家體驗的前提下,這種方式成本最低,也最直觀,但想要用得自然並不容易。而在體量較大的遊戲中,這種順序也不太可能成為主導的敘事順序。
- 上述三種順序以外的其他順序,例如意識流,或者基於互聯網流行梗進行敘事,這些都太小眾了,我就不展開了。
- 而遊戲當然並不是只能採用一種敘事的順序,在大部分項目中,三種主流的順序都是交織在一起的。用哪種順序作為主導,以及在何種場景下使用哪種順序,並且搭配什麼樣的敘事方式,這是要求設計者根據自己項目的需求細緻考慮的事情。這裡提供一個優秀的案例以供參考——《薩爾達傳說:曠野之息》。
- 情緒變化
- 玩家接受這些符號的過程實際是在接受與遊戲交互的反饋。理想情況下,獲得意義的反饋會影響玩家的情緒。如果敘事過程能配合玩法持續地影響玩家的情緒,使其上忽下、起伏不定,那玩家便會持續地被吸引住,產生代入感、沉浸感。這是一個遊戲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不讓玩家“無感”或“無聊”。
情緒變化也是故事層的最基本的要求,下面便是設計者們可選擇添加的內容了。
- 故事與角色
- 我們在前面提到過,遊戲規則往往天生符合故事成立的要素,遊戲其實非常適合講述故事。故事中的價值變化和角色的成長弧光能激發玩家的共情,讓敘事帶來的情緒變化上升為情感變化,玩家便與遊戲產生了情感紐帶,這極大地增強了遊戲的吸引力。
- 利用故事層講一個故事其實要比用電影、小說、戲劇講故事有著更多的限制。這是因為故事是充滿矛盾的,矛盾其實就是二元對立的結構,而遊戲已經先有了虛構層的結構了。故事的結構必須先融入虛構層的結構當中去才能順暢地講述。例如在一個沒有戰鬥的休閒建造遊戲內放入一個跟建造無關的,主角戰天鬥地的故事,有極大概率會顯得水土不服。如果故事的核心矛盾,也就是核心的結構,貼合虛構層的總體結構,也就是貼合著遊戲玩法,那故事的呈現便能自然地嵌入遊戲流程當中。例如用象棋的規則講一個楚漢爭霸的故事,用肉鴿遊戲講一個逃脫輪迴的故事。
- 而如果遊戲中的符號既非常符合呈現玩法信息的要求(也就是先有一個好的虛構層),又非常符合呈現故事信息的要求,那麼故事的主題展現便能自然地嵌入玩家遊玩遊戲的體悟中,角色在故事壓力下的抉擇對應著玩家在規則壓力下的選擇,角色成長魅力的呈現貼合著玩家在玩法中的成長,那遊戲帶給玩家的情緒變化也就自然在故事高潮的力量中上升為了情感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玩家將為遊戲的高潮所震撼,從而與遊戲產生情感鏈接。例如《蔚藍》《逆轉裁判系列》。
- 價值觀
- 而通過結構,設計者也能在故事層中傳遞出自己的價值觀。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了通過“正義”與“邪惡”的結構來傳遞邪不壓正的價值觀。而如果將主角設計為多元性別人士,TA的敵人是各種對TA存有偏見的人,或代表著偏見的兇暴生物,那便能打造出符合歐美DEI政治正確的遊戲價值觀。
- 遊戲的交互性使得遊戲相較於其他媒介,更易於讓受眾在遊戲過程中接受植入的價值觀。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特點,玩家如今已學會在挑選遊戲時避開那些充滿說教意味的,甚至引起他們反感的價值觀。不妥當的價值觀還會在玩家社區內引起輿論風波,而如果處理不當,在平臺時代,玩家社區對遊戲越來越重要的當下,這便幾乎等於給遊戲的社區活力和商業前途判下死刑。例如《少女前線2》《龍騰世紀:影障守護者》。所以,價值觀的選擇必須慎之又慎。
- 即使設計者無意傳遞價值觀,但就如我在上文中提到的,我們早已處於現實的文化語境中,有些符號或對立結構是帶有意識形態標籤的(比如男與女的對立),玩家也有可能試圖從中揣測設計者植入價值觀的意圖。設計者需要留心,自己遊戲中的結構有沒有在無意中傳遞出某種有風險性的價值觀,或自己能夠接受的價值觀是否是當今的玩家群體難以接受的。如果因為這種事情而導致好遊戲風評受損,那也太冤了。例如《活俠傳》。

三、遊戲敘事的“好”有哪些維度?
我們在第一節中提到了遊戲敘事設計應該採用媒介的視角,而上一節的內容其實主要集中在媒介內容上,也就是遊戲本身的內容上。我們已經從虛構層、故事層兩個角度總結出好遊戲媒介內容要滿足的幾個條件了:
- 符號的之間的聯繫與對立關係清晰,並且在作品內外的文化語境中的聯繫與對立關係也足夠清晰,並且這種聯繫與對立非常契合遊戲規則中的聯繫與對抗,這樣的符號體系構成的虛構層便非常易於理解,也會呈現給玩家一種簡潔、準確、又似乎能包羅萬象的優美。
- 遊戲按一定敘事順序/敘事方式呈現符號,清晰地呈現出它們的關係與意義。並在這個過程中配合玩法持續地影響玩家的情緒,使其上忽下、起伏不定,持續地吸引住玩家,使玩家產生代入感、沉浸感。
- (如果有故事的話)故事的核心矛盾,也就是核心的結構,貼合虛構層的總體結構,也就是貼合著遊戲玩法,將故事的呈現自然地嵌入遊戲流程當中。
- (如果有故事的話)遊戲中的符號既非常符合呈現玩法信息的要求,又非常符合呈現故事信息的要求。使故事的主題展現自然地嵌入玩家遊玩遊戲的體悟中,角色在故事壓力下的抉擇對應著玩家在規則壓力下的選擇,角色成長魅力的呈現貼合著玩家在玩法中的成長,讓遊戲帶給玩家的情緒變化自然在故事高潮的力量中上升為情感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遊戲的高潮將震撼玩家,從而讓玩家與遊戲產生情感鏈接。
- 審慎地植入價值觀,確保遊戲中呈現出的價值觀是玩家群體能夠接受的。
但遊戲這一媒介處於一個極其複雜的外部環境中,達成了上述條件只是遊戲敘事被評判為“好”的基礎。遊戲的敘事內容還需要:
- 在產業中,經歷項目內部的、公司內部的、發行商的評判。
- 在流媒體平臺中進行宣發,經歷平臺用戶的打量。
- 隨後經歷發售平臺、國家制度的審核。
- 發售後,經歷玩家的體驗與評價。
- 形成玩家社區後,在玩家反覆的二次創作中不斷經受提煉與審視。
可以說,要闖過以上眾多難關,最終形成一個好的風評,才能被稱作為“好”。這麼看來,這簡直是地獄難度。我試圖在這裡再額外提供一些“好”的維度參考,以幫助大家的敘事內容渡過上述難關。
- 商業性
- 我想沒有遊戲開發者會認為這是一個不重要的維度,所以我必須把它列在這裡。但這個維度很寬泛也很概括,與其看我這個失業小文案誇誇其談,感覺不如去問Deepseek。我就不耍大刀了。
- 創新性
- 玩家渴望著新的敘事體驗,而行業也渴望著新的前進方向。遊戲的敘事內容在滿足上述五個條件後,如果還具備創新性,那不可能不受到歡迎。
- 敘事創新最終體現在能否讓玩家感嘆:“原來遊戲故事還能這樣講”。 真正有價值的敘事創新應滿足下面兩個條件:
- 提供前所未有的體驗,能在玩家認知中建立新範式。例如《黑暗靈魂》的碎片敘事。
- 激發行業模仿與迭代。例如《極樂迪斯科》的對話呈現方式。
- 而在上文的虛構層、故事層的邏輯下,我覺得從下面這兩個方面探索可能更易實現敘事創新,給大家作為參考:
- 虛構層與遊戲規則更深層次的結合。例如《巴別塔聖歌》。例如《1001夜》 探索基於對話AI的創意敘事遊戲玩法 。
首頁 | 1001 Nights
- 敘事順序/敘事方式的創新。例如《十三機兵防衛圈》的網狀敘事。
- 社群話題性
- 在平臺時代,玩家的評價越來越決定一款遊戲的生死,玩家社區的活躍程度也越來越決定一款遊戲的生命週期。所以我會建議在敘事設計時便儘可能考慮當代玩家的需求,考慮創造社群話題性。
- 如果遊戲的敘事能夠在宣發時在玩家社區中創造有積極影響的話題,可能會幫助遊戲的銷量提升一個數量級,例如《幻獸帕魯》《米塔》。
- 如果遊戲的敘事內容留有足夠的空間供玩家長期挖掘話題,那麼便可以形成良好的二創生態,極大提升玩家留存率和遊戲影響力的持續時間,例如東方Project、《碧藍檔案》。
- 藝術性/審美價值
-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抨擊了完全將遊戲作為個人表達藝術來創作的方式,但那是在枉顧遊戲團隊創作的形式、枉顧遊戲本身性質與設計原理的前提下。而一個遊戲作品如果只是純粹的文化工業的產品,那再成功的商業成績也只會讓它在歷史的長河中曇花一現。只有藝術性能讓遊戲敘事超越時代的限制,為代代的玩家帶來超越時代的審美體驗與感動。藝術性仍舊應該作為敘事設計的最高追求。
- 那什麼是藝術性呢?我採用了張世英先生在《哲學導論》中的回答:
以有限表達無限,或者說,以有限超越有限。
- 一個遊戲作品超越有限的程度,決定了它的藝術性的強弱,也決定了它審美價值的高低。
- 在這樣的理解下,遊戲敘事需要追求在有限的內容中,傳遞超越無窮時間、無限空間的感動與哲思,去折射我們的“生活世界”,去叩問我們這樣渺小的生命在這樣的無窮和無限當中,有著怎樣的意義和出路。我想,這就是《蔚藍》《星際拓荒》為什麼偉大的原因。

四、如何落地遊戲敘事設計?
在開始這一部分之前我必須聲明,遊戲敘事設計沒有標準流程。
我下面提供的只是基於上文中對遊戲敘事認識的理想化的流程。而項目需求是千變萬化的,開發實際也是千變萬化的,每個人擅長與不擅長的部分也千差萬別。對於遊戲敘事的設計者來說,什麼是媒介視角?就是既要尊重敘事理論,也要尊重開發實際,尊重團隊創作的形式。
所以,所有的流程一定開始於與團隊成員的溝通。請在理想化的流程的基礎上,在開發過程中積極探索適合自己團隊的工作流。
注意:以下故事相關的術語皆來自於羅伯特·麥基《故事》,這裡限於篇幅,便不展開解釋一些故事相關的原理了。而我會向任何想要學習故事寫作的人推薦這本書。
- 前期準備
- 首先了解大家期望本項目的敘事要達到什麼效果,跟團隊一起確定本項目敘事的主要目標。
- 與團隊成員溝通,瞭解大家對敘事的認知程度,以及對本項目敘事內容的一些願景。尤其需要與美術、音頻溝通,瞭解他們的風格,以及他們希望在本項目中創作什麼。
- 嘗試統合大家的想法與靈感,做一些取捨。一起配合玩法的設想擬定一個大概的敘事方案,初步設想虛構層風格與結構,一些核心的符號。設想一些故事層的要素,例如主要的敘事順序與敘事方式,設想主角形象,以及確定需不需要故事等。
- 與相關崗位的團隊成員商量好對接的流程,初步建立起工作流。如果在建立工作流的過程中,感到大家對敘事的認知水平有差距,或還沒有對本項目的敘事達成較為統一的認知,可以根據需要將敘事目標和初步設想總結為一份敘事規範,並在敘事規範中科普一些敘事相關的知識。然後用生命去逼迫大家仔細看這份敘事規範。
- 確定虛構層結構,與核心符號
- 確定好核心玩法後,需要確定下虛構層結構,與核心玩法相關的符號。例如在一個攀登模擬遊戲項目中,確定好玩家扮演的主角是什麼?他利用什麼攀登?攀登的是什麼?往下是什麼?往上又會見到什麼?
- 確認上述內容後,實際也就基本定下了項目的敘事風格,可以再次與美術、音頻對接,看他們是否能接受這樣的風格。可以與美術、音頻協商,創作一些早期的概念設計,進一步統一團隊成員對項目的想象與願景。
- 確定敘事順序與敘事方式
- 與負責玩法的策劃確定預期的遊戲流程長度,以及流程中是否有重要的節點需要敘事配合。配合預期的玩法流程確定需要採用的敘事順序,搭配相符的敘事方式。再次與負責玩法的策劃溝通,盡力讓敘事順序與敘事方法更好地融入流程。例如在攀登模擬遊戲項目中,確定好需要故事配合玩法,而預期的流程長度為一個小時,那故事便只能是短篇;流程為關卡制,有關卡切換,可以配合關卡切換設計場景變化、時間變化等符號的變化;關卡中有休息點,可以作為主要的敘事節點,在休息時用自由選擇對話、演出的方式呈現故事;而可以在關卡中穿插一些Bark來連綴敘事表現。
- 這一個部分是最有創新空間的部分,也是再往下推進後就難以回頭修改的部分,可以多花一些時間在這裡迭代。
- 如果項目不需要故事的話,便可以直接跳躍到確定角色設計的步驟了。如果項目甚至不需要角色的話,便直接跳躍至豐富世界觀設定的步驟了。如果項目甚至不需要世界觀,那可以直接建立並維護敘事符號庫,然後開始最後的具體的文本設計了。
- 確定故事矛盾、故事結構
- 如果項目需要故事的話,務必先配合以上兩個步驟的結果,先確定好故事的矛盾,也就是故事的結構。例如在攀登模擬遊戲項目中,向上和向下的對立是虛構層最核心的結構,那便可以將向上和向下確定為故事的核心矛盾之一。思考向上和向下在故事中分別代表著什麼,我們在故事中是希望主角最終選擇向上?還是向下?主角配合著玩法流程在故事的結局該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這種矛盾結構是否缺乏內涵,是否需要再加入一對矛盾豐富故事的內涵?
- 這個過程也建議反覆迭代。
- 而在流程大致確定的情況下,故事的結構確定下來,實際也就基本確定下來了主角的成長弧光,以及項目想要傳達的主題。這時需要再次與團隊成員溝通,初步設想主角形象,初步設想故事開頭、故事高潮、故事結局時的情景。
- 請美術老師為上述情景畫一些簡單的故事板,再請音樂老師配合故事板做最初的配樂demo。不要吝嗇這些工作量,這其實是再次統一團隊成員對項目的想象與願景的過程。
- 確定角色設定
- 在初步的主角設想的基礎上,確定好主角的各種設定。包括外觀、性格與氣質、背景故事、成長弧光等。確定好主角相關的符號,向美術提出正式的人設需求,並配合美術對人設進行反覆迭代,直至最終定稿。
- 可以視需求的優先級陸續設計其他角色。
- 構建故事大綱
- 初步定下故事的高潮,再從故事的高潮反推整個故事,逐步寫下故事大綱。我建議一定要從高潮反推,高潮對遊戲故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只有這種方式才能保證高潮的質量。要儘可能避免《咒術回戰》的下場。
- 故事大綱儘可能以幕、序列、場景的卡片結構構築,此時至少要精確到序列,並儘可能精確到一些重要的場景。這裡的場景並不是指遊戲場景,而是指的是劇作理論中包含一個價值變化事件的劇本單位。而標註出激勵事件、幕高潮、序列高潮。然後再反覆迭代。
- 請再次與團隊成員溝通並對大綱達成共識。而如果美術有餘力的話,請在不受傷的前提下繼續逼迫他們根據大綱自由創作一些故事板。
- 豐富世界觀設定
- 與美術一同豐富世界觀設定,為遊戲在世界觀設定的組織下加入更多的符號,為後續的UI設計、場景設計等工作提供支持。
- 視項目需求,為美術提出一些正式的概念設計的需求,並幫助美術迭代概念設計。
- 細化故事大綱至細綱
- 細化故事大綱,直至精確到場景。如果可以的話,標註出每個場景中故事的價值變化,看看是否能對應上玩法上的價值變化。繼續迭代細綱。
- 在迭代細綱的過程中,根據故事需要,細化各種之前的步驟中沒有來得及完成的設計。例如配角的設計、場景的設定、怪物的設定等。這個過程中,也需要反覆與團隊成員達成共識。
- 建立並維護敘事符號庫
- 如果項目的符號較多,便需要建立一個專門的文檔,畫出虛構層的結構、故事的結構。並統計上述步驟中使用到的一些主要的符號,標明它們的意義,它們的關係。在來得及更改的情況下,可以嘗試精簡符號。
- 再次與團隊溝通,並就這份文檔達成共識。這份文檔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給美術、音頻在進行設計時提供符號選擇上的參考,保證虛構層的優美。請在符號有更改時及時維護這份文檔,並通知相關團隊人員。
- 具體的文本設計與迭代
- 到這一步不同項目的需求就完全不一樣了。但無論如何,積極主動地與團隊成員溝通,協助他們的設計工作,並保證團隊對敘事內容達成共識都是必不可少的。這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實現優美的虛構層,若在團隊沒有共識的情況下進行開發,便常會出現美術畫出的一些元素不太好融入現有的符號體系當中去的情況,這樣的元素增多便會使虛構層顯得鬆散,甚至影響世界觀的可信度,從而影響到玩家的沉浸感。
- 同時,迭代也是必不可少的。相信最開始的靈感一定不是最好的選擇,經得起審視的藝術是在打磨中練就的,或者會在打磨中變得更好。
我在這裡放上攀登模擬遊戲項目的敘事設計文檔。它比較細緻地展示了我從無到有構建敘事框架的過程,可以供大家參考。當然,當時的我一定還有做得不夠好,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對白),大家也可以當做反面案例。
《伊卡洛斯之旅》敘事設計

結語
以上內容僅是我個人對遊戲敘事認知的階段性總結。 我利用媒介學、遊戲學、敘事學、符號學、結構主義、故事原理的一些知識搭起了我自己的認知框架。我認為這當然不是真理,我將它分享出來,只是希望拋轉引玉。我非常歡迎大家來提出自己的見解、指出我的不足之處。
遊戲敘事這片土地本就沒有標準答案。有人用《最後生還者》證明線性敘事的生命力,有人用《極樂迪斯科》展現文本深度的可能性,也有人用《動物森友會》詮釋"無劇情"中的敘事魔法。我們像在不同山徑上攀登的旅人,最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丈量遊戲敘事的維度。
我們搭建認知框架的意義,或許就像工匠打磨自己的工具——不是為了雕刻出完美無瑕的雕像,而是為了讓每一次下刀都更穩、更深、更貼合遊戲的肌理。當方法論在實踐中反覆淬鍊,當個人經驗與集體智慧不斷碰撞,我們或許終將觸摸到那個本質:好的創作不是對理論的刻板復刻,而是讓知識沉入潛意識,再隨著創作者的生命體驗自然流淌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