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稍早時候,筆者在機核投稿了第一篇文章,收穫了不錯的反響,也算是點燃了我對社區討論的一些熱情。於是時隔一年,還是決定回到機核,無論如何也要給過去一年的遊戲生活來個總結,也是給新一年留些盼頭。在這個不尷不尬的時間點,也祝願看到這篇文章的讀者們,過去一年或多或少陪伴過我的編輯部老師們,新年快樂,吉祥如意。
由於一些私人原因,明顯感覺到今年投入在遊戲上的時間變少了,玩遊戲的時候也多次出現心不在焉的情況。也不止是遊戲,能感覺到對電影、戲劇、生活的精力與熱情也在衰退。總的來說,今年一共通關了9款遊戲,相較去年少了近三分之一的總量。同時,開了個頭沒有玩下去的遊戲也變多了,例如《最終幻想起源》《八方旅人》和《海市蜃樓之館》;去年立志要玩完的《最終幻想零式》《勇者鬥惡龍11S》等也沒有繼續玩下去。如果要再為明年立一個目標的話,還是希望能定下心來,把手頭上這些開了坑的遊戲好好地收官封盤。
為了讓文章的內容量更加充實,今年決定提升一些文本質量與深度,更想著重於筆者個人的專業方向去討論,Gameplay的部分會略微減少一點。屆時可能也會引入一些理論與概念,如若感到枯燥,還望諸位海涵。
那麼接下來與諸位分享,2024年共計9款遊戲的個人感受。
1 《戰神:諸神黃昏》 4
這款遊戲我是在它2023年12月發售DLC後遊玩的,所以嚴格意義上並不能完全算是一部我在2024年玩的遊戲。雖然我也不是很喜歡這款遊戲,但是還是有兩點值得與各位說道說道。
一是,《戰神:諸神黃昏》並不是一個好的續集故事。
所有的續集故事都要面臨的一個問題,你要如何讓一個已經在前一部作品中擁有了完整弧光的人物更進一步,更加完整?
在前一部作品《戰神4》的結尾,奎託斯與兒子阿特柔斯歷經險阻力克強敵,登上了九界最高的山。兒子將母親的骨灰遞給父親,父親將骨灰袋推回給了兒子,並說了一句 “We do together, son.(兒子,我們一起)”。到此為止,從劇作角度來說,父子和解的戲劇效果已經達成了。兒子完成了對父親的理解,父親也完成了對兒子的認可,這一對父與子的人物關係已經完滿了,在續集中要如何進一步深挖這對父子關係,讓人物更加完整呢?
《戰神5》給出了最擺爛,最不用動腦子的解法。那就是把《戰神4》復刻一遍。

所以在《戰神5》中,玩家可以看到一個處於青春期事事叛逆的兒子,和一個如同反駁型人格,只會復讀‘You’re not ready’的父親。前期的所有劇情推動全靠父子二人的鬥嘴,但這一切都已經在《戰神4》裡預演了一遍了。兩個人的人物形象沒有一絲一毫的進步。同時,這也就是“親情”這種普世的、大眾的親密關係在文藝作品裡的流氓之處。試想一下,如果二人不是父子關係或母子關係或兄弟姐妹關係,而是一對普通的隊友與搭檔,福爾摩斯與華生,蝙蝠俠與羅賓,沒頭腦與不高興,觀眾會像這樣不在乎劇情的合理性嗎,還會用“父親對兒子嚴厲的愛”這樣蹩腳的理由來替編劇圓嗎?
所以回到問題本身,一個好的續集故事應該是什麼樣的。
這裡筆者給出兩個例子,一是2023年的《壯志凌雲2:獨行俠》;二是2004年山姆·雷米版的《蜘蛛俠2》。這兩部作品都是非常經典的讓主角經歷新的困境,並使主角完成第二次成長的續集故事。
《壯志凌雲2》,阿湯哥已經當了30多年的戰鬥機飛行員了,他老了,飛行員這個行業也老了。所以他面臨的新的困境是,如何不被新的無人駕駛技術取代。他需要向他的上級,向全世界證明,在這個新時代裡,舊時代的餘暉仍然可以發光發熱,而他成功地做到了。這就是人物經歷了新的困境,並完成了再一次成長。
《蜘蛛俠2》則更絕。它剖析超級英雄的內心,超級英雄也是人,彼得·帕克沒有辦法平衡好帕克的生活與蜘蛛俠的工作,於是他選擇放棄當蜘蛛俠。但歷經險阻打打殺殺後幡然醒悟,只有戴上蜘蛛俠的面具,他才能維護和保護好彼得·帕克的私人生活,更進一步地瞭解了貫穿整個蜘蛛俠系列的“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含義。
所以再回到《戰神5》,發現了嗎,甚至直到故事結尾都沒有突破《戰神4》父子二人撒骨灰的人物形象,兩個人的人物弧光是沒有絲毫的進步與成長的。而與上文兩個例子做比對更加發現,上文的兩位人物都是自發地,向內挖掘新的故事動機,所以人物是與故事的表達緊密相扣的。而《戰神5》的故事起點則是父子二人“被迫”捲入芬里爾之冬,然後來一個意料之中的反轉,死一個無關緊要的配角,到最後整個故事也並沒有什麼記憶點,更不要說有什麼表達了。

硬要提聖莫妮卡找補幾句的話,其實他們也發現了這個問題,在遊戲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他們想去深挖角色更私密的形象。例如奎託斯俠骨柔情的一面,試圖去塑造他與妻子之間的一些互動,或是去塑造一個情竇初開的青春期男孩。但我還是覺得他們做的挺失敗的,一是如上文所說的,這些橋段並沒有在我的記憶中留下很深刻的記憶點,二是明顯能感覺到這樣的感情不夠“真”。所以我會想向喜歡《戰神5》故事的玩家們推薦葛韋格導演的《伯德小姐》,同樣是一個很俗套很工業流水線的故事,來看看葛導是如何用情感來俘獲觀眾們的。
第一點說的有點長,第二點也比較抽象我儘量長話短說。那就是,《戰神5》反映了市場的導向以及玩家價值觀的變化。
這就要提到整部遊戲中,我個人最喜歡的一處場景了。在遊戲的中段,奎託斯騎著凱爾派去找命運三女神,三女神十分詳盡地以旁白的形式敘述了這場戲,預知了奎託斯要說的每一句臺詞,並最終給出了一個非常強烈的暗示,奎託斯命中註定會死。
現在我們知道這算得上是新戰神為數不多的妙筆,從《戰神4》就開始鋪的一個敘述性詭計。從前一部結尾奎託斯看到壁畫上一名男性死在阿特柔斯的懷裡,我們就開始猜測,是不是最終奎爺會死,是不是奎爺又要殺出冥界,是不是奎爺又要流亡去往一個新的國度,但幾乎我們不會去猜到死在阿特柔斯懷裡的並不是奎爺而是奧丁或是其他人。因為在潛意識裡我們冥冥意識到,這樣的劇情編排是違背戰神這個故事的調性的,因為在戰神的故事裡,命運應該是不可更改的。
是的,不管我們再怎麼噴戰神的故事,說它是男性爽文,歐洲起點,但其實戰神的故事是十分契合古典希臘悲劇的核心理唸的。即“英雄與他不可迴避的命運做鬥爭,並最終被所命運打敗”。

我們不與歷史上鼎鼎有名的《俄狄浦斯王》《美狄亞》《普羅米修斯》之流做對比,我們就拿戰神的故事做縱向對比。《戰神:斯巴達之影》裡是有預言說,人間有個臉上帶疤的禍害最終會弒父並推翻奧林匹斯的統治,於是宙斯才派阿瑞斯下凡去殺了奎託斯弟弟防範於未然。不管這是不是《戰神3》推出之後對設定的填充吧,最終我們也都知道奎託斯的確手刃了親父宙斯,也在臉上留下了疤痕,這體現的正是命運的不可迴避性。同樣的在《戰神1》中,阿瑞斯設計使得奎託斯親手殺害了自己的妻女,並將骨灰附著在奎託斯身上,成就了奎託斯的經典形象。而這體現的其實也是古希臘悲劇中的一個理論,即為亞里士多德的悲劇過失說。即 “(主人公)並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他之所以陷入厄運,並非由於他為非作惡,而是由於他犯了錯誤。” 在這樣宿命論與古希臘悲劇式的劇作方法下,戰神的故事基調還是相當嚴肅的。
但現在的問題是,現在的市場與受眾,其實是並不能接受這樣比較嚴肅的故事的。國內外正反各舉一個例子的話就是《逆行人生》和《魷魚遊戲》,主要宗旨就是“生活都這麼難了還要餵我這麼苦逼兮兮的故事”。無法否認的一點是,現在主流觀眾的主要訴求就是短平快和奶頭樂,就算是正劇,也得是《復仇者聯盟》那種“笑中帶淚”的“大製作”才買單。所以能夠看見從4代開始,整個故事向好萊塢主流的工業劇本開始看齊,先用公路片模式試水,到了5代是完全模仿《復聯》式的每個人物一條線,最後集合打boss的故事模板。這就是市場帶來的變化。
而觀眾價值觀的改變也體現於此。新時代的觀眾其實是不吃古希臘悲劇命運論的那一套的。你現在在街上隨便拉個人問TA信不信命,TA估計會以為你是來算命的。這一套對於命運的看法早在1994年《阿甘正傳》乃至更早之前就已經改變了。不要小覷文藝作品對於價值觀潛移默化的影響,新好萊塢這一代對於美國夢的宣傳早已將“努力可以改變命運”的價值觀深深種進一代觀眾的腦海裡植根發芽了。而更新的,未被“老登”價值觀染指的Z世代則對命運有著更新的理解,但這就不在今天的討論範疇之內了。此處的重點是,《戰神5》捨棄了傳統古希臘悲劇的宿命論,擁抱了主流受眾(存疑)的主流價值觀。
所以這也是《戰神5》這一處敘述性詭計寫的妙的地方。雖然它做出了迎合主流市場主流價值觀的選擇,引導玩家認為奎託斯的命運得到了改變。但它又並不是對奎託斯命運的直接改寫,而是一個巧妙的誤導,既保全了戰神故事原有的基調與宿命論應有的厚重感,又沒有得罪與冒犯了玩家群體,可以說是現代商業作品裡少有的一舉兩得的妙筆了。
2 《緋夜傳說》 7
在年初遊玩的時候我也不會想到,這部作品竟然會變成年終我最有話講的一部作品。
而對於這部作品我又是十分矛盾的。因為於我個人而言,我並不是十分喜歡這一部作品;但從專業性角度出發,我認為所有的遊戲編劇,對遊戲敘事感興趣的玩家,都應該來好好閱讀一下這個故事。
在遊玩這個遊戲的時候,我又同樣地想起這樣一部我個人並不是很喜歡,但是所有的遊戲編劇都應該拉出來學習一下的遊戲。所以在下面的分析中,我會將這兩部遊戲做一個橫向對比,而那一部遊戲就是,《最後生還者》1代。
在正式介紹兩部作品之前,我需要引入一個概念,一個正兒八經的故事模板,布萊克·斯奈德的“救貓咪節奏表”:
- 開場畫面 Opening Image(1)
- 闡明主題 Theme Stated(5)
- 佈局鋪墊 Set-up(1—10)
- 觸發事件 Catalyst(12):
- 展開討論 Debate(12—25):
- 進入第二幕 Break into Two(25):
- 副線故事 B Story(30):
- 玩鬧和遊戲 Fun and Games(30—35):
- 中點 Midpoint(55):
- 反派逼近 Bad Guys Close in(55—75):
- 失去一切 All is Lost(75):
- 靈魂黑夜 Dark Night of the Soul(75—85):
- 進入第三幕 Break into Three(85):
- 結局 Finale(85—110)
- 終場畫面 Finale Image(110)
具體的這些情節點所對應的意味有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詢(目前世面上浙江大學出版社的《救貓咪》翻譯水平較為一般,有能力的建議還是閱讀原文)。並且由於遊戲與電影的敘事結構還是存在較大的差異,此處也只是簡單借用一下這個概念。一言以蔽之,這是一個可以套用在市場上90%以上商業類型片的故事模板。有趣的是,如果將《最後生還者》與《緋夜傳說》(下文縮寫為《TLOU》與《TOB》)的故事代入進這個模板,可以發現它們與這個模板有著極高的相似程度。
還是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模板。可以看到每一個節奏點的後面有一個數字,這些數字對應的是劇本上的頁碼。在標準的工業流程中,一頁英文劇本可以約等於一分鐘的電影時長。這些頁碼有的是一個獨立的數字,而有的則是標註了一定的範圍。也就是說這些節奏點有的是直接對應劇情中的某些“情節點”,而有些則對應的是劇情中的某些“橋段”。模板給出的總頁數是110頁,即可以看做這是一部時長約110分鐘-120分鐘的電影。根據這裡所標註出的頁數範圍,我們亦可大致推測出這些橋段在整部作品中所佔的比例。
根據模板我們來看第一個情節橋段,即“佈局鋪墊(Set-up)”。直接按字面意思理解即可,這一部分應該讓觀眾建立起對主人公最基礎的瞭解,TA長什麼樣,TA是一個什麼樣的人,TA的生活是怎樣的,TA的驅動力源於何處。如果是有別於現實世界的奇幻故事,也應該大致地向觀眾展示一下世界觀。在粗略介紹完主要人物過後,主人公會在這一階段遭遇某些變故,TA平靜的生活將會被打破。緊接著,就是模板中的第一處關鍵情節點,在這一模板中被稱為“觸發事件(Catalyst)(催化劑)”,而在另一個著名的故事模型中,這一情節點被稱為“英雄收到召喚”,其實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激勵事件”。這一個對於主人公異常關鍵的事件使得主人公進入了劇情,產生了矛盾衝突,也確立了行動目標,也可以看做是主人公人物弧光產生變化的關鍵節點。此時也就確立了整部故事的基調,以及主人公的動作性需求,即整個故事最終所要達成的結果。
按照模板來看,在進入第二幕之前還有一個長約15頁的橋段,被稱為“展開討論(Debate)”,翻譯為“爭吵”“爭論”會更符合它的表意,與上文對應的另一個名字則是“英雄拒絕召喚”。這一橋段的含義是主人公在正式踏上旅程之前與自己內心的第一次爭執。主人公會懷疑自己是否該這樣去做,或是這樣去做的正確性、可行性、合理性。它可以是向內的,是主人公自己做心理鬥爭的視覺化呈現,對主人公深度人物形象的第一次探索與完善;也可以是外化的,具象為一次主人公與反面人物(反面人物不一定是反派人物,例如艾莉與喬爾就互為正反面人物)的爭吵或爭論。這一橋段在現今更摩登的工業化劇情中已經被大幅刪減甚至直接優化掉了,因為過於冗長的心理鬥爭或是爭吵會顯得人物很“婆婆媽媽”,很“事逼”(說白了還是觀眾不愛看)。我腦子裡立馬能想到的例子大概是某一部《碟中諜》,也是類似於伊森·亨特並不想接任務然後糾結拉扯良久之類的情節。所以這也算是一種比較老派的寫法了。

這裡我們不再去過多分析這些橋段放置進遊戲中應該如何呈現,例如將這些橋段與新手引導聯繫起來,或是如《TLOU》更藝術化地讓玩家代入進女兒的視角有更深的沉浸感,我們只看敘事結構。從結構上來講,竟然可以說是一模一樣。同樣是在Set-up階段對於主人公生活一個粗略的展示,例如《TLOU》中藉由女兒視角對於喬爾原有生活的大致描寫,《TOB》中薇爾貝特在故鄉小村裡平靜的生活。同樣是打破平靜生活的某場變故,《TLOU》的疫情爆發害死喬爾的女兒,《TOB》裡姐夫操辦的紅月祭祀害死弟弟。激勵事件的展示與出現時間二者略有不同,《TLOU》中亡女的喬爾哀莫大於心死,他是在遇見艾莉並接下火螢的任務後才有了動作性需求,即護送艾莉前往火螢基地,邂逅艾莉是喬爾的激勵事件;而《TOB》在Set-up階段薇爾貝特就已經明確了她的動作性需求——找姐夫復仇,因此越獄才是薇爾貝特的激勵事件。甚至我上文寫到比較老派的“Debate”橋段也可以一一對應,例如《TLOU》中喬爾與搭檔針對護送艾莉而產生的爭執,與《TOB》中薇爾貝特的親友與萊菲對復仇行為的勸誡。
兩部作品之間的相似點還有很多。例如同樣是無中生有的“虛構”的親情關係,又或是結尾處類似的道德困境與選擇。兩部作品與故事模板的相似點也有很多,但礙於篇幅這裡不把遊戲的全部劇情展開分析了。要說不同處的話在於,《TLOU》的故事更像是美劇劇本,它的段落感和章回感更為明顯,喬爾與艾莉在冒險的路上遇見不同的人並展開不同的故事;而《TOB》則更“遊戲”一點,它將幾乎所有的人物都展現給玩家,並引導玩家在不同的時間與地點一一去觸發這些故事。
費勁心思講了這麼多,又引用了這麼多晦澀難懂的概念是為了說明什麼呢?其實就是想要表述我不喜歡但又想推薦給各位的理由。這兩款遊戲,按我們行話來講,就是“匠氣”太重了。
這種充滿了“設計感”的“匠氣”不僅體現在故事結構上,故事內的“匠氣”也過重了。包括但不限於弟弟的冒險書與木雕店裡的羅盤,幾乎是立馬就會想到日後會有人代替薇爾貝特的弟弟去冒險;教會的雙胞胎工具人姐弟,同樣是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會有先死一個然後姐弟情深的戲碼;以及姐夫非常眼熟的人設和動機,也完全都是最終戰前可以猜測出的。一些小而精的故事設計是很加分的,這裡可以給出的例子是《如龍0》真島線的那塊手錶。但在故事結構已經如此匠氣的前提下,故事內容仍然充滿了諸如此類自作聰明的設計,與我而言,《TOB》的幾乎所有劇情都是可預測的,而可預測,就意味著無聊。
可預測和無聊的故事那麼多,上面剛寫過的《戰神5》也算一個,為什麼還要把《TOB》拎出來說呢。
因為《TOB》是一款JRPG遊戲。
在我為數不多的JRPG遊戲經驗中,無論再怎麼說JRPG的故事套路模板,每個遊戲的故事多少還是會有那一個讓人眼前一亮或是眼前一黑的獨到之處的。而完全循規蹈矩恪守成規去寫一個流水線故事,大多是歐美遊戲才幹的事,比如一開始提到的《戰神4》《戰神5》,或者什麼《神秘海域》《漫威蜘蛛俠》一類。能閱讀到一個正統JRPG班底寫出來的工業類型故事,對我來講是一個很新奇的事情。並不是想拉踩,但其實這也說明了,做一個平穩落地的及格分故事並不是什麼很難的事情。而JRPG的創作者們仍然熱衷於為玩家們“整個大活”,反而說明了他們還仍懷有著創作欲和表達欲,還沒有完全向商業低頭,仍然有廠商像當年的史克威爾一樣,做著屬於自己的“最終幻想”。
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傳說”這個系列IP,對前作以及前作的粉絲騷動一概不知。而對《情熱傳說》的炎上事件有了瞭解後,我認為南夢宮做出這樣保守的商業決定也是十分合理的。如我之前所說的, 雖然匠氣十足,但《TOB》與《TLOU》一樣,都是十分優秀,值得學習的商業遊戲故事模板。
但除此之外,我對故事還存有一處不滿,即沒有展現出薇爾貝特作為女主人公獨有的女性魅力。

這其實也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了。日本作為一個極其大男子主義的國家,它文藝作品中對於女性角色的呈現簡直是災難級。這一問題在近些年的作品中都沒有得到很好的改善。例如《水星的魔女》和《JOJO的奇妙冒險:石之海》,與《TOB》一樣,同樣主打系列首次女主角並大力宣發,實則是JUMP系男主人公的性轉體。我希望看到的女主角是如同新《Tomb Raider》裡勞拉·克勞馥一樣會有著迷茫、不安、害怕,並最終收穫成長的一個女性形象。而不是一個能完美適配男性主人公形容詞的女性主人公。薇爾貝特必須是殺伐果斷,被複仇“矇蔽”雙眼的形象嗎?這樣的冰山美人只能在假弟弟面前吐露真情感嗎?展現女性魅力除了做飯和女工就沒有別的方式了嗎?希望未來的JRPG能寫出更多更好的女性形象來打我的臉。
故事之外要說的是,我真的很喜歡《TOB》的收菜玩法。大概就是每半個小時可以收取一次遠航的獎勵,獎勵大概是什麼食材啊裝備啊素材之類的,也會有稀有收藏品。雖然獎勵算不上很豐厚,但是這個收菜玩法確實很上癮。有的時候哪怕不玩也會開著PS5,隔半個小時去收一次菜。
然後我也很喜歡《TOB》的裝備系統和戰鬥系統。裝備系統類似於“經驗值”或是“精煉”系統?類似於裝備某件裝備打怪時可以漲裝備的“經驗值”,經驗值滿了這件裝備的詞條就永久烙在你角色的身上了。我覺得算是有種鼓勵了“不要‘一鍵最強’走到底”的那種感覺吧,這種養成感和收菜一樣也挺讓人上癮的,不知道續作有沒有把這一項繼承下來。戰鬥系統可以自定義招式和打入異常狀態可以得到更多行動點數的良性循環戰鬥模式很戳我。但沒想到就在今年遇見了完美符合這兩點並在此之上有著更完善戰鬥系統的另一款遊戲,那就是玩一半太監了的《最終幻想:起源》(cnm真的太光汙染了)。
3 龍之信條2 5
寫完了兩個比較有話講的,再寫兩個沒啥話要講,而且是在同一天發售的遊戲,先說《龍之信條2》。
但我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評價這個遊戲,因為它實在是,太無聊了。
它講了一個比我預想的還要十倍無聊的故事,但它與上述的“可預測”的無聊還略有不同。打個比方,上述的無聊是你看完了《鯊捲風12345》之後去看《鯊捲風6》的那種無聊,而《龍之信條2》就像是你第一次看《鯊捲風》時的那種無聊。
不好,也不爛,但就是無聊。

所以還是來多聊一聊這遊戲的Gameplay吧。
雖然這遊戲的動作系統和戰鬥系統比起卡普空的其他遊戲算是相形見絀,但不得不說的是,這遊戲給我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好的法師戰鬥體驗。
因為我個人還是很中意長讀條法師的,FF14的主職也是黑魔,後面要寫的《艾爾登法環》也是玩法師,法師在這類遊戲裡確實是很難打的“爽”的一個職業,但我覺得《龍之信條2》做到了這一點。從讀條時的儀式感,到魔法擊中敵人的打擊感,再到大型魔法毀天滅地的動畫特效,以及一些小魔法產生的對戰鬥或探險的幫助(例如踩冰塊二段跳)和戰法牧編隊提供的安全輸出空間,會讓我真實的覺得,我在玩一個法師,而不是下一秒我就要開始滿地亂滾或是拿著棍子衝上去和小怪搏殺。
當然該吐的槽還是要吐。作為一個法師,兩大終極魔法之一的隕石術還限制地形,且隕石落點不能手動控制,且幾乎所有技能傷害都幽默的不行。那話咋說來著,法師是工作,魔弓才是生活。
然後就是,我還算是比較喜歡這遊戲裡一些謎語人式的解密。
比如在覲見斯芬克斯之前,能看到一副畫著前面的人拿矛戳不動斯芬克斯的壁畫。這應該是遊戲內唯一一處暗示,告訴玩家在解謎之後,要用弓箭射斯芬克斯屁股,才算是真正完成斯芬克斯的隱藏挑戰。類似的設計遊戲內還有很多,b站和機核裡都有找到,我在這裡寫多了也沒啥意思。

我覺得這些設計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僅限一次”和與之配套的噁心人的SL邏輯毀掉了這些巧妙的設計。由於我個人是有在遊戲前查看遊戲獎盃和攻略的習慣的,所以我算是提前瞭解到了斯芬克斯僅限一次不可重來的噁心之處,因此打的格外小心。試想一下如果有一個幾乎滿練接近通關的玩家遊玩至此,因為不知道要拿箭射屁股錯過了這一週目的斯芬克斯,那得有多絕望。以及那個初心者之證,哪怕玩家願意多花很多的遊戲時間在大地圖裡漫漫尋找那個初心者之證,他也要說不行,要多加上7天(還是3天?)遊戲日的時間限制來噁心玩家。幾乎就是完完全全噁心初見的一個設計。
4 浪人崛起 6
在正式聊《浪人崛起》的內容之前,我真的要搖旗吶喊,所有的遊戲廠商,日廠歐廠美廠,都給我把忍者組這一套遊戲內置聯網捏臉數據和幻化系統都給我抄來。
我本身是一個捏臉但是對遊戲人物顏值要求又很高的人。每次玩這種需要捏臉的遊戲都會花費很長的時間在找作業抄作業上,最終對作業的效果不滿推倒重來又喪失耐心亂捏一氣這種事也是屢見不鮮。《浪人崛起》的內置捏臉數據簡直稱得上我的福音。在排行榜上看到好看的就直接下載套用然後改個喜歡的髮色瞳色,不喜歡的地方微調起來也很簡單。幻化系統也是目前我玩過最好的幻化系統,除了必須要回據點不能隨時隨地想換就換以外,可以說是沒有缺點。
至於這部遊戲的劇情。其實我對它的劇情本身就沒啥期待,我對它的唯一要求就是能給我貧瘠的日本幕末歷史補補課。畢竟毫不誇張的講,我的三國的所有的知識來源,幾乎也是來自於光榮旗下另一款系列遊戲。我覺得從這個層面來講,《浪人崛起》算是圓滿完成任務了。

懂的應該知道這是在幹啥
但關於故事還是有兩個小缺點可以提及一下。一個是比較明顯的,當你選擇了某一陣營派系後,故事的走向並不會因為你的選擇而發生改變。畢竟本質上還是個歷史故事大河劇。但出現了上一秒我才救了某某某下一秒就要和他反目成仇這種存在明顯合理性問題的橋段時還是會產生一些很強烈的矛盾感。第二是嚴謹的主線歷史故事之外,一些支線是包含有一些浮誇戲謔的野史成分的。正如《明日方舟》傳奇構史家妮芙的主張一樣,“野史可以不夠史,但是一定要夠野”,很明顯遵循歷史原教旨主義的光榮就沒能做到這一點,沒能把野史裡足夠有趣,足夠吸引人的地方表現出來,感覺上是挺可惜的。
然後說到Gameplay部分。我真的要說一句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話,我是真的很喜歡《浪人崛起》的開放世界設計。
一來我覺得《浪人崛起》的開放世界是一個很健康合理的地圖大小,包括他細化後的每一小塊區域也都是在我接受範圍之內的大小。在過大的地圖裡跑圖會讓我產生極強的疲憊感,而《浪人崛起》在我產生疲憊感之前就已經換到第二張新的地圖裡了。而小區域劃分的更細更小也使得互動元素密度的提高,只需要走兩步就能看到一個新的清據點或者是新的小boss,清圖的時候也省去了找來找去的麻煩。二來其實我感覺《浪人崛起》的開放世界引導做的也挺好的。無論是地圖上標出來的交互事件,還是弱引導的聽聲音尋找流浪貓和樹上綁紅繩引路的隱藏boss,都是不用額外花心力動腦子,簡單輕鬆就能完成的清圖。畢竟開放世界並不是也並不能成為遊戲的主要玩法,這樣“弱保軟”的設計使得玩家聚焦於更為核心的故事劇情或是戰鬥上,以我的視角來看是一種很不錯的資源整合和避免資源浪費的手段。
5 女神異聞錄3 Reload 7
讓我來盤點這部作品其實我心裡還是有點沒底的。因為哪怕白金了,我也沒打這一代的隱藏boss伊麗莎白,我也沒有玩後來通行證推出的後日談DLC。所以就簡單聊聊一筆帶過了。
關於P3的故事可以去翻閱一下我去年年終總結裡對於P3P的分析。將近20年過去了,其實P3的自殺議題以及它向死而生的主題仍然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包括像今年在大陸公映,由香港導演卓亦謙執導並斬獲臺灣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影片《年少日記》,或者由三宅唱執導入圍柏林電影節論壇單元的《黎明的一切》,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新導演去觸碰這個敏感的問題,也能在當下壓抑的社會氛圍裡察覺到一些端倪。包括從我給出的例子中也能看出來,對於歐美來講這一話題也許會有一些文化衝擊或是宗教信仰上的禁忌,但放眼兩岸三地與日韓來看,這一問題仍然是有普世意義,討論價值與上升空間的。只不過20年前原版《女神異聞錄3》的年代與現在,對於這一現象的成因是有所變化的。《P3R》如它宣傳的“原汁原味”一樣,也只是將故事移植到了現代,所以它故事的表達就並不像原版那樣深入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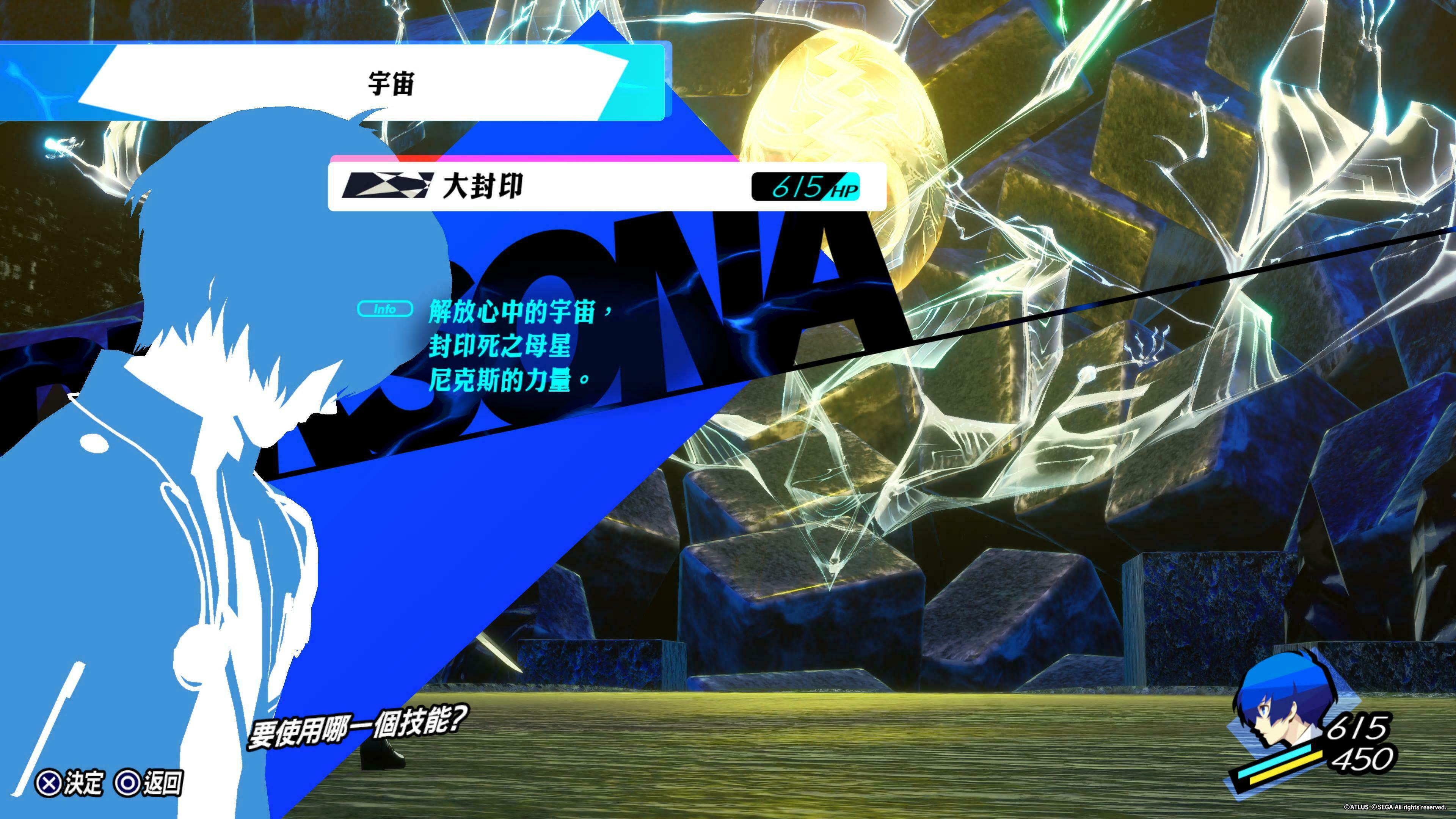
其次我對這個遊戲最不滿的地方,就是它新加入的“降神(神通法)”。
首先這個設計源自原版P3的合體技,為了給這些技能適配上炫酷的特效,從數量上就已經砍了一大半。而在P3P裡,它是以道具的形式,需要“有償”購買和使用的。到了P3R的降神,幾乎可以是“無償”“無條件”“無責任”的無限次使用下去,甚至它還很貼心能無視屬性抗性。並且在遊戲前中期,就已經能夠解鎖十分強力且好用的神通法了。這也就導致例如死神的一回合兩動,或是單子之門裡無吸反怪的一些特性很輕易就被逃課了。雖然可以看出來從P3到P4到P5難度遞減的趨勢,但對於這種破壞遊戲性的設計,我覺得還是少來點為妙。
6 最終幻想7:重生 8
終於到我今年最喜歡的一款遊戲了。
我覺得去討論這款遊戲的故事啊表達啊的確還為時尚早。因為確實也正如許多玩家批評的那樣,到目前為止它還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但也能從目前的諸多設計裡管中窺豹,最起碼,它沒有像《戰神》那樣去copy《復聯》啊《速激》啊,走一條簡單的路。
《FF7》,作為傳說中能夠復活一家公司這種級別的IP,尤其是在第一部DLC揭露了扎克斯沒死之後,它完全可以把大夥喜歡看的端上來,真當SE不知道玩家們想要什麼喜歡什麼嗎,那麼大一家公司的市場調研吃乾飯的嗎。它當然也可以賣情懷,而且完全可以說它配得上賣情懷這三個字。但是它沒有這麼幹。這就是我《緋夜傳說》裡寫的,這一輩老東西們還是有屬於他們的藝術追求在的,雖然現在還不知道結果如何,但作為玩家和粉絲的我們,看到有這樣的創作態度,我認為是完全值得為之等待的。
關於新的劇情走向筆者亦有許多假設與猜測,不過都如上文所講的一樣,靜候佳音,慢慢等第三部就好了。
既然劇情無話可講,那《FF7RB》故事裡還有啥很亮眼很優秀的地方嗎?
有的,那就是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更細緻一點,特指愛麗絲與蒂法。這兩位女性角色寫的好到讓人感覺不應該出現在JRPG的劇本里。
愛麗絲的獨特之處,在於她是一個極其少有的,在JRPG中存在著“背德感”的女性角色。她對自己做出的某些行為是懷持著後悔與愧疚的態度的,但她的慾望,她的責任感,她個人的主體意識驅使著她不得不這樣做。從一開始站在鐘樓上遠眺米德加,到旅途中不停抒發著對家庭和母親的想念可以看出,其實愛麗絲對離開家庭離開母親是有一定負罪感的,其實對應著的就是東亞傳統觀念中的“不孝”。尤其是在第一部鋪墊了愛麗絲的身世與第二部再次Call back之後,這種不希望深愛著自己的養母為自己擔心卻又不得不踏上冒險的這種內心矛盾體現的淋漓盡致。可能這一處對於普通玩家而言並不是這麼明顯,那麼到了中期海灘的個人劇情中,愛麗絲明確說出“我所想象的復仇過於狠毒甚至連自己都感到害怕”這樣的臺詞時,即使現實生活中幾乎不會出現這種血海深仇,但這樣複雜糾結的內心糾葛才是更接近於正常的人類情感的,也才更容易讓玩家有與愛麗絲共情的餘地,會讓玩家去心疼愛麗絲這樣一個外表很堅強樂觀,內心其實很脆弱的小女生形象。而真正巔峰造極的人物塑造與背德感的體現集中在貢加加與扎克斯父母會面一段。她對扎克斯父母隱瞞他們兒子死訊的一點內疚,對扎克斯睹物思人的一點懷念,對克勞德暗自萌發的一點情愫以及對自己移情別戀的一點羞愧,這一段臺詞和人物情感的描寫真的非常多層次,非常推薦各位反覆品味一下。
愛麗絲在感情上體現出的這種背德感,從第一部RE時的“你可不要愛上我了”就已經有所鋪墊。而到了RB中,除開上文所述的貢加加見父母一段,愛麗絲好感度最高時的摩天輪約會說出的“我在找的是你,我想見的是你”,以及結尾在幻想中的教堂花田裡擁抱時所說的“消失吧,罪惡感”將這種矛盾的情感宣發的更為露骨。這種感情很像《花與愛麗絲》中的有棲川徹子,一個知道閨蜜喜歡但仍然喜歡上了同一個男生的青春期女生形象。而這樣立體、多面、真實,甚至同樣散發著青春氣息的女生形象,是真的在JRPG裡很少見的。

而蒂法也正如廣大男玩家所述的那樣,確實是一個更符合男性審美的,集多重優點於一身的,在文藝作品裡也比較隨處可見的,更貼近於虛構和想象的女性形象。她青梅竹馬雙向暗戀,她身材火辣面容姣好,她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就這樣一個賢惠的、完美的女性角色,是很容易寫成花瓶或者男主角的附庸的,而原版中蒂法的定位也於此大差不差。RB中編劇是如何妙筆生花拯救蒂法的呢,這就要提到另一個比較方法論的寫作技巧了,那就是給你的女性人物增加一個男主角不知道的秘密。編劇需要讓這個角色,通過這個小秘密,這個男主不知道的事,來獲得有別於男主和故事的另一個目標,來獲得屬於自己的角色驅動力,來獲得一個獨屬於這一位女性角色的主體意識。在RB裡很明顯,蒂法被星球守護者Weapon吞下這個橋段就發揮了這個作用。由於RB裡並沒有蒂法過多的戲份,但我們仍可以在結局中窺見,由於蒂法得知了克勞德和我們觀眾都未知全貌的信息,很有可能蒂法是一個將要在第三部中發揮重要劇情功能的女性角色。這樣“公主救王子”的戲碼出現在JRPG的敘事中也是很令人驚喜的。說明哪怕是日本遊戲編劇,他們的性別意識也是在與時俱進的。

而說到Gameplay部分,我其實認為RB比起RE,戰鬥系統算是退步了的。原因就在於比起RE,RE的戰鬥系統更加側重於動作部分,而更多地削減了策略性的部分。我很喜歡RE戰鬥系統的地方就是它同時有著即時戰鬥的爽快以及老式回合制燒腦的策略性。其實不妨回想一下,在RE裡給防具打上屬性加魔法珠就能逃課的Boss有哪些。我個人而言立馬能回想起的就是主線流程裡克勞德愛麗絲雙人戰的地獄屋和最後神羅大廈裡巴雷特與愛麗絲戰的電系機器人(JJC應該也有但記不清了)。在前作中,我可以通過調珠子用弱點魔法等行為來讓我的戰鬥難度降級。而到了RB中,哪怕多了雙屬性魔法珠,能逃課的場景依然不多。甚至它還加入了全新的,針對玩家手部乘區進行考驗的Boss奧丁和VR薩菲羅斯。我自詡我的遊戲水平不低吧,也仍然被這兩個boss噁心了一下。我其實真的挺好奇一般玩家對這種設計的看法的,是大家都打低難度不折磨自己呢,還是人均動作遊戲天尊菜就多練。於我而言吧,還是希望能有更多與Boss與設計者“鬥智”的這個環節,但其實從SE半回合制戰鬥系統的鼻祖《FF15》來看,感覺他們是沒考慮過加深遊戲策略性的。
其次我覺得最大的設計敗筆是容錯率低,這是遊戲體驗差的根源問題。你要說那些小遊戲真的很無聊折磨,其實倒也不至於(除了海盜船打槍),鋼琴和打牌我玩的甚至還是很開心的。挫敗感強重複度高的根源還是容錯率太低了。像是青蛙跳,被碰到一下就死,還不停給你加障礙。像陸行鳥鑽圈,就是硬性要求每一個圈都要過。以及像是賽鳥,碰到一個障礙物就可以準備remake了。這種容錯率低的問題不止體現在小遊戲上,如果我記錯了歡迎各位指正,但是我真的記得前作的JJC和AI挑戰最多也只是5連戰。這次前置就來好多個10連戰,最終挑戰和隱藏挑戰也都是10連戰。打10連戰真的就是容錯率低試錯成本高再外加精神壓力大的數重摺磨,放寬一點條件可以使得遊戲體驗立馬提升很多,小遊戲也是同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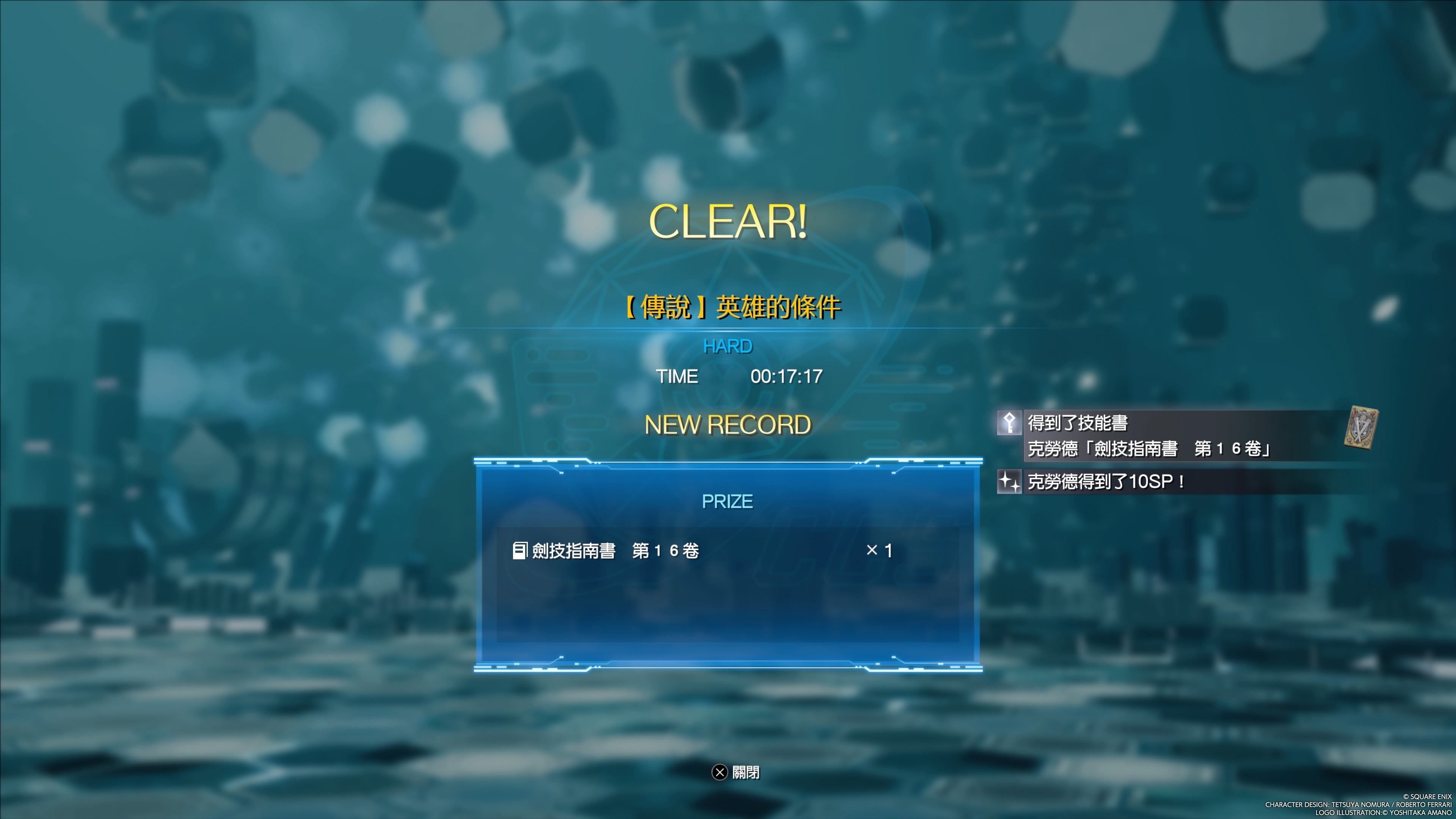
最後還是提一嘴開放世界吧。其實和上面《浪人崛起》一樣,我還是挺喜歡《FF7RB》的開放世界的。不煩神不費事,跟著地圖走也不會漏東西。但比較難繃的是他竟然把這麼弱保軟的地圖設計帶到了迷宮設計當中,舉個例子,最後古代種神殿愛麗絲的解密,正常來說應該是用來鋪路的魔晄總量是固定的,我要走哪條路就把哪邊的魔晄吸出來移到另一邊去,我覺得這樣的設計很合理吧。當我看到愛麗絲鋪好一條路之後裝置裡的魔晄和路都固定死了我的人真的是驚呆了。一個JRPG的迷宮竟然可以敷衍,弱保軟,一本道成這樣嗎?真被十年前的《TOB》爆殺了吧。第二是這個和開放世界配套的裝模作樣的合成系統。我最後做白金的時候合成獎盃差幾個素材,我不知道諸位知不知道,就在我準備打開遊民星空查詢一下這些素材是哪些怪掉落的時候,我TM竟然發現,這遊戲裡的素材全部都是可以在賽鳥人妹妹的商店買到的。那你TM裝模做樣有模有式地搞一個採集系統和合成系統是為了幹啥,就喜歡玩家為了經典時尚小垃圾多繞點路跑點圖嗎?最後的最後,我真的他媽繃不住這個遊戲的光照系統,每次進出一個有光暗變化的地方都要吃滿一個閃光彈。配合上這遊戲高的離譜的畫面亮度和對比度,不誇張的講,玩這遊戲的兩個月我完整地用完了一瓶新開封的眼藥水。
7 艾爾登法環&黃金樹幽影 7&8
在寫這遊戲之前我覺得有必要先疊個甲。本人只通關過《血源》,《惡魂重製版》《黑魂3》與《只狼》都大約只打到第一個boss就玩不下去,除此之外沒有玩過其他任何魂遊以及類魂遊戲。我深知自己不是這款遊戲的受眾群體,我玩這款遊戲是因為有一個對我而言很重要的人,她很喜歡這款遊戲,也很喜歡宮崎英高。
雖然今年這篇文章一直在講故事,但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講《艾爾登法環》的故事。因為我沒有辦法去銳評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我們就不談上文提到的“救貓咪”或者“英雄之路”故事模板了,我們拿最簡單的,小學生寫記敘文的六要素來說事。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
時間?不知道,反正在環碎了之後,反正也不重要。地點?交界地,雖然根本不知道這是個什麼鳥不拉屎的鬼地方。人物?更是迷因。我是誰?不知道啊?瑪麗卡女王是誰?也不知道啊?開頭一串報菜名式的人名都是誰?到遊戲結尾都沒給你解釋明白。起因?我究竟為啥要當艾爾登之王?我的驅動力是什麼?我當王之後的目標是什麼?一概不知。經過?這是唯一明白的,幾十個小時的遊戲內容就是經過。最後的結果呢?當了王之後咋了,交界地變成啥樣了,燒過的樹和王城有沒有災後重建?都tm不知道,反正就“落葉傳來訊息”了。

我知道這時候可能會有人跳出來槓,說這些東西遊戲裡面的物品說明有,遊戲官方設定集裡有,扒開遊戲的代碼廢案裡面都有。但是要明白一點,一個遊戲作為一個消費品而言,在呈現給你的消費者的那一刻就該是完整的。不應該在消費者追求一個“完整”的故事體驗時,強行要求消費者去付出額外的時間精力與金錢。為什麼我要對此保有如此強硬的態度,因為我唯一通關過的魂遊《血源》告訴我,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血源》的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就要比《艾爾登法環》清晰的多。
當然也不是說《艾爾登法環》的故事一無是處。很明顯艾爾登法環在世界觀的設定上是下了大功夫的。這樣詳盡的設定的確是很利好玩家主動探索和二次創作的。它在社區有如此之高的熱度也是理所應當的。

那麼關於法環我還想說的是什麼呢,是遊戲內的文本與翻譯。
怪不得這次是隻能用英語配音,我不知道GRRM參與了多少,但是這個英文的文本質量比起《血源》,比起傳言是用英文寫作的《FF16》要高上了太多太多。完全不像是非英語母語者寫作的水平。而與此同時,中文的翻譯可以說是一坨狗屎。
由於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我個人是更傾向於使用繁體中文進行遊玩的,也算是為了避免“精神鐘塔的瑪利亞修女”這種災難翻譯。而這次,我不知道是哪個天才想出來的,他們竟然把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的翻譯統一了,導致我都不知道該罵哪一邊的本地化翻譯組。
首先我們來看法環裡的人稱代詞。法環和其他文藝作品都一樣,說話者使用的人稱代詞,語氣詞,用詞習慣是可以暴露出這個人一定的人物特徵與形象的。可以著重關注第一次遇見菈妮時的對話,這裡菈妮使用了極為特殊的一個人稱代詞——“thee”。這是一個極為古典、老派,常見於莎翁劇裡的人稱代詞,它可以看做“you”的古稱。它在中文中有著直接對應的翻譯,即“汝”。以及哪怕聽不懂也可以感覺出來的,菈妮說話時使用的一些對仗詞,她語句中包含的韻律美。都可以初步推斷出菈妮是這麼一個遺世獨立,沾滿書卷氣的人物形象。而中文翻譯就是很直白,很冷冰冰的“你”,同時也沒有將行文的對仗關係,音節韻律給翻譯出來。
第二是和人稱代詞類似的,針對特定人物的稱謂。這裡我們看DLC中的人物金針騎士蕾妲。她針對不同人使用的都是不同的稱謂。例如針對米凱拉,她一直都尊稱為“Kindly Miquella”或者“Miquella the Kind”,這裡保留原意的話我更傾向於翻譯為“仁慈的米凱拉(大人)”。針對梅瑟莫以及其他男性角色,蕾妲使用的稱謂是“Sir”,即某某“閣下”或某某“爵士”,在這種語境下我更傾向於認為是“爵士”。而對於託麗娜,蕾妲使用的是“Saint”,即“聖·約翰”“聖·喬治”中的那個“聖”,是帶有強烈宗教意味在裡的。這些稱謂很好地體現了蕾妲是持有嚴格等級制度觀念,懷持著騎士道精神的性格特徵,完全可以看做是最後雙方意見不合而相互對峙的伏筆。而在中文翻譯中,這些獨具特色,體現人物性格的稱謂,全部被翻譯成了某某“大人”。

我相信網絡上b站上隨便找一找都有總結的比我更好,翻譯的比我更到位的糾錯文檔或者視頻,這裡我就不多賣弄我的三腳貓英語水平了。我覺得重點還是得多提升自己的外語水平,就像是四二老師說的一樣,就算是當二等公民,也得有當了二等公民的自知之明。
說迴游戲,我覺得我是為數不多喜歡DLC多於本體的玩家。我感覺DLC的地圖設計和本體都不是同一個水平。雖然DLC有些地方也很大很空,但是地圖整體的聯通性和統一性,完全不像是本體那樣,整的跟《P3R》一樣,到了一個新的區域就全換一個美術風格。並且DLC的地圖大小,就是我能接受的最大的一個魂遊的遊戲大小。本體的圖真的太大了,而且其實仍然充斥著許多工業化的痕跡。比如地圖上看到法師塔就知道是解密然後拿一些法術相關獎勵,看到小黃金樹就知道是打怪然後爆露滴。包括DLC被詬病許多的幽影樹碎片的設計,我覺得對應的就是傳統RPG裡找怪刷級的一個邏輯。而我個人就是更喜歡刷完級之後再去推圖打boss的,我玩法環本體的時候也是先將智力刷到了80點才開始推圖。
除此之外法環還充斥著各種我難以理解也不想理解的遊戲設計。比如傳說中的根據PVP來削弱武器技能。DLC的前置boss蒙格,我臨摹視頻中的打法上一樣的buff用一樣的裝備,視頻裡一個彗星亞茲勒能滋死,而我怎麼滋都skip不了二階段。我都玩法師了,不圖的就是這一口站樁輸出玻璃大炮嗎,更何況是一個範圍如此之窄,前搖僵直無比之長,使用起來如此之繁瑣的法師終極大招。單機遊戲的輪椅平衡性真的這麼重要嗎?還有地牢裡數不清的隱形橋隱形門和踩閘刀。這些設計給我的感覺就是硬推他的那個諫言系統。明明不是強制聯機遊戲,打起來不聯機的體驗卻跟吃了屎一樣。可能宮崎英高是在苦口婆心地教育我,孤僻的下場就是一個人連享受《艾爾登法環》的資格都沒有吧。

唉,如果和她一起玩的話體驗可能確實會好上不少吧。
8 寂靜嶺2重製版 8
今年第二喜歡的遊戲,但反而感覺沒啥可聊的。
我們常說什麼形式大於內容,內容大於形式。《寂靜嶺2》很明顯就是一部形式大於內容的故事。
《寂靜嶺2》的故事其實很簡單,而且其實我早年在做《寂靜嶺》電影分析的時候就已經對《寂靜嶺2》的故事有所瞭解了。那《寂靜嶺2》是如何達成這樣深入人心的故事效果的,少部分原因是我開頭講的,依靠於一個普世性強的,大眾所熟知且容易共情的親密關係(夫婦),而剩下的,全都依靠於他講故事的技巧。
而且這種技巧大部分也都是遊戲的交互性所獨有的,雖然說這遊戲的玩法不重要,但基本都是玩家通過遊戲所引導的故地重遊場景重現,來去主動地接收信息,抽絲剝繭得到故事的真相。因此我覺得這遊戲的影視化其實還挺難做的,因為很難去復原遊戲中那種未知的神秘感,並且一旦過於還原遊戲的流程,這種跑任務式的遊戲感就直接露餡了。因為遊戲需要繁瑣的流程來擴充遊戲時長,來使得一個簡單的故事複雜化,而電影則使用不同的手段來達成這一效果。聽說《寂靜嶺2》的影視化作品將要推出了,只能說謹慎地期待一下吧。
此外就是它用符號與意象講故事的能力。例如最經典的三角頭形象,在遊戲中其實有比較明確的指向性,例如在下樓梯前往監獄前的寂靜嶺博物館裡的掛畫上可以看見,它是與中世紀的瘟疫醫生所戴的頭罩有關聯的。因此三角頭的表意其實應該更傾向於“疾病”“病魔”。當然也可以由三角形對應陽性,圓形(一說倒三角)對應陰性的符號學理論來解讀為男性陽具或是性慾。以及詹姆斯站在絞刑臺上的自殺意象,安潔拉內心的火焰等等,這種符號與意象的模糊性與多義性( ambiguity )也保有了諸多可供玩味的解讀空間。

最後還是要感嘆一下這個外包水平如此之高。雖然我知道《寂靜嶺2》的故事但畢竟沒有玩過原版遊戲,重製版裡的謎題質量高到我懷疑它並不是出生在2024。畢竟眾所周知的,2024年這類遊戲的平均解密水平應該是什麼考眼力啊,試錯啊,一元二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之類的。我是聽了機核的節目之後才知道這些謎題都是翻新了的,原有謎題做成了收藏品處理。以及山岡晃親自重置的OST,也是把這個遊戲帶到了更高的高度。其實我真覺得今年TGA可以把最佳音樂頒給《寂靜嶺2》的,但一想到輸給的是《FF7RB》,那好像確實也沒啥辦法。
9 暗喻幻想 6
終於到最後一個了,年度最大CJB,阿特拉斯歷時不知道多少年詐騙之作,《暗喻幻想》。
其實可以藉著這款遊戲,來跟大夥聊一個遊戲編劇真的很愛寫,但是真的又怎麼都寫不好的劇情橋段,“反轉”。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一個最普通,最公式化的反轉。此處我要Call back本篇文章的第一位受害者,《戰神5》。在那裡我就寫到,劇情裡有一個完全意料之內的反轉,那就是奧丁假扮提爾。
這個反轉公式在什麼地方呢?首先一救出提爾的時候,假提爾就告訴奎爺他放下屠刀一心向善了,此時兒子阿特柔斯和腰上掛的人頭都在提醒你,這個提爾好像不太對勁,我們的好大奎非常公式化地為他辯解兩句先打消觀眾的疑慮,讓觀眾放下戒備,“也許就是當戰神當累了,我太懂了”。當假提爾到達據點之後,依然在鋪墊這一條線,繼續讓觀眾加深這個提爾不太對勁的印象。然後反轉發生,奧丁揭露真面目並殘忍殺害一名無辜好市民。緊接著反轉之後,腰上掛著的人頭和芙蕾雅立馬告訴你,奧丁這個逼太狡猾了啊,他能三十六變七十二變,我們的一舉一動早就被奧丁變的烏鴉盯著了啊。
這就是一個最基本,最公式,最套路的反轉。編劇引導觀眾,讓觀眾首先發現有一絲的不對勁,緊接著又插科打諢轉移觀眾的注意力,反轉發生之後立馬開始找補。觀眾心裡一尋思,還真對,他早就給我鋪墊好了。但這樣的反轉,它也就只具備一個普通情節點的意義了。一個真正好的反轉是得如同字面含義一樣,得對劇情產生巨大的轉折,也得讓觀眾真的驚呼“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
那什麼是一個好的反轉呢?正巧在同屬阿特拉斯的遊戲裡有一個例子,那就是《女神異聞錄5》。

在《P5》本篇的最終階段,我們得知天鵝絨房間的主人伊戈爾是偽神假扮的,而真正的伊戈爾在被囚禁之前幫助我們覺醒了力量,並在得救之後於絕望之際再次幫助我們擊敗了偽神。這樣的反轉就是一個在情節上有著重大意義的轉折點,同時,雖然這個反轉的草蛇灰線沒有在遊戲內得到很好的體現,但是玩家是可以通過聲優的變化察覺出一些馬腳的。但由於聲優田之中勇老師的離世,這樣細微的馬腳並不需要刻意的引導也會被玩家自發性地自我說服。在揭露真相的那一刻,才會發現這一切的佈局都是那樣歐亨利式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此處應該會有人疑問,為什麼不舉明智吾郎的例子。因為首先,在我的視角,明智吾郎是反派臥底這件事阿特拉斯就沒想著要藏。不然他也不會起明智吾郎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名字。其次,從明智吾郎就可以看出,阿特拉斯寫反轉的能力真的特別的差。不知道諸位還記不記得《P5》裡越獄佈局的橋段了,在雨宮蓮要回憶起某些重要情節時,阿特拉斯竟然用“吐真劑起作用了頭好痛”這種簡直可以稱得上是低劣的手法,來“強行”讓雨宮蓮“不記得”某些情節。這種寫法在寫反轉,寫驚喜橋段的時候都是大忌,這不就是明晃晃告訴觀眾,注意看,接下來我要反轉了。
孤例不證,阿特拉斯駕馭反轉的能力差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例如P3裡理事長這個角色,完全就是為反轉而生的一個工具人。還有P4裡的足立透,這個去年已經說過了,作為一個推理核心劇情的遊戲,為了設計反轉而把故事裡的線索全部抹掉簡直就是本末倒置。不過我懷疑本來他們就沒想為足立透的反轉預留伏筆,說不定還因為覺得設計這樣一個人畜無害型角色反轉當幕後黑手很成功而沾沾自喜。
不然很難解釋為什麼阿特拉斯如此普通卻又如此自信,他在《暗喻幻想》裡,加了得有七八個理事長級別,足立透級別和明智吾郎級別的弱智反轉。
從“哈哈,沒想到吧,我就是死不了”的傳奇耐殺王路易,到“哈哈,沒想到吧,其實我才是大壞逼”的大主教,再到“哈哈,沒想到吧,其實我也是壞逼”的聖女蕾拉以及不計其數的弱智小反轉,感覺阿特拉斯每一次都騎在你臉上在問,“怎麼樣?這個反轉有沒有震驚到你?”,乃至於最後的最後都要以一個弱智反轉給故事收尾,“哈哈,沒想到吧,其實我是你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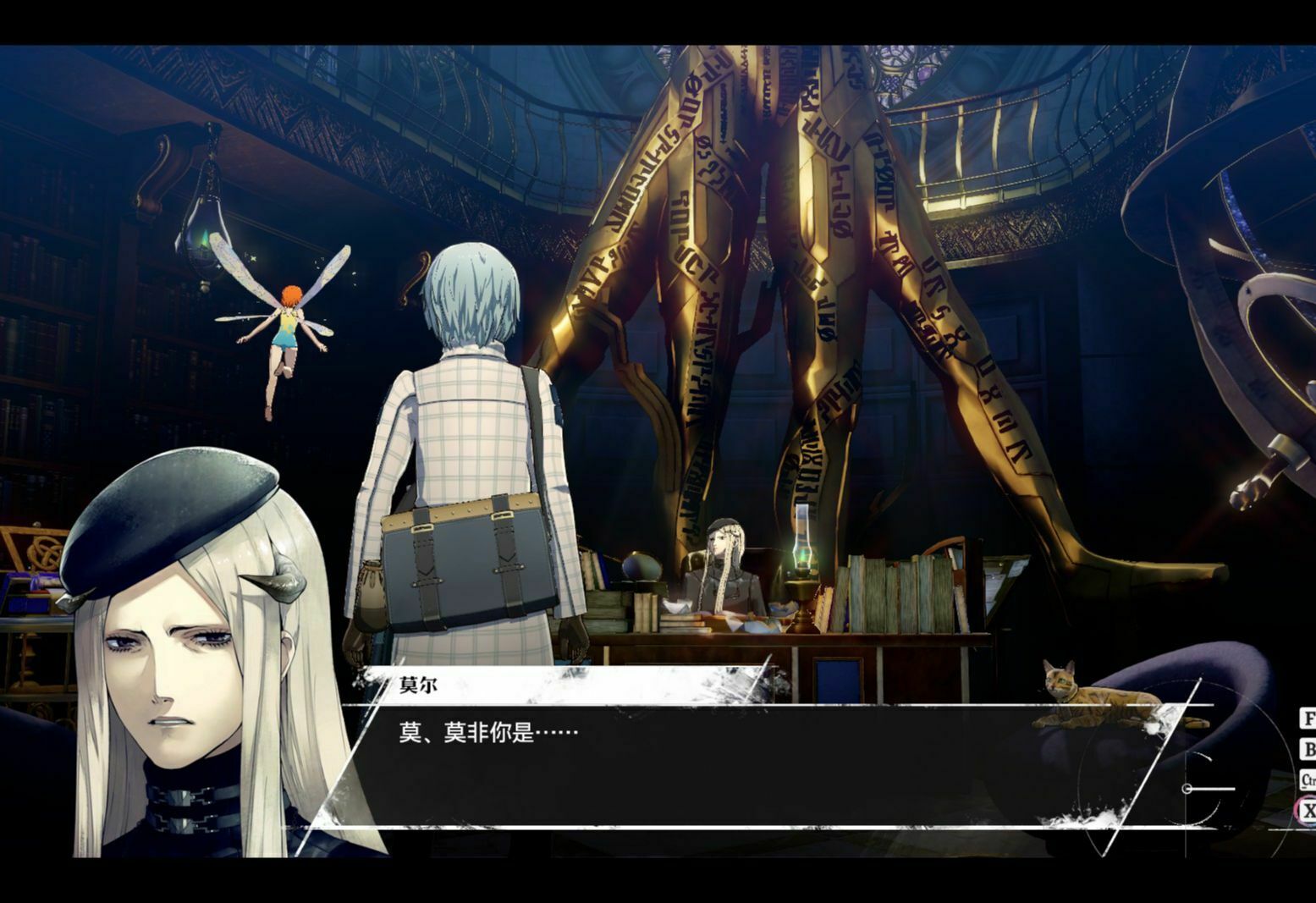
我是恁爹!
真的,大可不必這麼侮辱人的智商,你的每一處反轉我都想得到。
然後說一下這遊戲的表達吧,這遊戲的表達主要有兩個也都比較明顯。一個是種族歧視,另一個是民主。
第一個問題一開始大張旗鼓地鋪墊了好久,又是當街砍頭示眾又是不讓進店的,但講著講著也不知道是阿特拉斯沒想好怎麼處理這個問題,還是直接就給忘了,這麼大個事基本上就只存在於主角的口號和同伴們的臺詞裡了。那畢竟你是JRPG嘛,喊著友情啊羈絆啊什麼的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了也很合理。但是當了王之後直接就變烏托邦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隔壁《FF16》好歹還死了個克萊夫呢。我知道種族議題是很具有當下性和現實意義的一個問題,但要只是這麼蜻蜓點水地提一下都能有這麼高媒體評價的話,我真的要替《悲傷逆流成河》伸冤,它可是國內反校園霸凌題材電影的先驅啊。
第二點我其實覺得更可惜。關於民主的話題這裡不便討論太多(已經被退稿一次了),這裡推薦大家去看一看希拉里敗選時的白宮講話。在民主的制度下不應該只看如何贏,更應該看如何體面的接受輸。很明顯遊戲裡的路易、主教,都沒能做到這一點,蕾拉的講話有點那個意思但仍不足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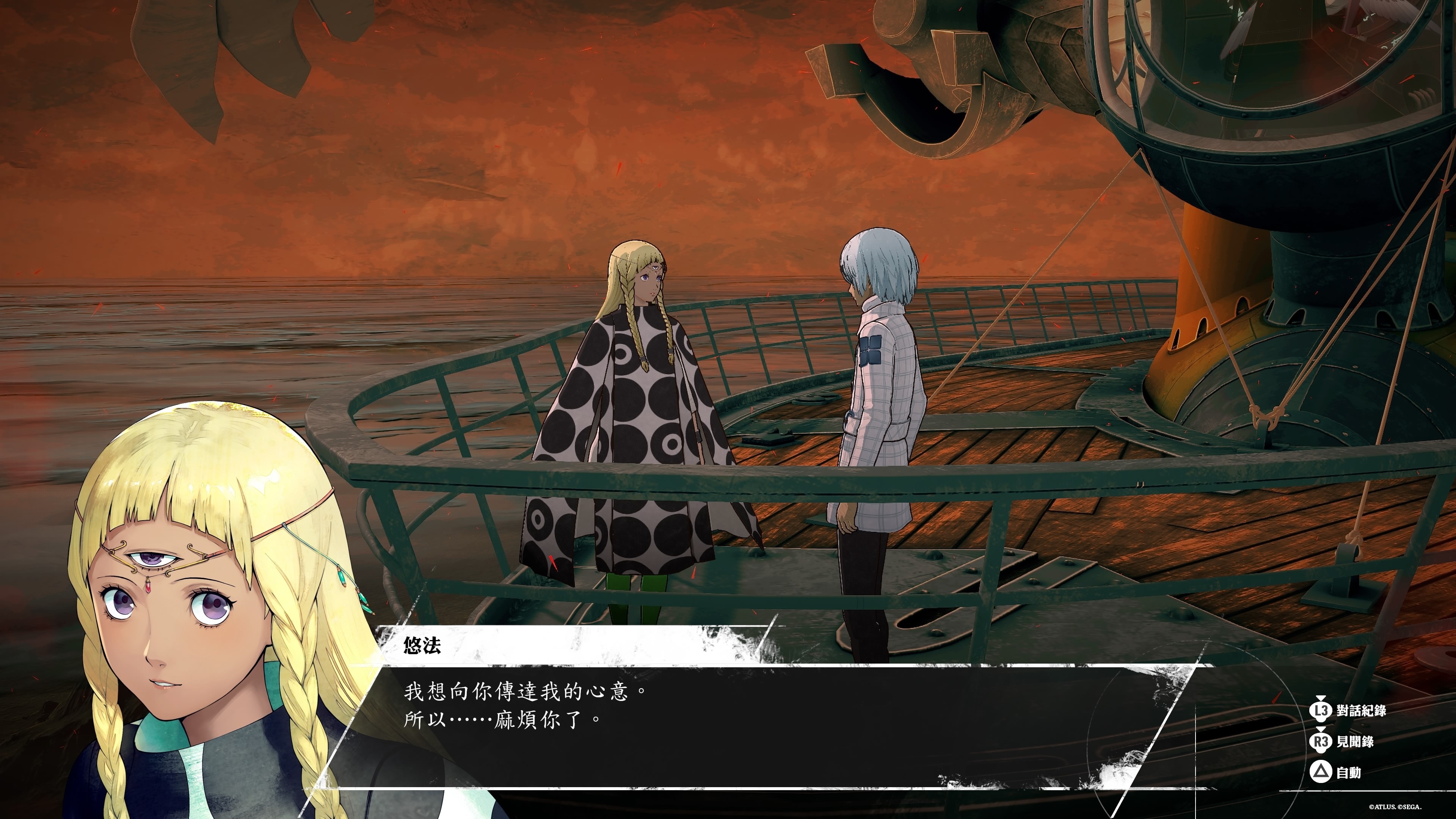
其實關於這遊戲還有挺多值得罵的,但是罵累了,就先這樣吧。
總結
費老大勁總算是寫完了。也不知道有沒有人能看到這裡。如同一開始寫的那樣,今年對我來講是比較糟糕的一年,可能算是把一些戾氣藉由這篇文章抒發出來吧,這次算是火力全開模式了(笑)。如果我誤傷到了你喜歡的遊戲,你也可以攻擊我最喜歡的遊戲《FF7RB》。
寫到後面真的好累好睏,寫到後面也越來越隨意越來越敷衍了(),今年玩遊戲的時候都沒怎麼截圖,也懶得開遊戲一個個截(只好亂jb加了)。但是,好歹還是把今年份的總結堅持下來了。也希望明年還能有這種熱情和精力坐在電腦面前碼字吧。嗯,今年就不談什麼遠大理想了,先好好活著再說。
然後的話,如同開頭說的,想把手裡一些太監了的遊戲繼續玩完。也歡迎諸位來給我推薦新的遊戲,或者是想聽聽我獨特看法的遊戲。電影也行。
那就這樣吧,辛苦看到這裡的諸位,若是有緣相信還能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