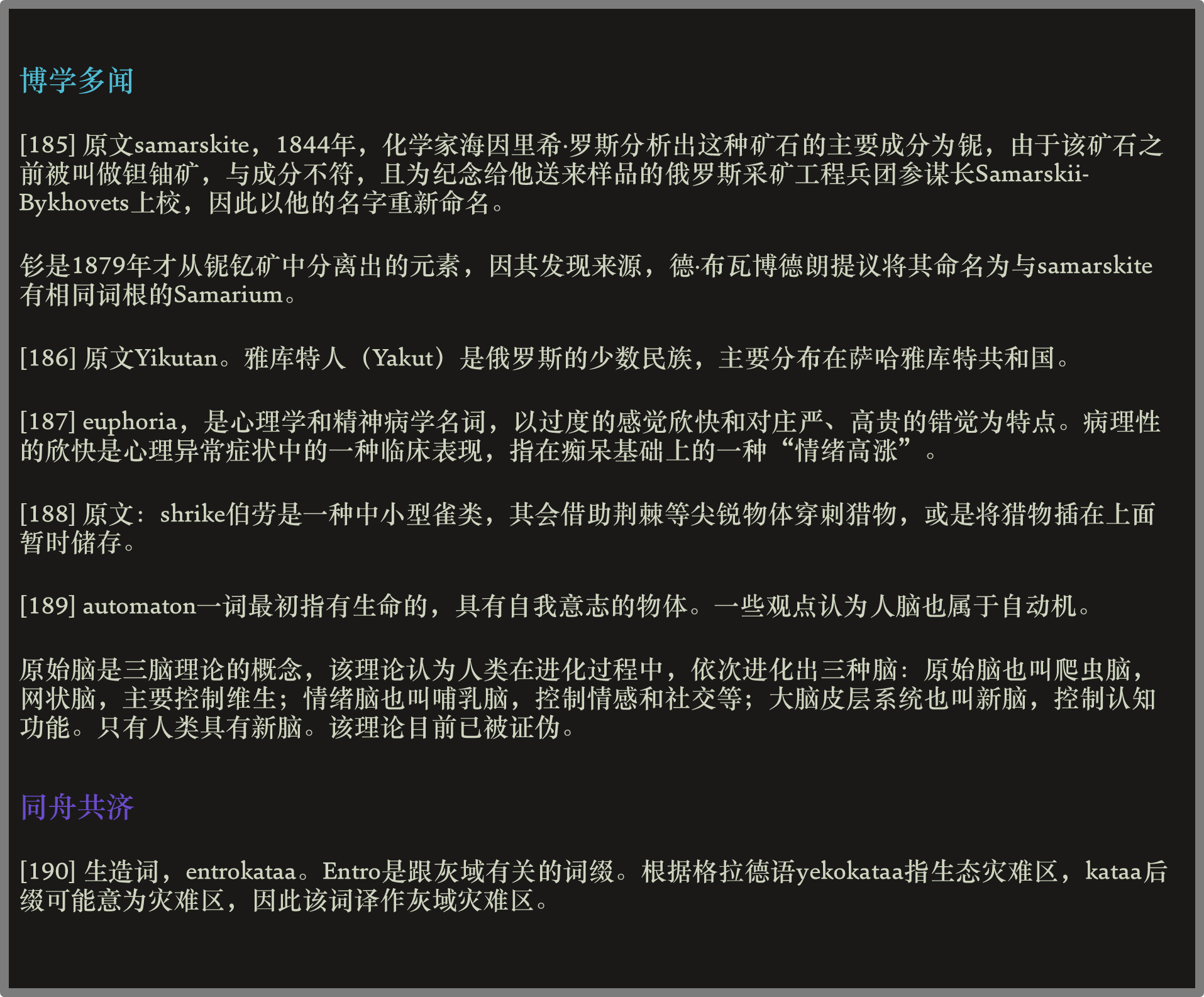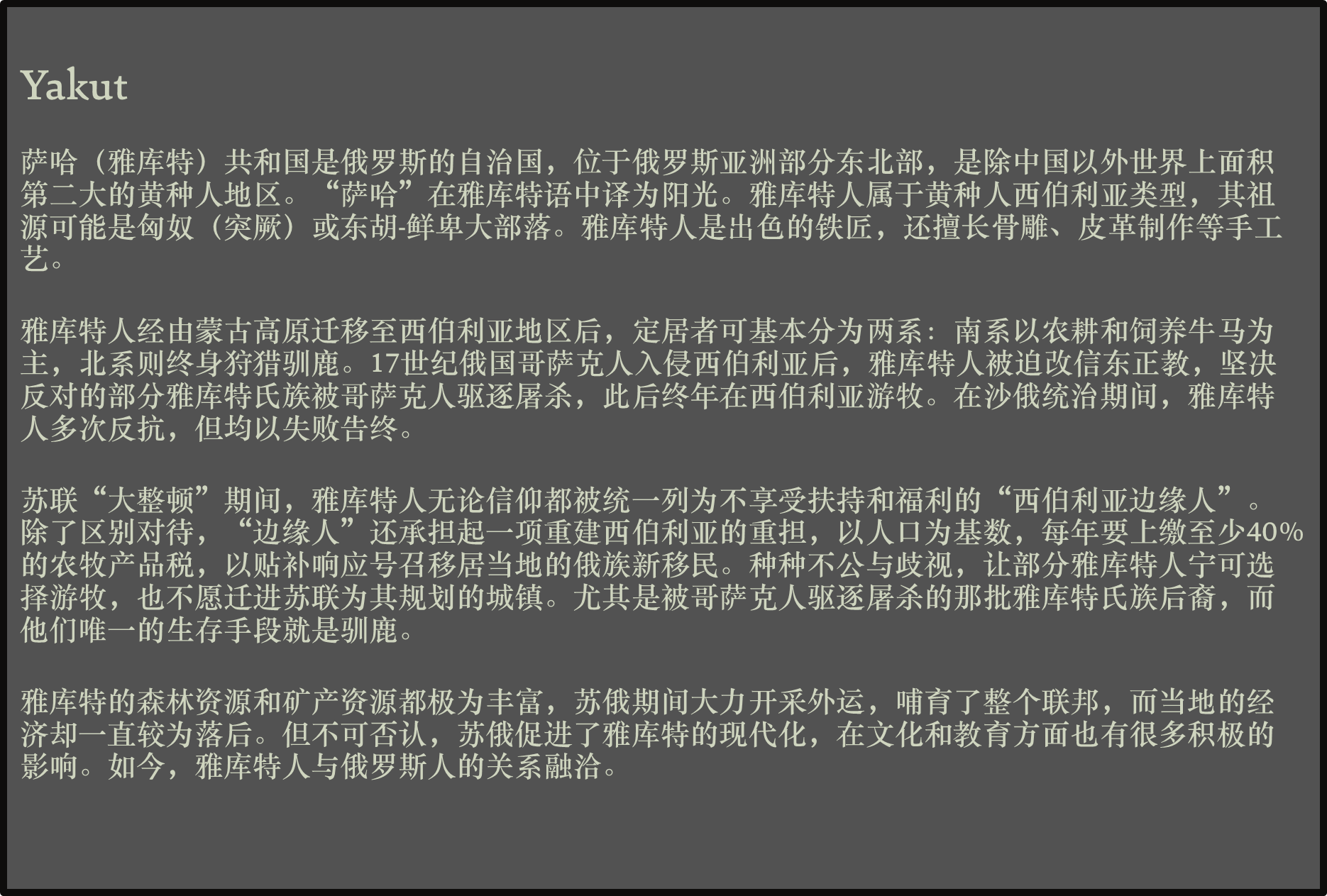六年前,某個遙遠的地方,另一片大陸的邊緣,一個男人甦醒了。現在是72年,他孤身一人。油布帳篷[173]裡寒冷,早晨黑暗。男人蜷縮在他的睡袋裡,揉搓身體兩側取暖,格子毛衣擦著他的皮膚。這使血液開始脈動,於是男人終於冒險把手從睡袋的溫暖中伸出。他睡覺時戴著羊毛無指手套。這在他的工作流水線上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他在地板上四處摸索,在黑暗中找到一個手電筒,花了半分鐘擺弄凍結的開關。終於,燈泡亮起,電能光源非常黯淡,只能勉強照亮一個人。男人盤腿坐在他的睡袋裡暖手。他在手指旁呼吸,張大沒有牙齒的嘴。在帳篷的內部,手電筒的光束裡,印出一個帶有製造商名稱的章,“‘微觀世界’合作社”。
男人把手貼在油布上,寒意刺骨。在雪的重量下,絕緣的帳篷在下沉。外面沒有一絲光亮,甚至也聽不見風聲。風暴已經在夜間平息了。電子手錶顯示今天是他的生日,他三十九歲了。現在是早上7:15。他蹲守在他的微觀世界帳篷中,從睡袋裡爬了出來,穿上他的阿諾拉克夾克,把腳塞進束帶靴裡。咔噠一聲,鎖打開了,就這樣,他光著腿離開帳篷,徑直走進灰域中。
距世界邊緣二十公里的地方,雪花輕柔地落下。現在是昏暗的清晨,一棵光禿禿的樹下,一個男人的影子從積雪覆蓋的帳篷處向前跋涉了幾步。在他周圍,針葉林景觀的黑白夢境從岩石牙齒和冷杉樹的幽靈長袍中浮現。在視線無法抵達的地方,幾乎察覺不到的藍色穿越雪和迷霧,滲進了無色的世界。現在是早晨,這裡也不會變得更亮了。身處其中,站在光禿禿的樹前的,是一個完全被摧毀的人類。他是一位灰域行者。他是年邁的搖滾音樂家。他的名字是齊吉斯蒙特·貝爾格,他穿著深藍色的白色條紋內褲。他在尿尿。
營地位於一座山坡上被冷杉樹環繞的臺地裡。即使在遠處,煙霧迷濛的山谷裡,也能聽見灰域行者的雪鏟挖開帳篷入口的響聲。然後,是斧頭的聲音。齊吉斯蒙特·貝爾格捧著一把光禿禿的樹枝,穿過平地回到了帳篷裡。厚厚的雪花飄在空氣中,男人已經穿上了牛仔褲。他站在那裡,阿諾拉克夾克的前襟敞開,兜帽掛在肩上。在他正前方的灰域中,有什麼東西正在移動。
寂靜無聲。這是衍生出所有其他寂靜的寂靜。灰域行者猛地吸氣,他的呼吸聲足夠響,淹沒了耳中自己血液奔湧的聲音。柴火在他的大腿上裂開。他像往常一樣微微駝背,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雪停了,灰域仍然與他一同存在。幾分鐘過去了,他手腕上的電子手錶凍結在“07:48”。
花崗岩上傳來蹄聲。在他的正前方,一處岩石凸起,一隻野山羊走出灰域。齊吉斯蒙特用銳利的眼神看著他,野山羊也看著齊吉蒙斯特。他們都有一雙深色的眼睛,因為寒冷而溼潤。齊吉斯蒙特·貝爾格扎著老年搖滾樂手的馬尾辮,髮際線後移,而阿爾法雄性有一頂巨大的角冠。在野獸背後,灰域裡,他的羊群滑過,畫出剪影,蹄子往上的直腿摺疊著;它們踏著步上坡。kozorogs[174]的角被灰 域包裹,就像舊日軍隊的長矛。一團團蒸汽從羔羊的鼻孔中升起。它們走在雌性身旁,而走在最後的是國王本人。野山羊移動著他戴著冠冕的頭,退回到灰域中。他把灰域行者一個人留在那裡。
“別走。”傳來齊吉蒙斯特沙啞的醉漢嗓音。“請不要走!”他扔下柴火,爬上積雪覆蓋的石牆。他的無指手套在花崗岩上打滑,他的腳找不到踩踏點。他呻吟著,拼命從低矮的灰色杉樹間穿過。一隻都沒留下,全都走了,你在找什麼,你這個傻瓜?
“*不要走,請不要走…*你就像那個老頭!你知道的,去公園的松樹林裡尋求陪伴的那個:‘小米奇,過來小米奇!’對親近的需求簡直如飢似渴。他控制不了。”
“但是我太孤單了。”
“你從未孤單過,齊吉。你還有你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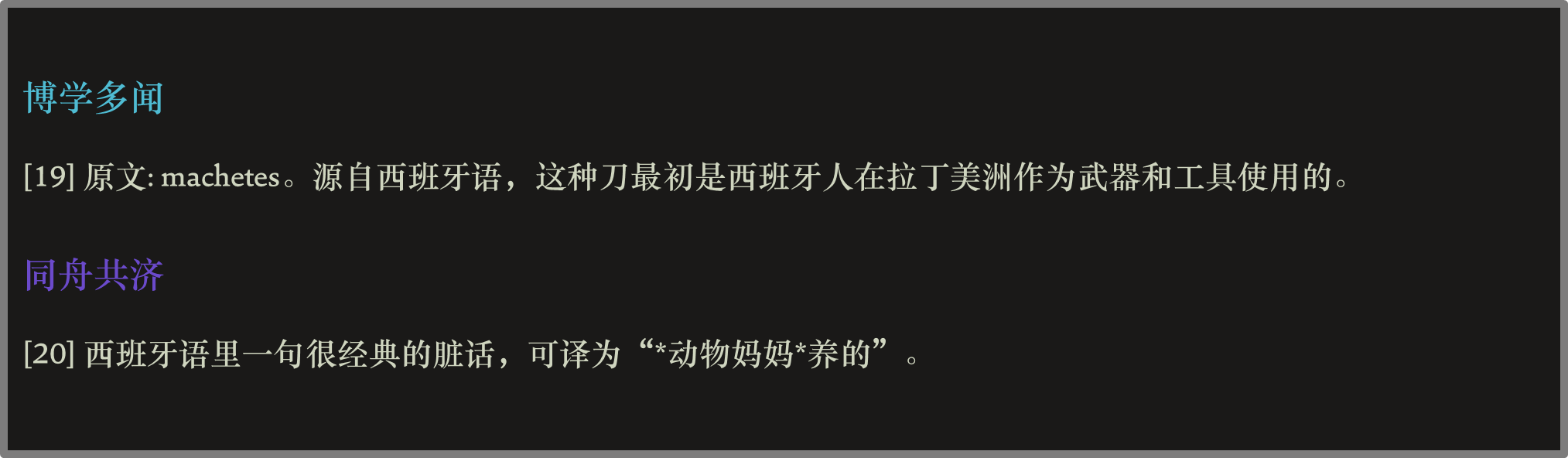
--------------------------------------------
二十一年前,寒假的一個晚上,齊吉站在有軌馬車站。兩天後,年號就要從51年變為52年。瓦薩的郊區在他周圍沉睡,已經很晚了,外面很黑,但他並不急著去任何地方。家中的母親沒在等他。男孩躺在車站的木凳上來回穿梭,皮夾克上的拉鍊叮叮作響。背景裡,高高的柵欄圍出的一塊地,是對私有財產的持續提醒。這讓他煩躁。
他剛給富孩子們賣了東西。再往前一小段時間,他在冬至派對上表演了他著名的*誦唱*。不論如何,小學男孩們開懷大笑,他們喜歡它。一些高中男生心想:“看看那個蠢貨,他活不到二十歲。”不過齊吉也不在乎那些高中男生。他們已經定型了。“小朋克。”同時齊吉親切地以此稱呼他們——只有他們還有希望。
同時齊吉也喝醉了,且絕對正處於找麻煩的狀態。但一天中這個時段的法魯車站,沒有其他人,所以他只得勉強接受一個無生命物體。看看他是如何挑戰時刻表的,但時刻表太容易屈服了。男孩對時刻表的缺乏攻擊性感到失望,試圖把它從柱子上弄下來,但金屬只是向他彎折。因為齊吉是全極樂世界最可惡的混蛋——那個偷走時刻表以使其他人無從知曉末班列車是否已離開的人——他把必要的信息壓成一個球扔了出去。車站依然空無一人,齊吉還處於惡作劇的狀態,他已經無法接受垃圾桶的* weltanschauung [175] *了。
“你說什麼?!”齊吉用兩隻手推了一把骯髒的垃圾桶,但它太滿了,併為捍衛自己的榮譽感到滿意。“我聽到你在那說的話了。‘*暴動的暴徒*’,你太過自滿了,‘*他膽敢舉手反對私有財產*。’你以為自己很酷,哈?‘*暴徒*’,‘*膽敢舉手*’。爭論有什麼問題,我們都是受過教育的人…但你猜怎麼著?”
垃圾桶並不知道齊吉在說什麼。它的頭上有一頂雪蓋,內部是熄滅的菸頭——這就是全部。難道還有不達成和平協議的可能性嗎?
“你想要那樣,對嗎?啊?你想要,不是嗎?吃蛋去吧,布爾喬亞!”齊吉一腳踏進垃圾桶裡,差點失去平衡。垃圾桶終於被制服了,而大自然無聲的暴力將他的注意力轉移到停車標誌上。它在風中啪啪作響,上面寫著“法魯”。在齊吉踢它的時,它像水車一樣轉了起來。但當他腳落地時,他滑了一下向後倒去。一團雪雲升到空中,一段時間裡,齊吉就躺在那裡,雪花落在他的臉上,他哈哈大笑。他的上方,燈籠在冬夜深藍色的天空中閃耀,雪花飄落。在上方某處,視線不可及的黑暗中,環繞運行著一顆被遺忘的舊日通信衛星。周圍的一切都那麼甜蜜,一個美麗,黑暗的世界,在鞦韆下搖曳。
但齊吉認為狂歡還不夠。他掙扎地起身。因為他拆除了時刻表,他現在不知道末班列車是否已離開。幸運的是,年輕的男人還沉浸在改變世界的情緒中,於是我們看到他步行走來,牛仔褲膝蓋處覆蓋著白色的雪,他的皮夾克正面敞開,流行明星的髮型在風中飄蕩…他向下走到郊區的街道上,步行回家。而在路的兩旁,尖樁柵欄後,坐落著木製房屋。他投去輕蔑的一瞥,舒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他在尋找正確的那座,其中最親愛的那座。
他的手裡有一塊磚。
他的額頭上有一個疙瘩。
卡爾·倫德,一位年輕的造紙商,在樓下的客廳閱讀報紙。報紙頭版上一個戴著禮帽的半人馬剪影十分顯眼,端莊的襯線字體寫著《Kapitalist[176]》。這可不是某些自稱為投機者的雜誌,而是五百年前,在市場經濟的曙光中創立的報刊,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報紙之一。它不提供快速致富的小把戲;相反,《Kapitalist》通過經濟稜鏡審視整個政治現實。在世紀之交白日夢的另一邊,僅僅反映出它真實的樣子。卡爾·倫德關心世界,他通過閱讀去理解,通過理解去提供幫助。真心實意。你可以親自閱讀一下——也會因此變成一個更有影響力的人——但不幸的是,你無法理解《Kapitalist》。
齊吉也無法理解它。他嘗試過,但它不能。不過他也沒付出多少努力。伊蘇特的饑荒,薩拉米里扎的黴斑[177]流行病——這些東西不會困擾齊吉。他並不會被它們觸動。對他來說,那些只是批評,還有消極。齊吉不關心世界,他不想理解和提供幫助。他想要完全不同的東西,而現在他將向你展示那是什麼。男孩繫緊他的鞋帶,感謝酒精的振奮,他並不覺得冷。他站在白色的木製房屋前,手裡拿著磚頭,瞄準目標。
磚頭脫手而出,齊吉發出野生動物一樣的奸笑。磚塊飛入冬夜的黑暗中,盡頭是一幅等待被砸碎的諷刺畫——甚至對年輕的齊吉斯蒙特·貝爾格的生活來說都有些尋常的事物:皮革裝訂的書籍,桃花心木的香味。窗戶碎裂成上千片,造紙商從他的扶手椅上跳了起來。樓上,如同一個不祥之兆,深綠色的眼睛睜開了。
“我再也等不了了!”齊吉咆哮著,胳膊肘在身體兩側彎曲,背部拱起。“終結,世界,終-結!”唾液和蒸汽從他的嘴裡噴出。他的吐息是帶著酒氣的火焰,他是一條惡龍。在51年,卡爾·倫德正處不惑之年的中期,還是個年輕人。他像步槍裡的子彈一樣飛到前門,穿上訓練鞋。一個月以來,他總能在花園裡發 現貼著“資產階級”標籤的垃圾袋。早上,到處都滿是垃圾,令人作嘔的罐頭食品盒掛在榲桲灌木叢中。他衝了出去,撞開花園的大門停頓了一下。大約五十米開外,街道的中央,一個穿著黑色皮夾克的人影在全力衝刺。造紙工業家從他的位置爆發啟動,在男孩身後衝出。
齊吉一頭流行明星略帶油膩的黑髮呈波浪形,在風中飄蕩。在齊吉經過時,他身後燈籠的冰冷光暈收縮又展開,形成光環。雪花從他的運動鞋下飛出,後襟翼在風中飄動。此刻,加滿了酒精的齊吉,正跑過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但是他的運動鞋在雪上打滑,而且他從九歲起就開始抽菸了。另外,體育課也不是他在學校裡最喜歡的課程。
卡爾·倫德經常與同事一起跑步。而且當然了,他不抽菸。不,連香菸也不抽。儘管齊吉——拿著一側寫有“資產階級”的垃圾袋——認為就在前幾天,他看到他在抽一個巨大的陰莖形狀的雪茄。那裡的某處,就在高雅木屋的玻璃之後。順便說一句,他也不喝卡拉夫瓶[178]外的白蘭地,也不是Les Morts[179]的一員。他也不在發展中國家參與性旅遊業。
一個男人飛馳而過,他穿著黑色高領運動衫,訓練鞋的白色皮革在雪地上閃閃發光。距離在縮短,齊吉在轉角滑倒,手腳並用再次啟動。在身後三十米處,他聽見卡爾·倫德大喊:“站住,你這個混蛋!”他的掌心刺痛,肺在流血,但是在酒精作用下,齊吉的超級人類疼痛忍耐力回來了。事實上,他已經把自己腿部的肌肉撕成了碎片,與多年無所事事的閒逛相比,計劃之外的衝刺就像一場突然襲擊。但齊吉什麼也感受不到。他能永遠跑下去。
當然了,這是幻覺。現實中他的身體存在上限,而在八分鐘追逐後,它自己也感受到了這一點。在一輛火車經過時,兩個人相隔不到十米奔跑著。齊吉急轉彎,沿著樓梯跑上一座平臺。在市郊的寂靜裡,腳踏在混凝土上的敲擊聲,以及兩人越來越拼命的喘息聲可以傳到很遠的地方。兩個模糊的黑影,在燈籠的光束下沿著平臺奔跑,距離持續縮短。齊吉向後一瞥,看到那個資產階級紳士在以迅捷的受控運動逼近,就像是從未來送來的*機器人*。在平臺的盡頭,男孩跳了下去,奔向市郊的鐵路工業圍場——他四處遊蕩的地方。他落地時保持著平衡,在雪地上繼續進行比賽。在鐵路路堤的黑暗中,他認為,他終於能甩掉那個機器人了。他怎麼還不放棄?!通常,像他這樣的人不敢走出住宅。他們會召喚心愛的警察,然後聚集在屋裡。
齊吉沿著尖樁柵欄和牆壁之間的雪帶,以及鐵路的路堤,率先抵達。伏特加的魔力正在褪去,他像一隻受傷的動物,帶著渺茫的希望奔跑著。他感覺他的右腿在抽筋。繼續!但在那之前,他需要最後再努力一下。現在別放棄,你這個濫用腿部者!我現在真的很想要一支菸。
在他的身後,卡爾·倫德的鼻腔中感受到男孩的汗液。他來自世界沒有終結的那個未來。那裡所有人都是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幾乎被完全摧毀了。卡爾·倫德瘋狂地掃了一眼四周,他看到在前方等待著的是車庫堵住的死路。為了將齊吉釘在牆上,他擠出最後的力氣,做好衝擊的準備。用盡全力。只瞟了一眼那隻細長的蜘蛛,他就知道他能抓住他。男人伸出手摸到了男孩的外套。此刻,離車庫牆壁僅有一米左右。齊吉將自己從右腿上推離,直接貼在磚牆上,但他抽筋的另一條腿並沒有像他腦海裡設想的那樣正確地鉤住牆上的裂縫。計劃執行了一半,他並沒有以塞拉斯的ensiferant [180]那樣的姿態跑上牆。他滑落了,但試圖用雙手抓住屋頂的邊緣。齊吉掛在了牆上,但卡爾·倫德抓住了他的腿。
“靠,男孩,放棄吧!”
但是在他的上方,車庫頂,齊吉的朋友矗立在他面前,在身後鼓勵他。儘管飽受時間的摧殘,但齊吉的朋友依然自信且強大。他像一面灰色的旗幟在黑暗裡飄蕩,並招手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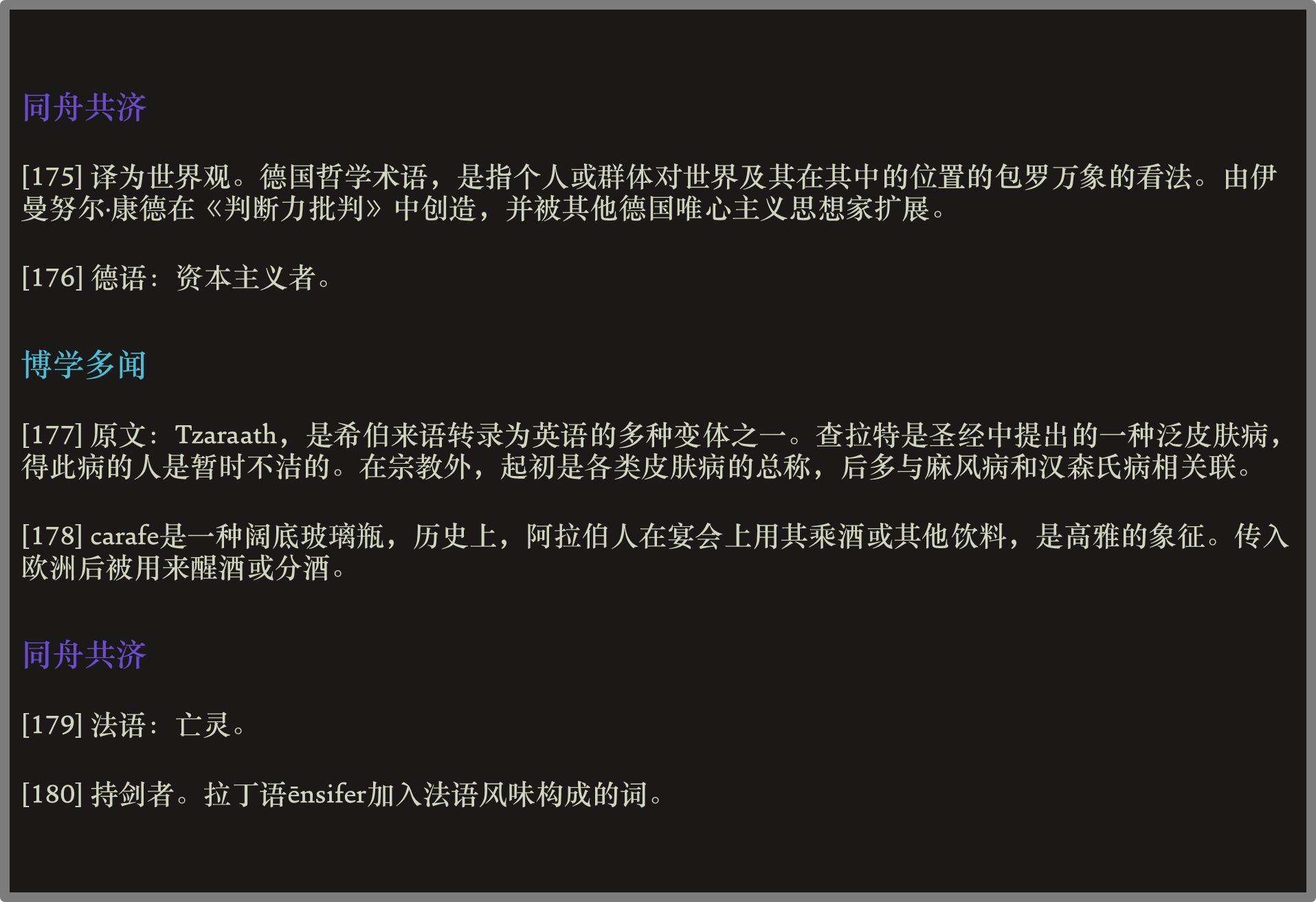
--------------------------------------------
在薩馬拉東北方,剛剛陷落的奈德-烏麥生態區的針葉林裡,一個被徹底摧毀的人類在抽菸。向南二十公里,世界從薩馬拉人民共和國開始。四千公里外的更遠處,東北方,是卡特拉洲,而兩者之間坐落的是什麼,沒有人知道。
“別幼稚了,這當然不是某種來生。”齊吉斯蒙特結束了無意義的爭論。他從鋁製黃瓜罐中取出菸草卷,把它們放在捲菸紙上。在離開薩帕爾穆拉特·烏蘭前,他囤積了夠用兩個月吸菸材料。糧食配給應該足夠了。在中央商場,只能用罐裝的乾燥剩菜兌換蕎麥券,紙沒用,膠帶也粘不牢固。紙貼在嘴唇上,發光的菸草從菸捲裡落到胸前。灰域行者用手撫摸著他的外套,灰域裡,發光的火星是他周圍唯一的色彩。他坐在帳篷的三角形入口處,兩條腿伸在外面,在他面前雪地中挖出的一個洞裡,火焰冒著煙。在火光的另一邊,伊格努斯·尼爾森,卡拉·馬佐夫學生時期的朋友,一個末日嗜血的幽靈細胞質,蜷縮著。膠片上的詭異缺陷被背景迷霧中的冷杉樹框住,它是黑白的,且極度反常。
“生日快樂。”灰色幽靈細胞質說。
“三十九歲,”齊吉斯蒙特回答。“呃,怎麼會這樣?”
“你現在可以簡單地把它四捨五入成四十歲。再也沒區別了。準備好,告訴你自己你現在四十了。”
“我四十了。”
“四十歲!怎麼回事?不是說你活不過二十歲嗎?到現在為止你都沒有計劃。你在這裡幹什麼?”
“你知道的,伊格努斯,我想要消失…”男人打著瞌睡,用一根木頭整理火堆。火焰中心的深橘色火焰恢復了生命。
“*又一次*?我們消逝得還不夠嗎?”
“你永遠可以更加消逝,伊格努斯。你可以在身後留下更少:紙屑,牙醫…”齊吉把水壺放在火焰上,裡面新鮮的雪開始融化。
“他們會用牙醫的事抓住你!你應該自己做的。當年在格拉德,你應該自己用ruuvimeisseli [181]把壞牙拔出來!”
“我嘗試過,但那太痛苦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兄弟,別亂說!另外,如果不是醫生,那你就是在高估資產階級司法系統。自由裁量權[182]協議,就像榮譽,他們只會*pakazuuha[183]*。還記得馬佐夫嗎?”
齊吉從阿諾拉克夾克的口袋裡拿出假牙放進嘴裡。“你才是胡言亂語的那個。跟馬佐夫有什麼關係?另外——看看我在哪裡!誰還能發現我在這兒?連灰域理論研究所都不會發現我在這裡。”
“你這樣認為?”
齊吉把手伸進隔熱手套裡,等待水燒開。“我這樣認為。而且還有!這次,我不只是想逃離那個國家。”
“那好,你是想逃離哪裡呢,齊吉?國家是很大的。”
“逃離世界。”
灰域變暗了,其下是雪原。水壺裡的水顫抖著。“我的天…”已經被時間審查員裁切成殘破碎片的伊格努斯·尼爾森,嘆了口氣。黑色的山脊留下他空洞的聲音,沒有回聲。“上帝,我真的受夠這些關於消失的胡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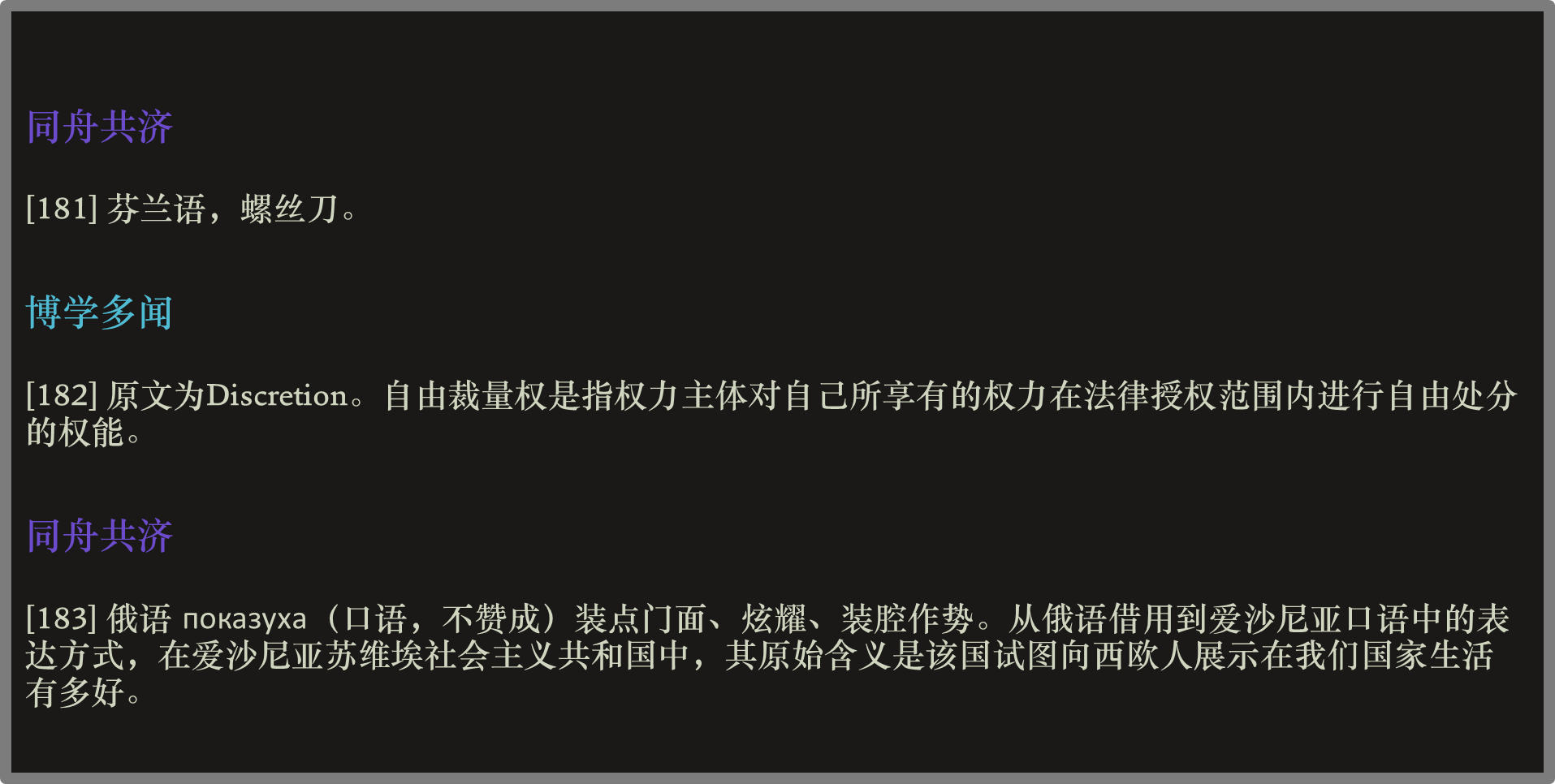
--------------------------------------------
一陣掙扎後,齊吉的腿從卡爾·倫德的控制中掙脫。他踩在擁有家室的男人的肩膀上,一腳蹬上了車庫頂。他站在那裡,在冬季天空下高奏凱歌,年輕氣盛,自由自在。資產階級蹲在他面前,一敗塗地。
“哈?你現在要怎麼辦?”齊吉大喊,瘋狂地比著手勢,彷彿要“鎮壓”這位工業家。“你會怎麼做,哈?試著爬上來?我會把你的手指踩成碎片!”他在車庫屋頂的邊緣跺腳,演示當你在他之後爬上來會發生什麼。“你-輸-了!我贏了!你剛剛*他媽的*輸了!”
“幹得好。”陰影中的伊格努斯·尼爾森低語道。“我也對中產階級做過那樣的事。和馬佐夫一起,我們殺了他們,你明白的,成百上千的他們。我們殺了幾乎一百萬個資產階級,我們本來能殺死更多,但是沒有時間了。”
“我要殺了你!”齊吉咆哮道。在車庫屋頂上,天啟鐵匠的* fiilis[184]*重新迴歸,萬事皆允。“你把世界聚集在一起,我要殺了你。我要殺了你的家人。”
“孩子,去看看醫生。”卡爾·倫德放棄了,轉頭離開,但齊吉的手中捏了一個雪球。當它擊中卡爾·倫德的後腦時,他在怒火中轉身三兩步走回來:“你這個小混蛋,我記住你的臉了!”
“*我記住你的臉了*!”齊吉嘲弄地說。“我也記住你的臉了,我知道你住在哪!”齊吉的周圍飄著雪,雪花在他的黑髮上融化。
“下來,你這個下流種,如果你是個有種的男人就下來!”
“噢,我來了!”齊吉扔下一個雪球,但男人躲開了。“我會和殺戮天使一起下來,她們穿著皮大衣,你的家人死定了!男同!”
“非常經典。”他身後陰影中的伊格努斯·尼爾森稱讚道,“引用特別委員會成員的話很天才。你是個詩人。但你是行為上的詩人,不是詞語上的!”
“我會強姦你的老婆!”
“你被怒火衝昏了頭腦,孩子,你在生氣!繼續!”
“你會被帶去葉科卡塔,我要把你的公司國有化!”
“現在有點太學術了,別向那個方向繼續,它是滑溜溜的冰塊。你知道你其實並不真的瞭解這些事。告訴他他是個基佬!”
“基佬!”
怒不可遏的卡爾·倫德試圖爬上去,但是齊吉用更多的雪攻擊他的面部,並跳到他的手指上,男人落回到下方。
“好的,現在是閃人的好時機了。但在那之前,說些能激怒他的話!”
“基佬!”
“那起作用了。”伊格努斯·尼爾森說,齊吉被皮衣包裹的身影消失在車庫的黑暗中。

--------------------------------------------
白雪覆蓋的藍灰色山坡上,一個剪影浮現在一輛翻斗車的巨大車輪旁。奈德-烏麥依然是半明半暗的灰色。齊吉斯蒙特·貝爾格沿著山路獨自走來,他揹著一個巨大的揹包,一條老搖滾樂手的馬尾辮深藏在兜帽下。他的阿諾拉克夾克的茸邊兜帽像煙囪一樣冒著煙。男人手拿兩根滑雪杖,嘴裡叼著一根菸,跋涉穿越灰域理論災難區。
“當馬佐夫不能再等待世界革命的時候…”
“你是說在他朝自己的頭開槍,因為他已經變成了一頭怪獸的時候?還是因為他正在失勢?”
“完全不是那回事。”伊格努斯·尼爾森像一面灰色旗幟,在他的左側飄蕩,“馬佐夫有一個溫柔的靈魂,各地的反應如燎原烈火,不論我們殺了多少人,總是有更
多。之後就是那些挫折,一切都塌縮進瑞瓦肖。那時他只是感到悲傷,他不認為自己是怪獸。”
齊吉斯蒙特·貝爾格的足跡在杉樹間的道路上劃過,兩側是滑雪杖扎出的痕跡。“告訴我——你為了獲得權力付出了多少?犧牲了多少位同志?告訴我,這次它到底是什麼。‘當其他康米主義者來殺我的時候,我就知道馬佐夫的思想再次發揮作用了!’是這樣嗎?還是相反呢?”
“當然不是,你想以最壞的惡意揣測我們,齊吉斯蒙特。這樣你就不用再相信任何事情。你就可以完成來這裡要做的事。告訴我,什麼時候我們能期待一場幹部的清洗?我們兩個都是。你什麼時候獨自上路?”
“說實話,我考慮過,伊格努斯。”
“那就好好想想吧,但要知道那不全是謀殺和迫害。當我接手時,當一切終於掌控在我手裡時,這是種令人陶醉的感覺。你能想象,整個國家都是你的嗎?除了美好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那種感覺。我輕輕握住格拉德,就像建築師握住一條鑲嵌線…”一個灰色的盒子在伊格努斯的胸前閃爍,一扇歷史之窗,“像手裡的一根火柴。而且我現在保證,提供一個機會——我就會為人類做任何事。而且你知道,我沒有讓自己失望。”
“一切都消失的無影無蹤。只留下一個大陸外殖民地,雪羊屎一樣的東西!”
“不要那麼狹隘。可以持懷疑態度,但不要低估薩馬拉。我的心埋葬在薩馬拉。當我們撤退到這裡後…”
“沒錯,你*撤退*了!你為什麼要再次撤退?為什麼我的人們一直在撤退?”
“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也不會聽天由命,成為一個宿命論者。我為這個殖民地鞠躬盡瘁。我的薩馬拉革命共和國!”
“是的,沒錯,‘人民共和國’腐朽了。”
“因為他們做的事,我永遠不會原諒他們。在他們給我全搞砸之後。多麼腐朽!我永遠不會原諒!”灰色的幽靈細胞質怒火中燒。
灰域行者走過暢通關卡間的山橋。路的兩側,空蕩的警衛棚屋在雪中打著瞌睡。在橋的盡頭,一個標誌上寫著“內門吉·烏爾——36公里。”而在更遠處,穿過下著雪的灰域,是烏麥山脈的針葉林。就在兩週前,世界最大儲量的螢石、鎢、鋅和稀有鈮釔礦[185]的一部分,從這裡的土地中提取...冶煉廠在燻燒,工業廢料將生態區剔透的銀色溪流變成鏽色的泡沫。但再也不會那樣了,現在這裡安靜而祥和。灰域行者沿著傾斜的貨車道,向下走進山谷的黑暗裂縫中,周圍的杉樹變得更加昏暗。而在他前方,雪路上,一串蹄印狂暴地劃過。
“太棒了!這是自我犧牲,完全獻身於人民。我是安非他命上的統治機器,我從不睡覺。我們全都不睡覺。我們從頭構建一切。憑藉葉庫坦[186]人的幫助,那是國家間的兄弟情誼。他們尊重我們的武器,我們尊重他們的快樂靈魂和舞蹈。六年間,一個國家從無到有,平地而起。工人們自願工作到死,連續辛勞工作到第五天,真的死在施工現場;心臟病,衰竭….”
“用槍指著他們的頭?”
“你以為是這樣,但你錯了。那是現在的情況,當然了,但那時可不是。你無法想象這裡發生了什麼,如何發生的。就像欣快症[187]一樣席捲世界!”
“欣快症?那時安非他命還沒經過醫學測試,到處都是。”
但是伊格努斯沒有在聽。“我說了恐怖的事情,是的!在暴風雪中,我站在一匹白馬上發表演講。在山區裡,在施工現場…我揮舞著我的劍,劍柄上反射著銀色的陽光。周圍的所有人都在揮舞白色旗幟,上面有銀線繪製的角冠,五角星在鹿角臂間,枝幹指向天空。和我一起來的人們都很開心,齊吉!康米主義很強大!信仰康米主義,它是一場爆炸!我保證!如果你相信人民的話那很美妙,但如果沒有了它…!”
“沒有了它,這裡就什麼也沒有。”
“什麼也沒有。這裡曾有一場雪暴。不過很亮,在早晨。康米主義是白色的,它在閃閃發光!康米主義是清晨,是歡騰!”
灰域行者周圍的灰域開始危險地衰退了。世界在變白,射線光束從伊格努斯的胸部滲入冷杉樹的暮色中。落下的雪在光束中像銀色紙屑一樣閃閃發光,色彩像威脅一樣滲入世界。齊吉蒙斯特用腳跺著地面。他用手捂住雙耳尖叫:“夠了!停下來!”
“夠了,停下來…”迴響在森林中,像一把利劍切開空氣。
“我真的非常抱歉,齊吉斯蒙特,我的朋友。”失真的聲音響起。男人在森林小路的中間喘著氣,半明半暗的薄暮恢復了。灰域回來了,男人解脫地長舒一口氣。“你想讓我…發瘋?”
“不,我只是想讓你理解那時的生活是多麼美妙。那時的時光啊,多麼美好的時代!我很抱歉…”
“那個時代結束了。它埋葬在你的穿孔卡和你的狗屎下。再也沒人能說出那時有什麼。沒有人知道那時究竟是什麼樣。它移位了。那裡真正存在的,消失了,只剩下灰域。那是幻景罷了。你知道這一點。*我*知道這一點。”
“那是你的女孩們會說的話。”細胞質在齊吉蒙斯特的耳中輕輕低語。杉樹搖曳,灰域昏暗而又誘人的輕柔。“你的那些女孩,女孩們不相信任何事,所有女孩都是資產階級,齊吉。”
“她們不是資產階級。”
“她們是資產階級。每一個都是。她們閱讀女孩雜誌。瑞瓦肖的資產階級時尚和香水,失去童貞的故事。都是資產階級。事實上,每個女孩都是資產階級的一把武器。”
“你不認識她們,你不知道她們在想什麼。沒人知道她們在想什麼。我也不知道,但那不是資產階級,伊格努斯。那是別的東西。”
“如果那就是你的想法,請。但你最好相信男人,而不是她們。相信康米主義。”
“我試過,但我不能!它對我不起作用…我不是康米主義者那類人。”
“那你為什麼在跟我說話?我就是康米主義本身,行走在土地上的幽靈。如果你不相信康米主義的話,那這麼多年來為什麼要跟我呆在一起?”
“出於對那些生活更富裕的人的仇恨,伊格努斯。此外——你是個怪物,怪誕之物。誰會不喜歡怪物的陪伴?”
“我不是怪物。”
“你是怪物。他們叫你‘世界末日的伯勞[188]’,你知道誰還被這樣稱呼?沒人!格拉德所有的大屠殺都出自你手,到處都是你的簽名。還有在撤退期間,連馬佐夫都停止發號施令的時候,你把敵人的士兵穿刺在木杆上。一萬兩千人。你為了木杆砍倒杉樹,你建造了木杆森林,那令人作嘔,伊格努斯!”
“這樣他們才會讓我建立我的國家!我的未來之國。你明白的,他們永遠不會放過我們…他們會像遊戲一樣獵殺我們直到死亡!”
“或許他們是這樣,但仍然:有點過分。‘伯勞’——看看你變成了什麼!”
人類的演講在灰域的死寂中聽起來錯位了。齊吉蒙斯特穿過雪地時,它在黃昏的樹林間迴響。那是K·沃洛尼金的音軌,一位老灰域行者,在灰域裡你必須要製造響聲。否則,沉悶就會襲來,過去將會顯現。但齊吉蒙斯特無需懼怕它。在第一次來到灰域時,他甚至極為驚愕地發現他不會像其他所有人那樣倒退。或者說,他會,但不是去他真正想去的地方。這使他需要馬佐夫的思想。倫德家孩子們的消失,確實賦予了齊吉特殊的灰域理論能力。
早晨結束了,天色開始變暗。幾十公里外,是深層灰域開始的地方,在那裡,世界白天的時光完全不登記。屆時他必須存夠電池。他想了一會兒,還是打開了手電筒。雪在手電筒的光束中閃閃發光,齊吉蒙斯特將它指向他可憐的朋友。伊格努斯的缺陷閃耀著光芒。
“看看你自己!你真可悲。如果他們做得乾淨些,對大家都好。一群業餘愛好者!我本該燒掉你所有的膠捲。太殘忍了,你就掛在這裡…”
“但那你就不會認識我了,齊吉。想想我們一起度過的所有時光。並不全是糟糕的。”
“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在談論你。一個不存在你的歷史,難道不是更好嗎?沒有木杆森林和安非他命,也沒有殘喘的細胞質。誰需要那個?”
“那不重要了。”伊格努斯慢吞吞地說。“你清楚的。我們殺了多少人並不重要。世界在終結。很快沒有人會記得我。更不用說你了。甚至連這個世界的偉大都不會被記住。”
“那更好,那就對了。*這個世界的偉大*?你是個噁心的怪物,在這個世界橫衝直撞!”
“你也在橫衝直撞!看看你的手,齊吉!我們不要忘記…”
“再說一個詞!說出來你就會消失了!”灰域行者大喊。“與你相比,我什麼都沒做!而且別忘了!我們中誰是革命委員?是你嗎?”
“不!”伊格努斯顫抖著,他害怕了。“原諒我,朋友,一萬個對不起!只有你是革命委員——齊吉斯蒙特·貝爾格——你的理性黨的一把手。我沒有權力。我的一切就是我給自己寫的謙遜的批評。拿去。但不要殺我。我的另一面一文不值。為了留下來我會做任何事。任何事。我希望。”
“你知道我想要什麼。這就是最後一件事。開始講話!”
但是伊格努斯不能說話。他沒有嘴。膠捲上的缺陷在黑暗中咔咔作響,被手電筒的光束照亮。這是殘忍的極點,要求不可能的事情。森林空氣中令人不安的死寂包裹著他。所有人都很尷尬。“為什麼,伊格努斯?”灰域行者重複道,將手電筒靠得更近,以窺歷史的心臟。“你為什麼要做那件事,它沒有任何價值。我理解你掃空了銀行,那有必要。你甚至在撤退時帶上了交響樂團。通過武力。畢竟,人民喜歡音樂。但為什麼是*那個*?它會讓誰開心?為什麼是‘哈南庫爾’,那個模型一文不值!告訴我你就能留下來。”
“但我一點也不知道。”背景裡的聲音悲傷地回答。音軌減慢了。“我不知道任何你不知道的事。”沒有其他的話語。灰域行者搖晃著自己。雪從他的肩頭落下,從他的阿諾拉克夾克上落下。他繼續獨自一人。在手電筒的光束中,凍結機器的軌跡經過這裡,羊蹄刻印在雪中。隨後,當路中間的雪羊群終於從黑暗中顯現時,它們被凍結在了原地。如同一場自然博物館展覽。通常,有些雌羊會原地移動和打噴嚏;這是一種神經衝動,一種肌肉痙攣。它們的背部已經被雪覆蓋,但鼻孔還在冒著蒸汽。它們還在呼吸——有的持續幾天,有的持續幾周。穿著阿諾拉克夾克的身影帶著專業的冷漠在羊群中移動,直到手電筒的光束將阿爾法雄性的角的影子投射在杉樹牆上。齊吉斯蒙特看向那隻動物晶瑩剔透的眼睛裡。那裡的時間感知已經瓦解了。自動機的原始腦段[189]比人類更先在灰域中陷落。這就是內陸獵人在*灰域卡塔[190]*中狩獵的方式。當然了,他們最後自己也發了瘋,某一天後再也沒有回來。但齊吉不是這樣,他有特殊能力。他從腰帶上取下彈簧刀,割開了蛋白質的喉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