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鷹之巢》原作者:(斯洛文尼亞)弗拉基米爾·巴托爾
譯者:湯姍華
面世83年來,首次中文版

封底

出版信息

腰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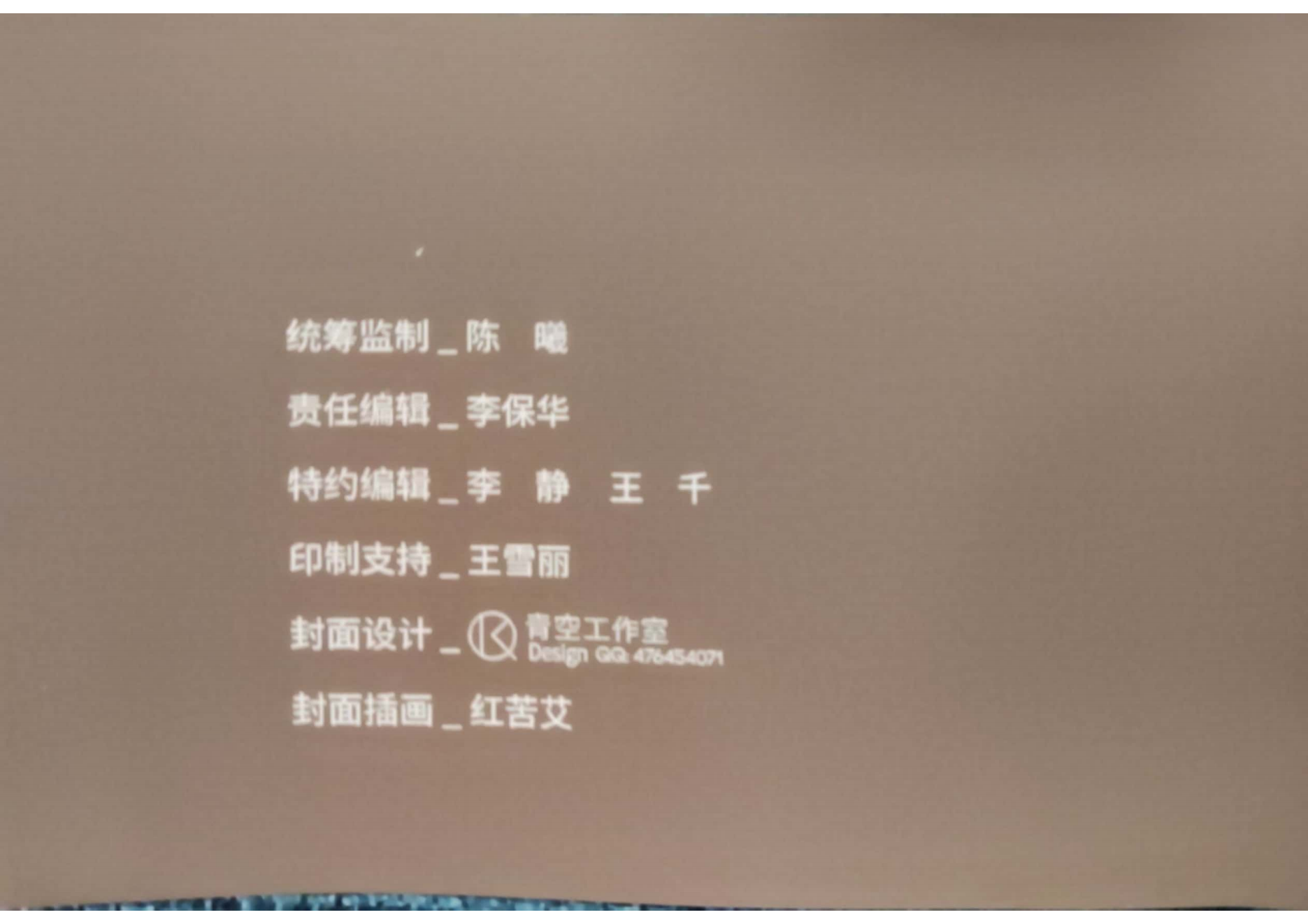
職員說明

封皮

封底

出版信息

腰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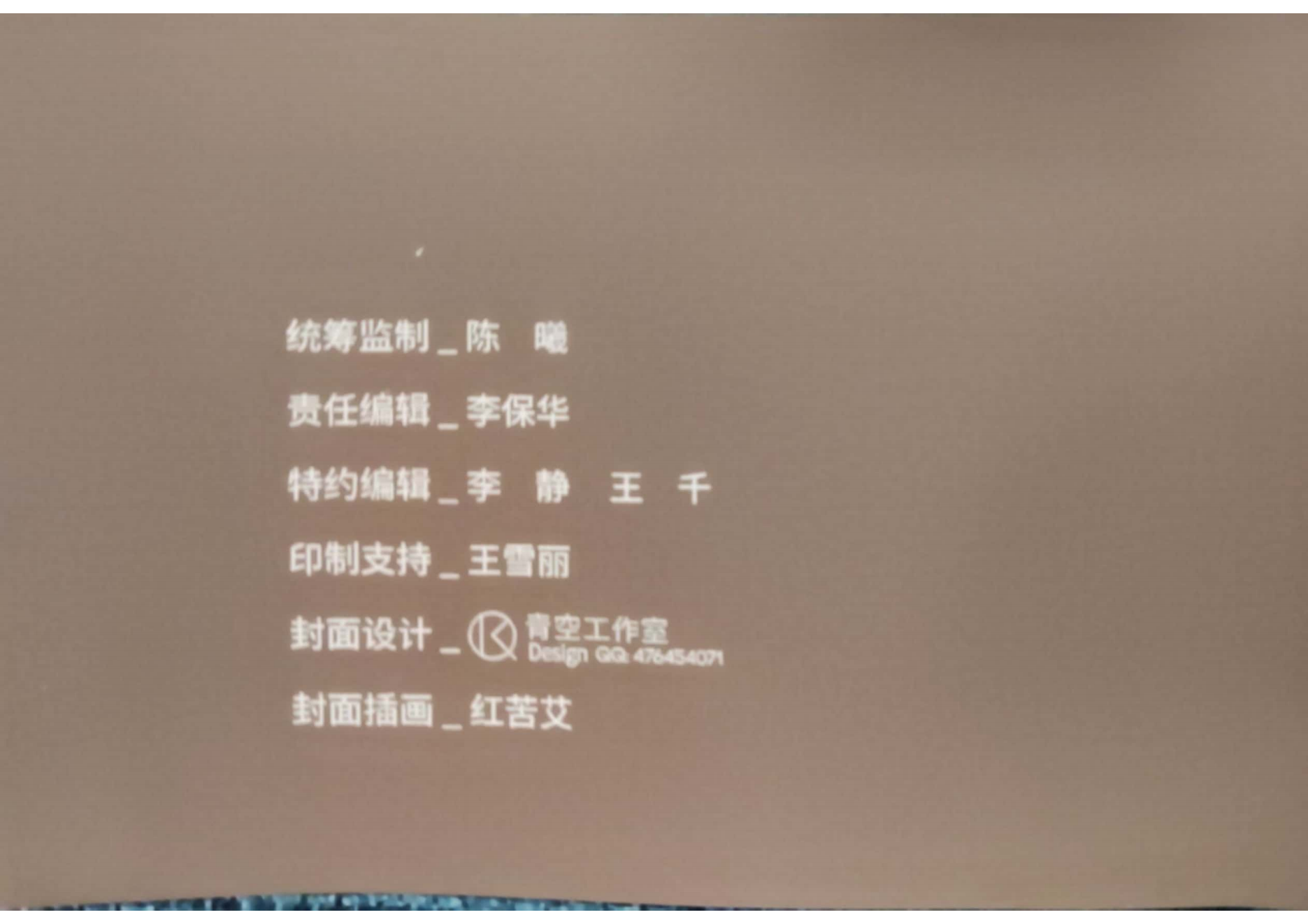
職員說明

封皮

封底
1 / 5
《鷹之巢》中文版實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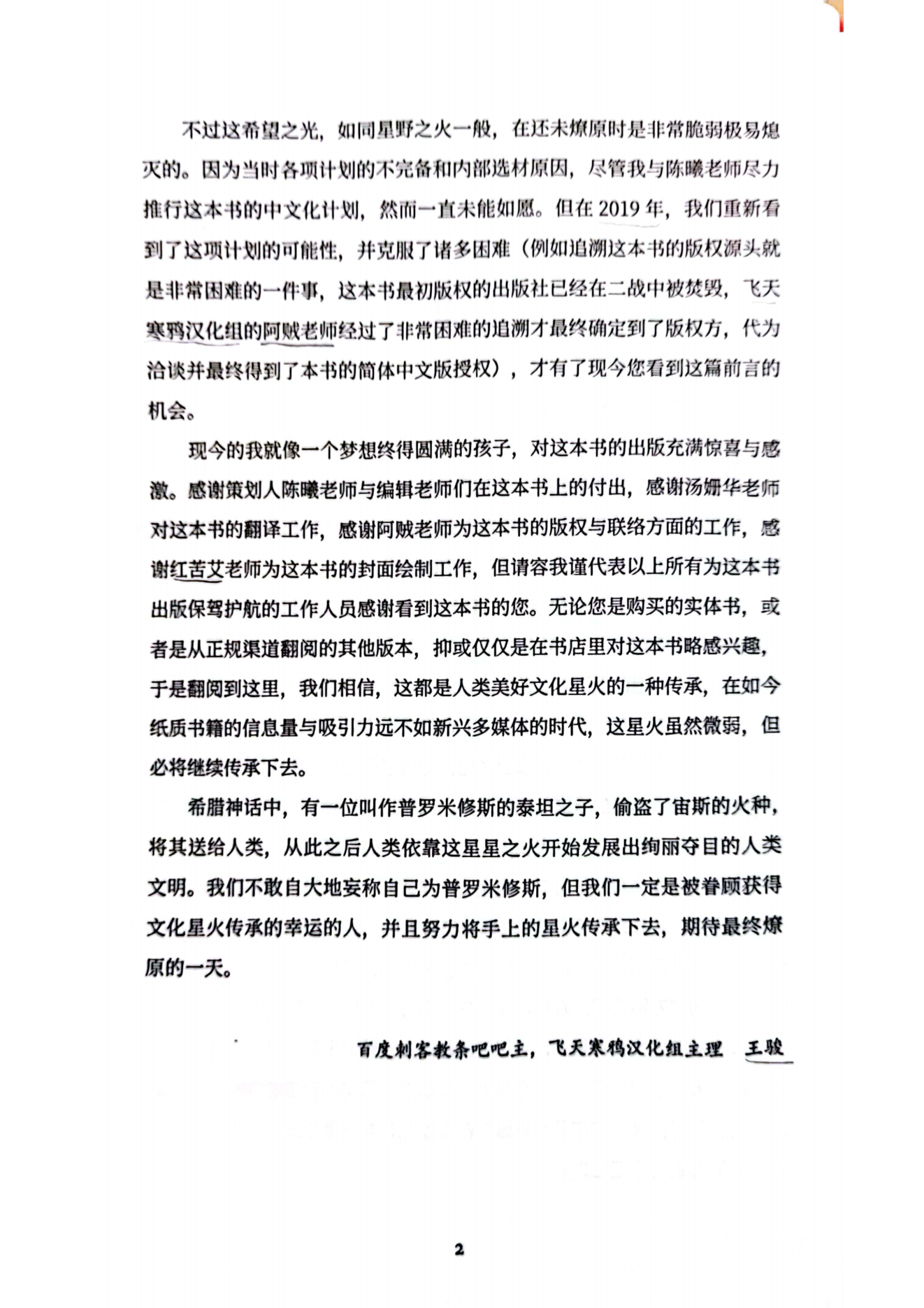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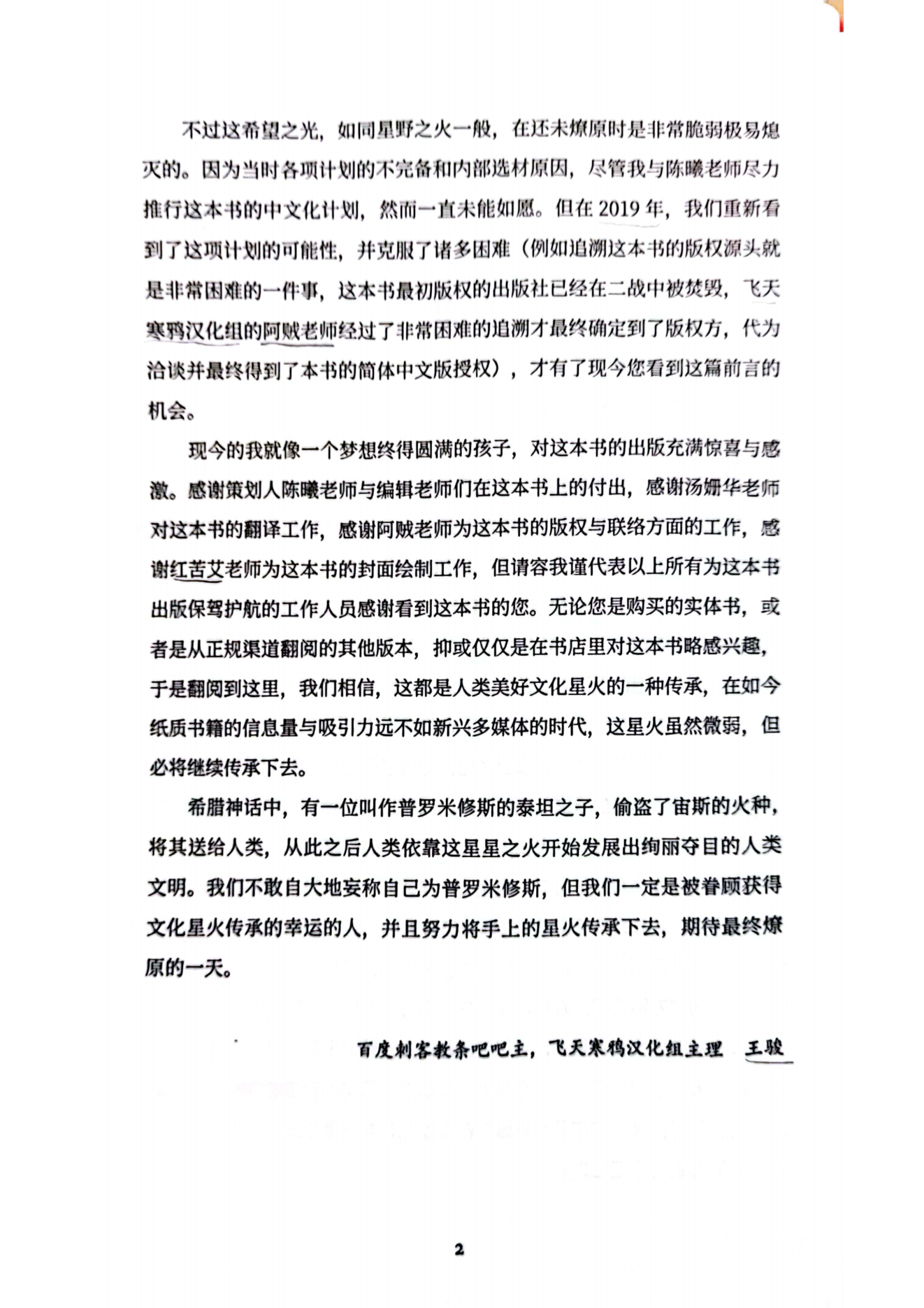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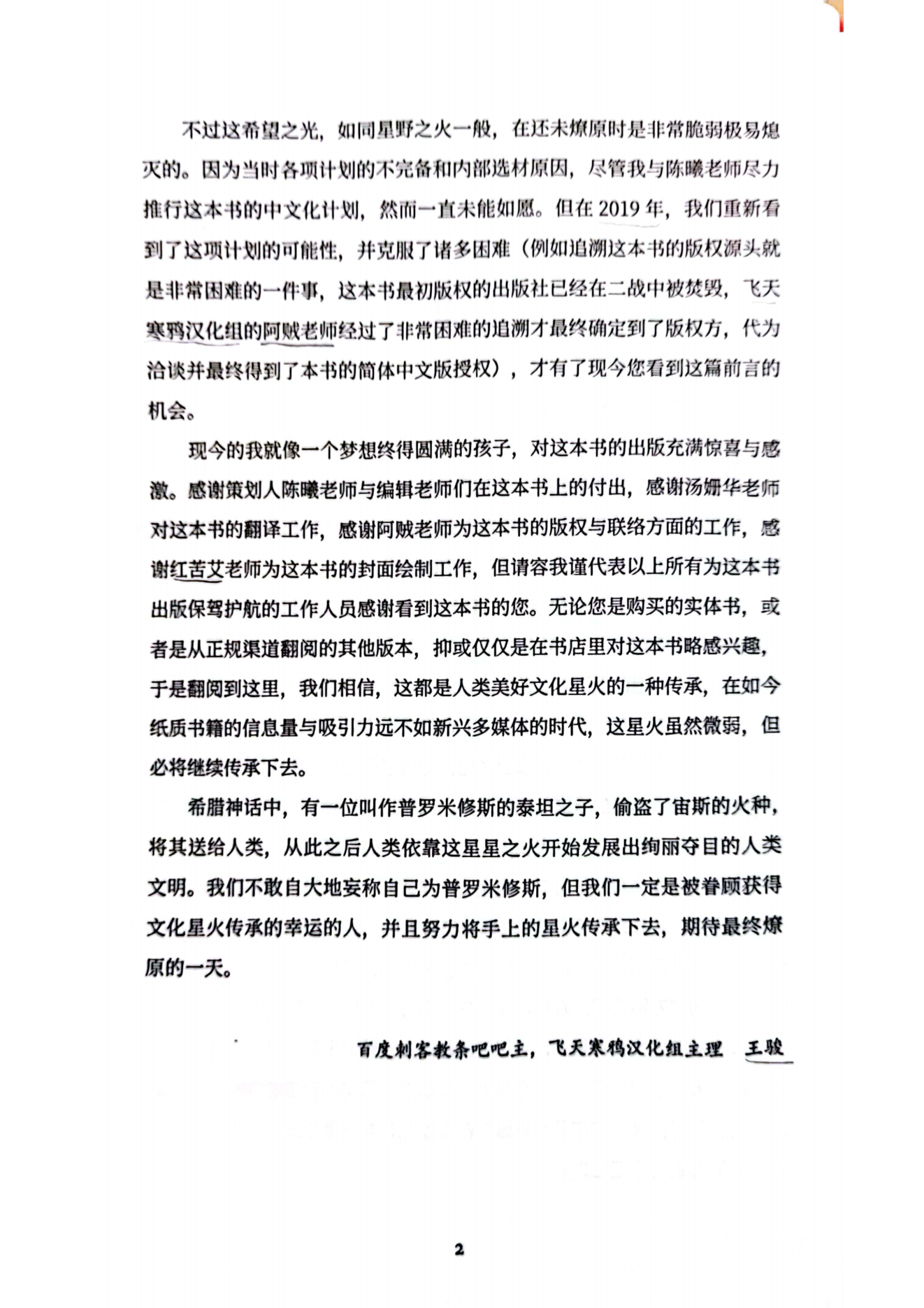
1 / 2
《鷹之巢》中文版代序
本文僅對2011年North Atlantic Books出版的《鷹之巢》英文版的引語、後記等進行翻譯:

鷹之巢堡壘,來源caspar david(artstation)
目錄:
- 介紹、其他機構評價
- 圖片(版權+出版+封面)
- 引語
- 出版商的說明
- 後記
- 關於作者
- 關於譯者

英文譯者:Michael Biggins
(翻譯自斯洛文尼亞語,並編寫後記)
介紹、其他機構評價
《鷹之巢》最初寫於1938年,是對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的一種寓言。在1960s年代,它得到鐵托Tito(約瑟普·布羅茲·鐵托Josip Broz Tito)統治下的南斯拉夫各地的邪典般的推崇,而在1990s年代巴爾幹戰爭期間,它被當作該地區衝突的寓言來閱讀,併成為德國、法國和西班牙的暢銷書。在2001年9月11日的襲擊事件之後,這本書再次獲得了新生,因為它在早期 描述了狂熱教派中的自殺式炸彈襲擊者的世界,在斯洛文尼亞的新版本中銷售了超過2萬冊。
- 美國中西部書評Midwest Book Review:
"《鷹之巢》是斯洛文尼亞作家弗拉基米爾-巴托爾Vladimir Bartol在60年前首次出版的文學經典,是一部經過巧妙研究和介紹的歷史小說,講述了世界上最早的政治恐怖分子之一、11世紀伊斯瑪儀教領袖哈桑-伊本-薩巴赫的陰謀,他用毒品和肉體享受欺騙他的追隨者,使他們相信他會把他們送到來世的天堂,從而為他執行自殺任務而毀滅自己。《鷹之巢》被完美地翻譯成了英語(還以其他18種語言出版),他把即使是最馬基雅維利的(不擇手段的)人也描繪成人類--無情、兇殘,但也受制於人類的美德、罪行和悲劇。邁克爾-比金斯(Michael Biggins)撰寫的後記介紹了作者的生活背景,將他的寫作與獨裁征服的興起(將導致爆發二戰)並列在一起,以及在作者的祖國斯洛文尼亞和世界各地對其出版的各種反應,使這部極好的傑作更加完善。這本書絕對是東歐文學書架上的必備之物,也是一部從頭到尾都非常引人注目的小說。
- 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
“由於它所有的煽動性的的想法,和有時令人毛骨悚然的先見之明,《鷹之巢》僅僅作為一個娛樂性的小故事也是成功的......巴托爾設計了一張激情,冒險和犧牲的拼貼畫,不斷變化著。書中的異國情調被描述得淋漓盡致,人物也很有魅力,很複雜--儘管他們中的一些人有狂熱的目標,要一心一意地獻身。"
- -摘自譯者Michael Biggins的後記
"《鷹之巢》......是一部精雕細琢、未被注意的小型傑作,它提供了......大量的 精心策劃、處死的細節以及象徵性、互文性和哲學解釋的廣泛潛力"。
- --伯納德·內日馬赫Bernard Nezmah,Mladina(斯洛文尼亞新聞雜誌)
"無論誰想了解基地組織領導人的戰略的成功,都應該閱讀巴托爾。就好像奧薩馬-本-拉登自己在讀完《鷹之巢》後才構思出他的組織的最強大拳頭一樣!日期的排列是致命的: 這部小說於1995年在伊朗出版,顯然非常吸引人,以至於在四年內被再次翻譯。1996年,對美國駐肯尼亞大使館的自殺式襲擊便開始了"。
圖片(版權+出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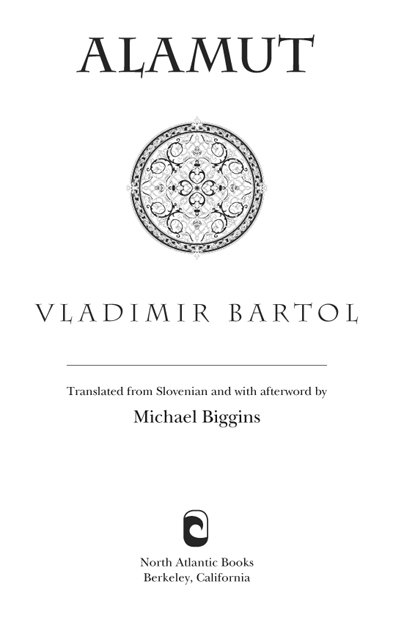
內封
翻譯版權©2007年,Michael Biggins
North American Trade Edition © 2007.
英譯本 © 2011年North Atlantic Books出版社
後記 © 2004年 Michael Biggins

外封面圖片(© 1996 Shirin Neshat, 格萊斯頓畫廊Gladstone Gallery 提供, 紐約)
Forough Farokhzad手寫:
我為花園感到遺憾
沒有人想過花
沒有人想過魚
沒有人願意相信
花園正在死去
花園的心在陽光下膨脹
花園
正在慢慢忘記它綠意盎然的時刻......
《鷹之巢》由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Native Arts and Sciences贊助,這是一個非營利性的教育公司,其目標是發展一種教育和跨文化的觀點,將各種科學、社會和藝術領域聯繫起來;培養藝術、科學、人文和治療的整體觀點;以及出版和分發關於心靈、身體和自然關係的文獻。
引語
NOTHING IS TRUE, EVERYTHING IS PERMITTED.萬物皆虛萬事皆允
-伊斯瑪儀教派的最高箴言
OMNIA IN NUMERO ET MENSURA
翻譯:https://www.latin-is-simple.com/en/vocabulary/phrase/1332/
出處:Omnia in mensura et numero et pondere disposuisti 《所羅門智訓Solomon's Book of Wisdom》
all things were ordered in measure, number, and weight.
對應中文版的封皮:秩序存於萬物的尺度與數量之中
出版商的說明
譯者邁克爾-比金斯(Michael Biggins)在該版本的後記中寫道:"對《鷹之巢》最盲目的解讀,可能會強化一些刻板的觀念,即中東是狂熱分子和不問世事的原教旨主義者的專屬家園......但細心的讀者讀完《鷹之巢》後 應該得到一些非常不同的東西。"
在出版這本書時,我們的目的是打破可恨的刻板觀念,而不是強化它們。我們在《鷹之巢》中讚美的是,作者揭示了任何意識形態如何被有魅力的領袖所操縱,並將個人信仰演變成狂熱主義。《鷹之巢》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反對信仰體系的論點,這種信仰體系會削弱一個人的道德行為和思考能力。哈桑-伊本-薩巴赫的故事的主要結論 並不是伊斯蘭教或宗教本質上使人傾向於恐怖主義,而是任何意識形態,無論是宗教的、民族的還是其他的,都可以以戲劇性和危險的方式被利用。事實上,《鷹之巢》是針對1938年歐洲的政治氣候而寫的,當時極權主義勢力在歐洲大陸上集結力量。
(高情商求生欲 ~哈哈)我們希望這些角色的思想、信仰和動機不被視為伊斯蘭教的代表,也不被視為伊斯蘭教容忍暴力或自殺性爆炸的任何證明。本書中提出的教義,包括伊斯瑪儀教派的最高格言"萬物皆虛萬事皆允",並不符合歷代大多數穆斯林的信仰,而是屬於相對較小的教派。
正是本著這種精神,我們推出了本書的此版本。我們希望你能閱讀並欣賞這樣的書。
後記
反對意識形態:
弗拉基米爾·巴托爾和《鷹之巢》
弗拉基米爾·巴托爾(1903-1967)在1938年約9個月的時間裡,在斯洛文尼亞阿爾卑斯山腳下的一個巴洛克風格的小鎮上,寫下了《鷹之巢》,這也是他唯一留下的有重大聲譽的書。當他寫早期的草稿時,在北面不到30英里的地方,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強行吞併。在西面50英里處,就在另一條邊界上,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經常追捕亞得里亞海沿岸城鎮的裡雅斯特Trieste的斯洛文尼亞少數民族,並且已經在尋求將他們的勢力範圍擴大到南斯拉夫王國的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地區。在幾百英里以北和以東的蘇聯,斯大林最血腥的大清洗達到了高潮,成千上萬的人成為受害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陰暗的地下室裡被一顆子彈擊中了後腦勺。在這種動盪和威脅中,斯洛文尼亞及其母國南斯拉夫暫時成為一個相對安寧的島嶼。如果說巴托爾在這種情況下寫下的這本書 被證明是對當時統治歐洲的大規模政治運動、魅力十足的領導人和操縱性意識形態的一種逃避,那麼這本書同時也是對它們的深刻沉思。

地理位置圖:斯洛文尼亞地理位置,來源維基詞條
最重要的是,《鷹之巢》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本好書--想象力豐富、博學多才、充滿活力、幽默風趣,故事背景設定在異國他鄉,但書中人物的抱負、夢想和不完美卻具有普遍可識別性。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鷹之巢》都可能是斯洛文尼亞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作品,最近在德國、法國和西班牙,《鷹之巢》的譯本已成為暢銷書。儘管《鷹之巢》表面上看似通俗文學,但它同時也是一部精心製作、尚未被發現的小眾傑作,為讀者提供了大量精心策劃和執行的細節,以及象徵、互文和哲學詮釋的廣闊潛力。
巴托爾本人是來自的裡雅斯特的斯洛文尼亞族人,曾在巴黎和盧布爾雅那Ljubljana學習,最終定居斯洛文尼亞首都,從事文學創作。1927年(24歲),巴托爾在巴黎求學期間,一位斯洛文尼亞同胞瞭解到巴托爾作為作家的抱負,建議他借鑑《馬可-波羅遊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中"山中老人"的情節,作為短篇小說或長篇小說的素材。這個故事是馬可·波羅沿著絲綢之路經過伊朗時聽到的,講述的是一個強大的地方教派軍閥,據說他利用大麻和一個秘密的少女花房欺騙年輕人,讓他們相信他有能力將他們帶到天堂,並隨意將他們帶回人間。因此,他贏得了年輕人的狂熱忠誠,能夠派遣他們到世界任何角落執行自殺性的政治暗殺任務,從而擴大他的權力和影響力。巴托爾將這一主題銘記於心,並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對這一故事的廣泛歷史背景進行了廣泛研究,同時發明了自己的小說情節和結構。完成這部小說成為他的激情和存在的理由。他在日記中懇求命運之神讓他活著完成這本書,並將其安全地交到印刷商手中。經過長達十年的漫長醞釀,在巴托爾於卡姆尼克Kamnik鎮度過的緊張而隔絕的幾個月裡,這部小說經過四易其稿,終於躍然紙上。從各方面來看,巴托爾在此期間都非常快樂,正如我們所想象的那樣,一個知道自己正在創作一部傑作的人應該是快樂的。
不幸的是,這部傑作面世的時機並不完美。《鷹之巢》的發展軌跡首先因1941年至1945年德國和意大利吞併斯洛文尼亞而中斷,然後又因鐵托領導的共產主義南斯拉夫的文學意識形態而中斷,多年來,這本書一直被視為一種威脅。此外,該書的主題和風格與二戰前後斯洛文尼亞文學的主流趨勢完全不同。在語言上與世隔絕的小國,作家們往往有一種強烈的需要,那就是書寫特定小國的生活,這或許是一種幫助證實和鞏固國家存在的方式。由於《鷹之巢》除了語言之外沒有任何斯洛文尼亞特色,因此他的作家朋友們將巴托爾稱為"斯洛文尼亞遺傳密碼中的一個錯誤"。這是一部以伊朗西北部為背景的冒險小說,書中有些地方寫得類似於《一千零一夜》,圍繞著該地區講巴列維語的什葉派穆斯林本土居民與塞爾柱土耳其遜尼派穆斯林統治者之間的深刻矛盾展開-這部小說可讀性強、研究透徹,用簡潔的散文風格描繪了豐富多彩的場景,展開了懸念迭起的情節,而不是通常的斯洛文尼亞農民、地主和城鎮居民之間的矛盾故事。巴托爾本人曾說過,多年後,他的一位老同學在街上找到他,告訴他:"我讀了您的譯本,非常喜歡。""什麼譯本?"巴托爾回答道。"那本胖胖的小說,某個英國或印度作家寫的那本,"那人解釋道。"你是說《鷹之巢》嗎?"巴托爾問。"是我寫的。"那人聽了哈哈大笑,不屑地揮揮手說:"走吧,離開這兒。你騙不了我。"然後他走開了。普通讀者難以想象,一個斯洛文尼亞人能寫出如此完全脫離自己歷史經驗的故事--這肯定是外國人寫的。巴托爾本人認為斯洛文尼亞作家協會分為兩類:一類是民族主義者,他們佔大多數,表達了他所謂的"對自己時代的痛苦哀嘆";另一類是世界主義者,他們有更廣泛的歷史感,但佔少數。毋庸置疑,巴托爾認為自己屬於第二類,即被普遍誤解的一類。
巴托爾在《鷹之巢》一書中的優勢之一是,他能夠在小說中幾乎不露痕跡,讓他筆下的人物講述故事。小說中沒有作者的聲音,沒有作者的評判,也沒有作者的指示,讀者不知道該支持哪個人物,該指責哪個人物。事實上,讀者可能會發現自己的擁護在故事過程中發生了變化,變得困惑和矛盾。巴托爾當然想寫一本神秘的書。文學史家們從巴托爾的傳記、個性和其他作品中尋找理解《鷹之巢》的鑰匙,但作者生活中的許多事情仍被隱藏起來。《鷹之巢》對各種解釋持開放態度,這也是該書令人受益匪淺的原因之一。
也許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鷹之巢》作為一部廣義上的歷史小說,雖然是高度虛構的十一世紀塞爾柱統治下的伊朗。從這一角度出發,讀者可以欣賞到小說對歷史背景的嚴謹研究,普遍沒有不合時宜的史實,對伊斯蘭教什葉派和遜尼派衝突起源的描述,以及對一千多年來該地區原住民對外來佔領者(無論是穆斯林還是非穆斯林)根深蒂固的怨恨的闡述。作者善於在這一環境中塑造富有同情心、複雜而又與時俱進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的志向和恐懼在讀者心中產生了共鳴,這種共鳴超越了人們對異國情調風景的固有期待,使這部以歷史為重點的小說讀起來特別逼真和感人。
對《鷹之巢》的第二種解讀將其意義牢牢地固定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巴托爾所處的時代,將其視為二十世紀早期歐洲極權主義興起的寓言代表。在這種解讀中,伊斯瑪儀教派的超理性主義領袖哈桑-伊本-薩巴赫成為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綜合描述。事實上,巴托爾原本打算將他的書的第一版獻給"貝尼託·墨索里尼",當他被勸阻時,他提出了一個更通用的獻詞"獻給某位獨裁者",但同樣被否決了。無論是哪種題詞,幾乎都可以肯定是一種大膽的諷刺,但他的出版商正確地看到了當時動盪時期的風險:讀者流失、當局惱羞成怒。其中一些人物似乎取材自當時新聞片中的真實人物。哈桑的得力助手阿布·阿里(Abu Ali)向鷹之巢士兵發表鼓舞人心的演說,其方式讓人想起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鷹之巢城堡夜間隆重的照明儀式可能暗指納粹黨的燈光集會和火炬遊行。伊斯瑪儀教派嚴格的組織等級制度、一些人物與法西斯或國家社會主義陣營中相應類型的人物之間的廣泛相似性、意識形態作為對大眾的蠱惑的核心作用,都與當時德國、意大利和蘇維埃俄國存在的社會和權力結構產生了共鳴,哈桑核心圈子逐漸提高的知識水平和與意識形態的臨界距離也是如此。
最近,另一種解釋試圖說服我們,《鷹之巢》是理想反應了斯洛文尼亞對當時威脅斯洛文尼亞和歐洲其他國家的德國/意大利極權主義的影射小說--換句話說,是哈桑作為希特勒解讀的鏡像。這種解讀著眼於巴托爾在的裡雅斯特周邊地區的出身,以及他對意大利從1920年代開始在這些地區統治和迫害斯洛文尼亞族的無可爭辯的憤怒。巴托爾與斯洛文尼亞恐怖組織"Tigers"的頭目私交甚篤,"Tigers"成員在意大利與斯洛文尼亞邊境地區對意大利機構和個人進行暴力襲擊。(該組織在斯洛文尼亞的名稱"TIGR"實際上是四個主要爭議地區名稱的縮寫:的裡雅斯特Trieste、伊斯特拉Istria、戈裡齊亞Gorizia和裡耶卡Rijeka[意大利語Fiume])。1930年(27歲),當他的朋友被意大利人抓獲並被判處20年監禁時,巴托爾在日記中簡介而不祥地寫道:"Zorko,我會為你報仇的。"哈桑的正面特質--他的理性、智慧和機智--以及他在小說後期對他的另一個年輕自我伊本·塔希爾(ibn Tahir)的啟示性告白,即他一生的工作都致力於將伊朗的巴列維族從外國統治下解放出來,所有這些似乎都支持這種觀點:即這部小說是對被壓迫的斯洛文尼亞人的伊索(寓言)式的勸誡,其重點是頌揚解放運動領袖哈桑/Zorko的人格魅力和馬基雅維利式的聰明才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GR
但是,儘管對鷹之巢的這種斯洛文尼亞民族主義解讀可能很誘人,但最終卻顯得膚淺而平淡。首先,哈桑的民族主義--巴托爾不合時宜地借鑑了幾百年後產生於18世紀歐洲思想的意識形態--如何能與哈桑更詳盡闡述的虛無主義、他對所有意識形態的摒棄、他對權力作為宇宙統治力量的接受以及他對權力本身的無情追逐相提並論?此外,任何有自尊心的人,不管是斯洛文尼亞人還是其他人,怎麼會把一個基於玩世不恭地操縱人類意識和人類生活以達到操縱者自己的目的的宣言放在心上呢?試圖將《鷹之巢》作為一部隱晦的民族解放論著,也與巴托爾本人自相矛盾地宣稱作者不關心政治背道而馳。最終,它們是以簡釋繁的、自相矛盾的,將這部讀起來感覺像一部多面的、內涵豐富的文學作品變成了一部二維的意識形態的空談。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今天,以及對《鷹之巢》的解讀,這種解讀必然是特別誘人的,因為美國已經遭受了東方復仇女神的哈桑式打擊,並以不可估量的破壞力進行了反擊。這種解讀將把鷹之巢視為一個預言性的願景,即使不是,至少也是對21世紀初的基本衝突的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預示:一方面 是一個靈活的、不可預測的後起之秀,依靠一個相對較小但緊密交織、自我犧牲的特工網絡;另一方面是一個龐大的、笨重的帝國,不斷處於守勢,而且很可能在其採取的每一個重點不突出、出於政治動機的進攻性步驟中為其對手招募新兵。今天基地組織與西方國家之間的衝突故事可能是一個不經意間掩蓋了一千多年前類似鬥爭的半湮沒記憶的拼貼畫:受傷和受辱的普通民眾容易接受激進和復仇形式的宗教的召喚;操縱性的激進意識形態向其新兵許諾以超凡脫俗的回報來換取他們的最終犧牲;傲慢、自我滿足的佔領國,其主要目標是從其佔有的土地上攫取新的利益;以及激進領導人的不祥預言,即有一天"甚至遠在世界另一端的王子也將生活在對其權力的恐懼之中"。但無論我們在巴托爾筆下的十一世紀和我們的二十一世紀之間找到多少相似之處,這些相似之處都不能預知未來。鷹之巢沒有提供任何政治解決方案,也沒有提供任何展望未來的窗口,只有對歷史進行細緻而有同理心的解讀所能提供的清晰視野。誠然,美國讀者可以從《鷹之巢》這樣的書中學到很多東西,晚學總比不學好:得益於巴托爾廣泛而細緻的研究,對伊拉克和伊朗的歷史複雜性和連續性(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基本教育是這部小說的有益副產品之一。
任何一種解讀都是可能的。但所有這些解讀都忽略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基本事實,即《鷹之巢》是一部文學作品,因此它的主要任務不是以線性的方式傳達事實和論點,而是做只有文學才能做的事情:在像生活本身一樣複雜和模稜兩可的掛毯中,為細心的讀者提供發現更深層、更普遍的人性真理的途徑,發現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以及我們的觀念如何塑造我們周圍的世界--從根本上說,認識我們自己。巴托爾並沒有明顯地介入敘事,以他想要的方式引導我們理解。相反,他用微妙的線索和一些虛假的誘餌來設置場景--就像現實生活中那樣--然後讓我們從錯覺中分辨出真相。對《鷹之巢》最盲目的解讀可能會強化一些刻板印象,即中東是狂熱分子和不容置疑的原教旨主義者的專屬家園。(那麼,如何看待歐洲六十年前產生的黑衫皮衣暴徒大軍呢?) 真正變態的解讀可能會發現這是在為恐怖主義道歉。這種風險是存在的。但細心的讀者應該會從鷹之巢中得到一些非常不同的東西。
首先,鷹之巢對意識形態進行了徹底的解構--包括所有教條式的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違背常識,許諾用生命或判斷和選擇的自由來換取前往安拉的國度。當然,還有哈桑對伊斯蘭教義及其宗教替代品的長篇啟蒙抨擊,他圍繞自己的人生經歷、年輕時對真理的追尋以及接連不斷的幻滅展開敘述。他講述了自己如何通過專注於經驗、科學和感官所能感知的事物來超越個人危機。但是,這種實證主義發展成為一種超理性主義,將人類經驗中的情感方面視為非理性和無效,從而使自己變得教條。在極端情況下,哈桑的理性主義宣揚沒有絕對的道德約束,權力至高無上,是世界的統治力量,必須操縱較低等的人類以實現最大的權力和推進他自己的目的--這在他的教派的最高格言中得到了明確闡述:"萬物皆虛,萬事皆允"。
然而,巴托爾讓我們看到的這個人物的複雜性和弱點可能比哈桑本人承認的還要多。我們可以短暫瞥見他對一生的對手尼扎姆-穆勒克(Nizam al-Mulk)的刻骨仇恨,尼扎姆-穆勒克在小說中是他的主要死對頭和復仇對象。我們兩次看到了他突然感到宇宙中的孤獨和脆弱時的驚恐。在小說的高潮部分,他自相矛盾地揭示出,他一生最大的驅動力是對自己國家的塞爾柱統治者的強烈憎恨。我們看到他多次無聲卻明確地拒絕了情感和肉體聯繫的機會,儘管他內心深處同樣明確地渴望這些機會。所有這些非理性的衝動都威脅到了他的理性主義意識形態,因此必須加以壓制,但在壓制這些衝動的過程中,哈桑抹殺了自己人格的某些方面。結果,哈桑成了一個情感畸形、智力超群的人--他的悲劇性在於他所掌握的巨大權力。
在小說的後半部分,哈桑將他策劃的各種相互關聯的事件稱為"我們悲劇的下一幕",但似乎並不清楚他所指的是誰的悲劇。在本書的最後一章,當哈桑展望未來時,他提到了"我們這些掌握著這一機制線索threads of this mechanism的人",意指刺客教派的可怕機制。除了讓人聯想到哈桑作為木偶大師的形象(他的確是),這些具象的線和機制還與他閹人僕人經常用來將他吊到塔樓房間的滑輪和繩索操作的升降機相呼應。考慮到哈桑在那個簡陋的升降機裡也感到很脆弱,他不知道如果閹人突然意識到他們被貶低的狀態,決定切斷繩子把他摔死會發生什麼,哈桑作為意識形態大師和操縱者的最終形象變得非常模糊。在書的最後幾句話中,他被神化了,他升上了他的塔樓,將在那裡度過餘生,編纂伊斯瑪儀教法和教條,再也不會出現,這是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結局。哈桑這個人物沒有完全意識到的是,他把自己推向了理性的極致,以理性的名義自願與人類社會分離,屈從於自己"機制"的"線",他使自己成為了這場悲劇最突出的受害者。
小說中許多情感的火花不是通過敘述或對話產生的,因為敘述或對話是以理性為主導的,而是在一些主要人物之間不經意的、微妙的口語交流中產生的。這些稍縱即逝、有時看似不經意的情感描寫--不自覺的面部表情、眼神、臉紅、肢體語言、壓抑的情感湧動--遠比言語更能表達人物的真實情感。這些情感交流通常是不完整的,部分原因是它們代表的是不完整的時刻,部分原因是所謂的更高境界(就義士而言,是意識形態;就女孩而言,是責任;就哈桑而言,是"理性")總是設法在它們能夠充分表達自己之前就將其壓垮。然而,這些都是小說中最明顯、最能揭示真相的時刻。
個人主義哲學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大放異彩,他們將人際關係中這些高度緊張的誠實和脆弱時刻視為神力顯現的主要媒介。作為對教條主義宗教和社會科學中類似的還原論傾向(當時主要是弗洛伊德心理學和馬克思主義)的反擊,個人主義對人類個性的各個方面給予了同等的重視,從生物、社會和歷史到心理、倫理和精神。與巴托爾同時在巴黎學習的還有他的一些年輕同胞,他們後來都成為了重要的個人主義知識分子,其中包括心理學家安東-特爾斯滕雅克(Anton Trstenjak)和詩人愛德華·科奇貝克(Edvard Kocbek)。儘管弗洛伊德和尼采作為巴托爾的早期影響最常被提及--當然哈桑也完美地體現了他們的教誨--但鷹之巢最終對綜合人類發展的重視表明,如果有任何意識形態對巴托爾仍然重要,那一定是類似於個人主義的東西。
從這個角度看,本書的雙重座右銘開始變得有意義了,這些座右銘顯然相互衝突,多年來也一直是評論家們感到沮喪的根源。如果說"萬物皆虛,萬事皆允"象徵著給予伊斯瑪儀教派精英的許可,那麼與之無關的副座右銘"秩序存於萬物的尺度與數量之中Omnia in numero et mensura"則具有最終的警示意義。萬物都有尺度,不過分。換句話說,懷疑論和理性是重要的資產,但過度依賴懷疑論和理性而犧牲同情心,就會導致哈桑的悲劇,就像他的有意和無意的受害者一樣。
巴托爾將自己的許多品質和個人興趣融入到對哈桑和小說中其他人物的描繪中。他熱衷於哲學、歷史、數學和自然科學。他是一位業餘昆蟲學家,(與另一位比他年長四歲、著有《洛麗塔》一書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一樣)是一位狂熱的鱗翅目昆蟲學家。在這個登山愛好者雲集的國家,巴托爾與他們中的佼佼者一起登山。與一位年長他三歲的法國著名作家一樣,他也是一位熱情而熟練的小型飛機駕駛員--而這一切只是他作家生涯的前奏。一個如此興趣廣泛、如此渴望體驗的人,要麼是被生活所迫,要麼是痴迷於生活。在私生活中,巴托爾是後一種性格類型的典範,但在他的小說中,他選擇了前一種性格類型的極端寫照。
在1957年(54歲)出版《鷹之巢》時發表的一篇評論中,年長的巴托爾-現在對讀者更加關心了-寫道:
《鷹之巢》的讀者肯定會注意到一件事。無論哈桑使用多麼可怕、不人道和卑鄙的手段,受他控制的人們從未失去最崇高的人類價值。他們之間的團結意識從未消失,友誼在他們之間發揚光大,就像花園裡的姑娘們一樣。伊本·塔希爾和他的戰友們渴望瞭解真相,當伊本·塔希爾發現自己被最信任、最相信的人欺騙時,他所受到的震撼不亞於他得知米莉安對他的愛是一場欺騙。最後,在哈桑所有嚴峻的知識中,他是不快樂的,在宇宙中是孤獨的。如果有人想從作者那裡瞭解他寫作《阿拉穆特》的意義,瞭解他在寫作過程中的基本感受,我會告訴他:"朋友!兄弟!讓我問你,還有什麼比友誼更讓人勇敢的嗎?還有什麼比愛情更感人的嗎?還有比真理更崇高的東西嗎?"
(Michael Biggins -2004年8月)
關於作者
弗拉基米爾·巴托爾(1903-1967)是南斯拉夫的主要知識分子之一,也創作戲劇,短篇小說和戲劇評論。在巴黎索邦大學學習後,巴托爾在的裡雅斯特度過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他在盧布爾雅那去世,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絕版了,在他的同胞中幾乎無人知曉。
關於譯者
邁克爾·比金斯MICHAEL BIGGINS翻譯過許多斯洛文尼亞當代著名作家的作品。 目前,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斯拉夫語言和文學系任教,併為俄羅斯和東歐研究的圖書館館藏進行策劃。


封面作為結束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