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傑斯帕到達他郊區的住宅時,燈是關著的。他在一片漆黑中摸索著行走,隨著傢俱逐漸從黑暗中顯現,他的眼睛適應了黑暗。他甚至沒脫掉鞋子。這裡乾淨且幽靜,超過半數的寬體玻璃窗剛剛清洗過。有人已經為特雷斯鋪好了床。聯合警探的嘔吐桶已經被移走了,鑲木地板閃閃發光。傑斯帕冬季靴子上的泥浸溼了羊毛地毯。書櫃將睡眠區從主臥裡單獨隔開,而傑斯帕停下了步伐。他看著印有“歐佐納爾”,“En Provence[94]”,和“*茶店*”的購物袋。空氣中瀰漫著綠茶的香氣。一條玲瓏的銀色短裙掛在衣架的衣帽鉤上。織物面料在黑暗中閃閃發光。
男人伸出雙手,撥開門簾溜進臥室。月光透過角落的窗戶灑在床上。傑斯帕的模特*女友*安妮塔在床上睡覺,一頭金髮散在黑色枕頭上。一道陰影沿著少女的身體延伸,後者被突出的肋骨彎曲,胸部有一個胎記。傑斯帕看著她的胸部升起。他嘗試回憶。四年了。他們在一起四年了。她現在多少歲,十九歲?傑斯帕三十四歲了。
“呲,嘿,醒醒!”睡夢中的女孩像孩童一樣咕噥著。傑斯帕對著她的耳朵吹氣,金色的長髮在他的氣息下顫動。“安妮,醒醒,我是傑斯帕,嘿!”
“呃嗯…傑斯帕,到床上來。”女孩把毯子的邊緣拉到下巴下。“這裡舒適又涼爽...”
“聽著,我不能。我得走了。”
“走…又去哪?”
“醒醒,我們聊一會兒。你想讓我給你煮杯茶之類的嗎?”
“我給你帶了茶,看到了嗎?”瓦薩-奧蘭冶混血模特伸出手,她的關節咔咔作響,黑色陰影移動到毯子的表面。“是的,我看到了。非常感謝。你非常貼心。”
女孩懇求著,昏昏欲睡的元音和她的雙腿一樣長:“明天再談吧,傑斯帕,讓我們上床睡覺…”
“明天不行,我說過我要走了。”傑斯帕看著女孩的臉。沉默。翻轉數字時鐘發出短暫的沙沙聲,窗外的風呼嘯著。
女孩突然發出鼻息聲:“哼,別再和你朋友去森林裡了,我根本見不到你。我們明天呆在一起吧。我是為你而來的,記得嗎?”
“不,你不明白。我*今天*就要走。”
“今天?現在幾點了?”白色鐘錶噼啪一聲。“凌晨兩點!這個點你要去哪?你最近的行為非常古怪!”女孩用胳膊肘撐起身,憂慮地皺著眉,抿起嘴。
“我來這兒是因為你,否則我不會來的。”
“我道歉,真的。我也為我即將提出的請求道歉。但求你了,從床上下來一會兒,我得移動一下它。”
“你放了什麼在那兒?”
“東西。”
女孩站在冰涼的地板上,一隻腳貼在另一隻腳上摩擦著,疑惑地看著傑斯帕移動床。床腿發出吱吱聲,瓦薩-奧蘭冶混血模特把毯子披在肩上,就像斗篷。她非常漂亮,但再也沒有任何意義。
“你要去哪?”
傑斯帕跪下,地板用咔咔聲回應他。“消失。”活板門敞開,傑斯帕從裡面提出一個打包好的雪白行李箱。
“那你什麼時候從消失中回來?”
“我感覺能給你的所有聰明的答覆都太過冰冷。所以我最好什麼都不說。”鎖開了,傑斯帕從行李箱的口袋裡拿出一包文件。女孩很惱火。她喜歡那些傑斯帕——在家煮茶的傑斯帕,才思泉湧的傑斯帕,在表示支持時尷尬的傑斯帕——但她不喜歡這個傑斯帕。“請別把我當成傻瓜。現在你不是在接受文化採訪。”
“那好吧。”傑斯帕焦慮地捲起文件:“你還記得我那時告訴你的倫德家女孩的事嗎?我認識她們,她們失蹤了,等等。”
“在我父母的夏日度假小屋裡?”女孩仍懷疑地蹙著眉,但她的嘴巴在記憶中軟化了。“你那時醉得厲害!”
“看,這就是我不喝酒的原因。”傑斯帕尷尬地笑了。“但是你非要求我喝,對吧?”
“你那次太搞笑了!”
“太搞笑了。”傑斯帕苦澀地強調。“那時候。好。我很搞笑。但現在,我要去找她們。”
“誰?”
“科尼利厄斯·古爾迪特[95],你以為是誰?”
模特靠在牆上時,從膝蓋傳來複雜骨骼結構的咔咔聲。“但你說過那毫無意義!你說過那件事已經結束了。還是說你記不得你說過什麼?”傑斯帕用捲起的文件敲擊著手掌,在地板上若有所思地踱了幾步,好像需要與另一個傑斯帕商量——在安妮塔父母的夏日度假小屋裡喝醉的那個。一個非常不合適的事件。一個非常不合適的傑斯帕。但仍然比現在的這個無助的生物聰明千百倍,優秀千百倍。他用捲起的文件撓了撓頭上的金髮,開口道:“有希望。”
“傑斯帕…”
“你明白的,我*必須*去。”
傑斯帕把他真正的房契放在女孩的手上。“留在這兒,拿走我的房子,住在這兒,求你了。以最快的速度賣掉城裡的兩套公寓,明早價格就會開始下跌。早晨的第一件事,去找我的經紀人。這是電話號碼...”女孩的肩膀顫抖著,但她什麼都聽不見,只有風在窗外低語。傑斯帕在他的模特面前蹲下身,他的冬季大衣下襬碰到了鑲木地板。他把手放在女孩的肩膀上。
“嘿,我去煮點茶來,好嗎?”
時鐘嘀嗒,“2:30”。杯中的蒸汽飄到地板上,方形糖碗裡放著棕色方糖,還有一個用於舀方糖的特製勺子。茶倒得很困難,但並沒有燈被點亮。
“2:45”
“我不明白。現在這些還有什麼意義?”女孩在漫長沉默的結尾吞嚥著。
“呃,你認為它有什麼意義?”
“而且每到這時,你就拿出那個行李箱。”女孩用食指指著房間中央。“就好像我根本不存在。”
“它在那的時間比你久。”
“什麼,我還得說服你嗎?”
“呃,行了,嘗試理解一下。”
“嘗試理解?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模特憤怒地把茶杯摔在地板上。“我認為倫德女孩的整件事都是胡說八道。你就是個戀童癖。”
傑斯帕遭受背叛的表情令人印象深刻。女孩甚至都驚訝於自己詞語的威力。對於這一點,且只在那一刻,她因此而後悔。
“行。”男人在判決中站起身。他提起行李箱,冷靜地穿過門簾走了出去。隨後,安妮塔的挫敗感再次佔據上風,一絲不掛的憤怒模特跟在傑斯帕身後,衝進大房間裡。
“讓你的立方體滾一邊去!我才不要呆在這個荒涼的卡特拉破洞裡!”花白的文件從她手中飛出,散落在黑暗的房間裡,一張接著一張,紙頁落在極其優雅的交叉縫式木桌和鑲木地板上。傑斯帕仍然沒有轉身,他停下腳步歪了歪頭。“那你以為你不留在這兒還能去哪兒?你要去格拉德彈藥工廠上班嗎?”
“你太可悲了!你和你的*女孩們*,只有可悲。所有人都警告過我!我在小屋那次之前就知道了!所有人都知道!我那時只有十五歲,我太傻了…”
安妮塔喘著氣,一隻手撐在廚房檯面上。“安妮長安妮短。我的名字不是安妮!”傑斯帕感到他的手變得冰冷。“病態”這個詞再次席捲而來。他記起那時的自己,一個未成年的內衣模特依偎在身旁,他說著“晚安,安妮。晚安,安妮。晚安。”我太幸福了。她睡著了,窗外的樹枝沙沙作響,就像第二次機會。那有什麼可悲傷的?太美妙了!
模特走回臥室,並在莫名的惡意中大喊:“*晚安,安妮*!”
人類的心靈是天生相互信任的。一開始,他並沒有考慮過這種巧合的噩夢可能發生。但是傑斯帕自己的想法和房間裡逐漸明顯的嘲諷聲區別越明顯,男人的呼吸就變得越緩慢。似乎因為羞恥,身體已經準備好停止工作了。他從地上撿起文件,一次一張,然後平靜地在大腿上整理好。他挑選著詞語,並不清楚他真正想攻擊的人是誰。世界,大概吧。他走回臥室,把文件放在床頭櫃上,擺出那張可怕的王牌。
“你是怎麼想的,你覺得還能回瑞瓦肖?那裡的事物已經不再*美好*了。過來,看看它。”
女孩坐在床上,正生氣地嘗試穿上她的晚禮服,並沒有完全理解有任何過度焦慮的必要。
“*那座城市*不存在了。”傑斯帕重複著,現在女孩驚慌失措地站了起來。
“你什麼意思?”
“你知道的,他們已經失聯五天了。”
“我不知道!和誰聯絡?”
“瑞瓦肖,爆炸了,消失了。你真的應該多看看報紙!”
“你在開-玩-笑嗎!”
傑斯帕,被複仇矇蔽了雙眼,並不清除他的謊言會把他帶去哪裡。他有個想法,但已經晚了。女孩劇烈地喘著氣,雙手因恐慌而顫抖。她用指甲咔噠一聲按下按鈕,收音機的黃色顯示屏在黑暗中亮起。撥盤在她的手指下旋轉,當指針劃過短波頻率時,嘶嘶聲和尖叫聲充斥著揚聲器。外國新聞報道的播報聲在緊張中保持著專業素養,一切都混亂不堪。她的國際化思維只抓住了可怕的碎片:“梅斯克侵略者”,“聖米羅”,“瑞瓦肖”,“原子武器”以及“一半的人口”。女孩抖動得如此劇烈,令傑斯帕不禁擔憂起她的身體健康。這臺易碎的機器隨時都會分崩離析。終於,畫外音宣佈了死亡人數,當外交部提供的國內旅客名單,以一種獨特漠然的播音腔滾動播報時,女孩受傷地癱倒在地:“...著名歌手佩妮拉·倫德奎斯特錄製了她的第三張錄音室專輯...”安妮塔因恐懼而睜大的大眼睛,在黑暗中黯淡下去。她尖叫起來:“天啊!我的姐姐!我的姐姐在那兒!”
“我很抱歉。”傑斯帕說。
“你確定嗎?他們怎麼能確定?為什麼他們什-麼-都-不-做?”
“我不知道。”傑斯帕提起他的行李箱。
女孩像匹馬一樣喘著粗氣,嘴巴扭曲成巨大而黑暗的尖叫。世界都有被那張嘴吞噬的風險。也確實如此,傑斯帕記不得更多的內容了。在尖叫的真空裡,無比潔白的雪花打著旋,混凝土牆面反射著房間裡的回聲:“別走!”傑斯帕關上身後的門,站在屋前,手腕上是她的指甲造成的淤青。庭院裡下著雪。天氣很冷,寒風在呼嘯,他滾燙的皮膚冒著蒸汽。他抓了滿滿一把雪,把它們揉搓在臉上。在庭院邊緣,冷杉樹隧道的嘴巴處,有一輛黑色機動車。特雷斯·馬切耶克在會客廳的光芒中走下車,向他揮手致意。傑斯帕手提白色的行李箱穿過庭院,大衣在風中颯颯作響。冷杉樹分隔開遠處的雪堆,*zig zag dröm*。隨後突然間,世界變得如此之輕,就好像他身體裡所有的意義都被抽離。從今往後他再也沒有任何價值。傑斯帕微笑著。
出租車裡很暖和。當他跨過汗落座時,汽車在搖晃。特雷斯關上車門滑進了車廂。
“進展如何?”
“呃,咱們只能說進展不怎麼樣。”傑斯帕答道,然後花了點時間整理自己。“開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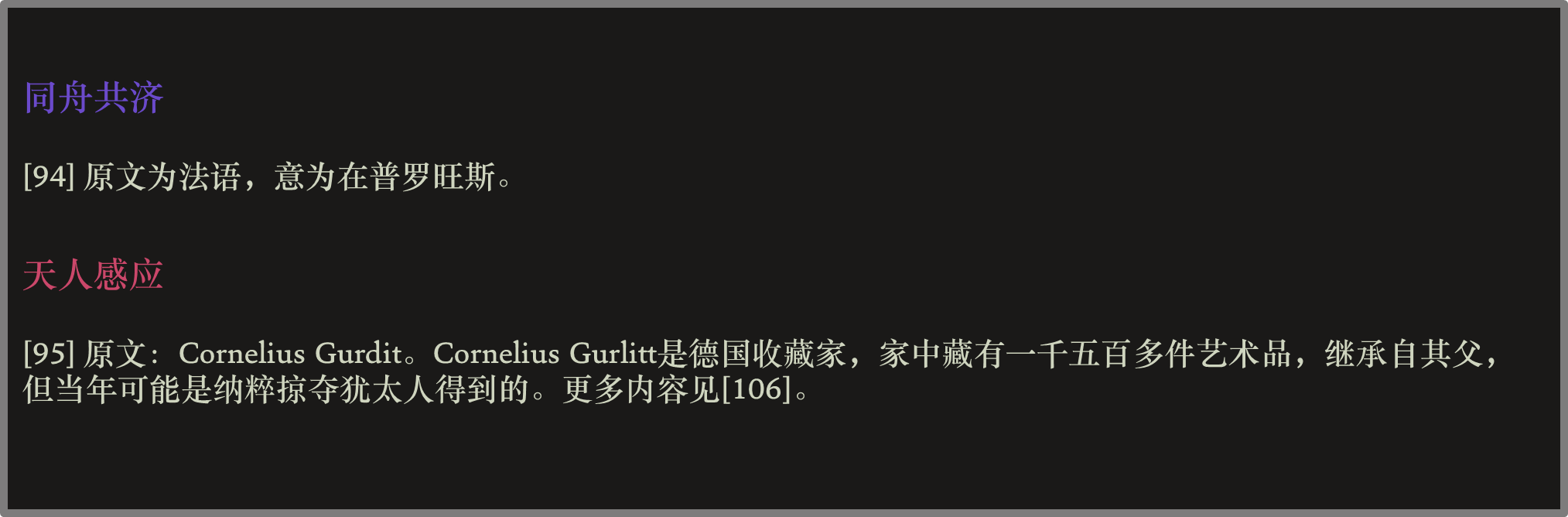
--------------------------------------------
七天前,星期一的前一天晚上。
出租車窗裡的城市像迪斯科一樣迸射飛濺,失去理智的特雷斯顫抖著。傑斯帕緊緊地扶住他:“聽著,他犯了癲癇之類的病,很嚴重。我們得帶他去醫院。”
“特雷斯,聽著,”汗俯身靠近他的朋友,“我們帶你去醫院,好嗎?”
“不!”特雷斯攥住汗的夾克。“求你了!”
男孩們疑惑地看向彼此,然後聳了聳肩。特雷斯的臉已經完全被汗浸溼:“你得向我保證!保證你不會把我帶進去!”他的下巴顫動了一陣,隨後呆滯的眼神又重回他的雙眼,身體則像原木一樣僵硬。“搞什麼鬼?”傑斯帕搖晃著特雷斯,把手放在他的嘴巴底下。
“他在呼吸,你懂的,我不知道,要不我們就別帶他去了,行嗎?”
“行,那就不帶他去了。去你那兒?”
傑斯帕重重地嘆了口氣。“好…好吧,那就去我那兒。只是有一個問題。有個女孩後天從瑞瓦肖來這兒,你怎麼看,他不會介意吧?”
汗沒好氣地搖搖頭。“我怎麼知道,你認識私人醫生嗎?”
“私人醫生,汗!你不在醫院工作的話是沒法獲得執照的!”
“呃,好吧,我還以為*你*認識一些人。”
“我認識一個普通的醫生,汗。正常的可以嗎?”
“普通的可以,別生氣。”
出租車在夜晚的瓦薩城裡疾馳。有時特雷斯會變成油氈推銷員,隨後變為赫德,接著是迪雷克·特倫特默勒,之後再次變回特雷斯·馬切耶克。有時他覺得他並不真的在那裡。瓦薩爆炸的色彩被水母一樣的黑色墨水籠罩,水族箱變暗了。而特雷斯的制服是最深的黑色,它由樹葉,自行車胎上的爛泥和城市上空的蒼穹製成。他拉直袖口,調整好領結。他禮貌而莊重。制服有乾洗的味道,隨後,像是墓地裡白樺樹下的雨傘,一場葬禮派對在他面前揭開。日思夜想的,終日惶恐的,都在那裡!葬禮上,是女孩們的母親,她戴在頭上的黑色蕾絲喪紗下,潛藏著因憂愁而堆起的優雅皺紋。造紙商卡爾·倫德將傘舉在女人頭邊。白樺樹葉振顫著,這是終結夏日之雨。
汗和傑斯帕也出席了葬禮。連汗的母親都來了,還有班級裡的所有人。他們現在都老多了。他們中的大多數特雷斯都認不出來,不過那邊的肯定是西克斯滕,還有那個是小奧列爾。馮·菲爾遜則在和他的男僕閒聊。還有齊吉!全校最淘氣的孩子也在那兒,依然穿著他的黑色皮革外套。只有傑斯帕的傘是白色的。特雷斯走過葬禮場地,所有人都在低聲交談,輕拍彼此的背。他經過時,人們恭敬地向他點頭致意。女孩們也在那兒,就在簇擁著的鮮花下,鬆軟透氣的泥土裡。她們是一排趾骨,操作杆一樣的肋骨以及像是聖物的鎖骨。沒有缺失的東西,一切都保存完好。相關記錄像學校論文一樣簡潔,這是一部鑑定學的*代表作*,她們今後會在學院中教授它。還有滿滿一把牙齒——瑪姬的乳牙,安妮顎骨上的珍珠,馬琳刻薄到不能再刻薄的虎牙——一切都在那裡,一切都嚴絲合縫:所有的小填充物,安妮臼齒上缺失的一塊,自行車事故。還有夏洛特露出的電影明星的微笑。某些人十分樂意從那裡帶走其中的一部分,只為留作紀念。那些珍貴的石頭將在他們手中發出多麼美妙的叮噹聲!但你不能那麼做。那是不專業的。
星期一晚上到星期二,一個醫生來注射生理鹽水。特雷斯終於恢復了意識,舉行葬禮的地方又陰又冷,一切都是灰色和銀綠色的。在野櫻梅灌木上的灰色帳篷裡,桌上擺著一個帶有水果圖案的古典水晶。這裡很安靜。有什麼東西在灌木中沙沙作響,聽起來像無線電信號。當特雷斯清醒後,他明白了那是什麼。北方公路崩塌的新聞讓公共空間被憂心忡忡的氛圍籠罩,而他並不想順從。特雷斯讓傑斯帕調到古典電臺。他們說的古典電臺,會播放死去的貧窮白種人音樂,即使在世界已終結許久後。普魯斯·米特雷西澎湃的音樂,聽起來十分優美,就像海洋,嗯…墳墓。所有人都在慢慢舞蹈,特雷斯越是想象它,就越清楚葬禮派對永遠不會舉行。這次調查讓人噁心透頂。到了星期二早上,他已經準備好向自己承認,他們永遠不會知道在倫德家孩子們的身上發生的事情了。
--------------------------------------------
高跟鞋在出租車裡的底板上留下印跡。女孩翹著二郎腿,塗成珊瑚色的腳趾甲排成一排,裸色綁帶環繞在她的瑟吉·範·迪克上。一簇寶石閃耀在綁帶的交叉點。優雅,你會說?如果這是一雙粘著粗製濫造的水鑽,在百貨商店售賣的鞋,那就是純粹的faux pas[96]!但是這隻瑟吉·範·迪克——我們正在注視的——價值一萬雷亞爾。另一隻還要貴五百雷亞爾——保養原因。一顆孤鑽從瑞瓦肖的德爾塔跳躍到這個骯髒的地方,多麼令人頭暈目眩的夜晚!此外,瑟吉·範·迪克本人說過,優雅和虛榮是有區別的。而自從瑟吉設計出這些鞋子以來…你們還是自己去得出結論吧。
“我要去科爾斯弗,130號。離市區有點遠,是嗎?”
鞋是37碼,多麼美麗的足弓!像是西方的穹頂…滿分10分,普里奧焦爾斯克圈的足部醫生,會打出應當將它們關在地下室的9.5分。
手提電話鈴聲響起,咔噠,蓋子打開了。但我們仍在看著那雙一萬塊的瑟吉·範·迪克,觀察在雙腳隨著出租車收音機的節奏搖擺時,寶石是如何閃耀的。法肯加夫。我們永遠都聽不夠。“嗨,貝蕾妮斯,親愛的!歐佐納爾!太棒了!我一直想和她們合作!不,我不會呆太久,就幾周。”
出租車車門關閉。十三釐米的高跟點在人行道上,天色開始變暗了;這裡不是暮色將至就是夜色低垂,白天哪去了?雪白的小腿閃過,背景裡的杉樹下,混凝土立方體的畫面鋪開。屋裡的燈亮著。苔蘚閃著水光,十月暴風前的寒霜覆蓋在水坑的表面。手提箱落在門前鞋子旁邊的地上。門鈴響起。傑斯帕的模特*女友*的雙腿似乎將矗立到永遠。我們從兩腿間爬過,披風叮鈴作響的邊緣似乎絕不會觸碰到我們。在到達臀部曲線之前,像鍋底一樣漆黑的世界毀滅者的梅斯克艦隊,出現在瑞瓦肖的地平線邊緣。在安妮塔的膝蓋處,時尚之都的人們已經把手放在眼眶上,發問道:海洋上從煙囪中冒出,像暴風雲一樣的不詳煙霧是什麼?
“門開著!”傑斯帕喊道。女孩走進去,瀰漫著強烈菸草味和甜味的寬敞大房間在她面前展開。傑斯帕從窗戶穿過房間。遮擋物的後面露出油亮的土豆棕色頭髮,有個人在床墊上。室內設計師接過女孩的手提箱,把她介紹給身旁渾身冒汗的肥胖男人。這個移民露出尷尬地微笑,當她和他握手時,他的手也同樣溫熱而浸著汗。
“我叫安妮塔。”女孩自我介紹道。
“我是伊納亞特,但大家都叫我汗。你也可以叫我汗。而這邊,”他指著一疊毯子,“是我的夥伴特雷斯·馬切耶克。咱們看得出來,他不太舒服。”汗覺得他做得很不錯。還有變糟的餘地:“怎麼搞的!?傑斯帕,你怎麼沒告訴我,你在跟一個真正的模特約會!酷斃了!如果我有安妮塔·倫德韋斯特的話,我會讓所有人知道!嘿,給我籤個名吧,嘿,你的姐姐是佩妮拉·倫德韋斯特,對吧,給我佩妮拉的電話號碼,然後再給我展示一下你的奶子!傑斯帕,讓她展示一下奶子!”
汗用“奶子”後的爆笑毀掉了他快活的自我介紹。它們隱藏在女孩寬鬆的時尚套裝下,他仍在盯著看。“奶子,奶子,模特的奶子,名模的奶子。”他幻想著,發出一陣接一陣的大笑。當然,他沒有注意到女孩再次詢問特雷斯的情況。
“可憐的東西。他怎麼了?”
“食物中毒。”傑斯帕挽起女孩的胳膊,帶她去臥室換衣服。汗開動腦筋在門口大喊:“嘿,那好吧,明天見,對吧!”
“你現在就要走嗎?等等,我給你叫輛出租車!”
“你和你的出租車,我情願走路。”
“再見!”女孩用友善的聲音喊道。在汗蹣跚而行穿過林間小路,去往公交車站的途中,他的腳在冰涼的苔蘚上嘎吱作響,而此時床上的女孩穿上了她的褲子。她寬鬆的波西米亞風上衣上印著瑟吉·範·迪克的肖像。肖像採用了革命性的雙色搭配方案,灰色和綠松石色,就像是模板印刷。什麼?這可不是自命不凡!範·迪克也是一種革命。一場*時尚*的革命。時尚圈的馬佐夫。只是,他沒有把資產階級流放到格拉德西北部的針葉林,他銷售它們,你懂的,衣服。
“傑斯帕,他們是誰?”
“你是什麼意思?”
“你從來沒跟我說過關於這個汗的任何事。還有另一個人是誰?”
“特雷斯。他們只是高中的老同學而已。我們不久前參加了老友會。我沒告訴你嗎?”
“沒有。”
“我們只是在追憶舊日的時光。對了,特雷斯住在格拉德。他會在這兒呆幾個晚上,我想。你不介意的,對嗎?”
“當然不。”女孩說,但她察覺到麻煩的存在。當傑斯帕去泡茶的時候,她狐疑地盯著他的背。剛才的接待殘存了一些渴望。一個極淺的吻。女孩在臥室裡生氣地踱步,接著注意到床頭櫃書堆上放著一個戒指盒。哦,一個驚喜?是為今晚準備的嗎?戒指盒離得很遠,而傑斯帕從床上伸出手剛好能夠到它。會是嗎?應該不是,但最好還是瞭解一下將要發生的事。還有——好奇心!情緒立刻好轉了。一個黑色的天鵝絨盒子,小巧的盒子。女孩打開盒子,咔噠!

--------------------------------------------
夜色籠罩了瓦薩。在科尼曼的城市中心,一隻狐狸幼崽跑過十字路口。它的氣息將空氣染成藍色,耳朵耷拉著。街道上無人且安靜,帶陽臺的老城區建築整齊地成排聳立,黃色的交通信號燈在窗戶鏡面上閃爍。夜晚的北方大都市就如同一個照明裝置——美麗的現代事物,但鮮有遊客。迪德里達達風格的皇家建築博物館漸漸顯現在河流之上,立面照明讓金色在建築上流淌。下方的黑暗裡,河水順流而下,像剛從冰箱裡拿出的伏特加一樣泛著光澤。蜿蜒的橋樑橫跨其上,背部裝點著成排的燈籠珍珠。一個獨行騎手正騎車返家,自行車發出嘎嘎的聲音,空氣中瀰漫著離別的氣味。伴隨著嗡的一聲,百貨商店拐角的廣告標誌轉為節能模式。付費電話線路上的巨型內衣模特微笑著消失了。安妮塔·倫德韋斯特。“孩子,照顧好自己。”委員會主席薩帕爾穆拉特·科內津斯基說道。“你不冷嗎?”兩位聯合探員快步登上警察局的樓梯。“特雷斯·馬切耶克!特雷斯·馬切耶克在哪?你們四天前逮捕了他!”這個男人來自內務部[97]。他是死亡天使。“特雷斯什麼?馬切耶克?”安保警官等待著機器的回答。“我們這兒沒有叫那個名字的人。”
瀝青馬路閃閃發光。塞勒姆的地面上滿是夜間的凝霜和凍結的水坑。木製房屋坐落在人行道上,街道上回響著腳步聲。在某處室內,地下室裡,伊納亞特·汗切換了“哈南庫爾”的照明模式。飛艇模型是唯一的光源,它每次亮起後又熄滅,揭露出汗的面孔。艦艇甲板上成排的燈光反射在他的鏡片裡。他有個想法,靈光一閃——其他所有的燈都熄滅時才亮起的那個。汗等待這個時刻已經兩年了。他切斷線,彷彿從搖籃裡托起嬰兒一般托起飛艇,用臂彎環繞著它跳起舞來。空空的展示櫃立在房間中央。街對面馬場的院子裡,聚光燈的白熾燈絲冷卻下來;有軌馬車消失在黑暗裡。一排馬在馬廄裡睡著了。
穿過郊區的街道,是一排排帶門閂的白色尖樁柵欄。遠處傳來犬吠,窗框在黑暗中閃著微光,木製花園傢俱空蕩蕩地立在遊廊上。誰在沙棘叢中沙沙作響?夜晚瀰漫著霜凍的味道,對未來的恐懼縈繞在核心家庭[98]的夢中。在洛韋薩的盡頭,是針葉林的起點,傑斯帕·德·拉·加迪從床上起身。安妮塔生著氣睡著了,傑斯帕很焦慮,不過不是因為她。傑斯帕找不到他心愛的束髮帶了。他穿著內褲偷偷摸摸地四處搜尋,查看床頭櫃和書架,然後穿上浴衣,撥開門簾走進客廳。從窗戶望去,端牆在黑暗裡閃著光,地板是一片雷區——牛奶盒,襪子,杯狀菸灰缸——一個叫特雷斯·馬切耶克的寄居蟹安頓在他的新殼裡。
警探的鼻子抵在玻璃上,醒了過來。傑斯帕把一杯茶擺在他的面前,聞起來像是薄荷。
“嘿,清醒點!我們稍微聊會兒,我不知道,隨便閒聊點什麼。”
“好,但我想在屋裡抽菸。”
嘴唇翕動,不時爆發出陣陣笑聲,而窗外,緩慢但肯定地,破曉來臨了。堆積成山的杯狀菸灰缸和水杯慢慢從黑暗中剝離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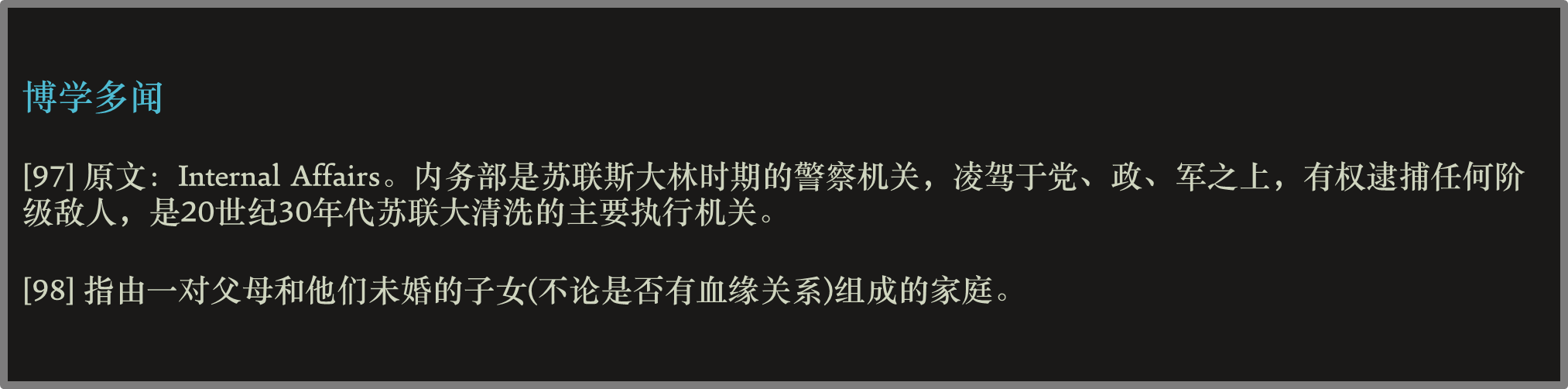
--------------------------------------------
晨光從“影院”咖啡館的玻璃後滲透進來。今天是星期三。在奧斯特姆,早起的人群熙熙攘攘,街道清掃器發出轟鳴,晨報落進一排排郵箱裡。車輛川流不息,機器操作工正在颳去擋風玻璃上的霜。
而立年將至,留著小鬍子的撰稿員正喝著咖啡,吃著炒蛋。突然,他被咖啡嗆到,跑去衛生間咳嗽。桌子上留下了攤開的晨間報紙。在公告部分,是瑪琳·倫德的筆跡複印件,上面寫著:“一切安好。我們和一個男人在一起,我們也很喜歡這裡。我們愛你們。”複印件下方是伊納亞特·汗的聯繫電話號碼,文案寫著:“好心人,現在仍然不晚。如果你有關於這封信的消息,如果是你送的信或是知道任何關於倫德家孩子們失蹤的新消息——無論是什麼——請聯繫我們。”
“我要一包含薄荷醇的‘阿斯特拉’,不,等等,‘雷達’到貨了嗎?”
“沒有,對不起,沃爾夫[99]先生,這次的撤離事件啊!沒有任何的新品到貨,我不知道我還能堅持開店多久。”
“呃,既然這樣,給我三包‘阿斯特拉’。”一位年輕的捲髮栗子頭男人說道。“那邊的黑醋栗酒,有多烈?”
“讓我們看看,讓我們看看。”售貨員從酒架上拿起一個落滿灰塵的瓶子。“哈。23度,我看是高純度的烈酒。”
“好極了,你還有更多嗎?”
“這裡有兩瓶。”
“這些和伏特加,‘終末站’。它在灰域裡陳化過,對嗎?”
“還能在哪兒呢。如果沒有,我親自帶去灰域,它就在草地後面!”
“那麼,一包火柴。一包,不是一盒。還有那些蠟燭,沒了嗎?哦太好了!我還想要這個野草莓利口酒,上次忘記買了。給我你那邊擺的兩瓶。”
“第二瓶是樹莓的,野草莓的賣完了。”
“嗯,它我也要了。你知道嗎?如果你要關店的話,最好把你所有的酒精都交出來。再來點菸薰香腸。”
“所-有酒精?”
“是的,還有半根菸薰香腸。”
年輕的捲髮男子騎著自行車穿過列敏凱寧的洛赫杜鎮,這是灰域理論災難直接影響的區域。滿是灰塵的瓶子和香菸盒混在一起,在拖車裡叮咣作響。還有半根裹在紙裡的“博士”煙燻香腸。鄉間小路上,路燈如同鑽石,在清晨的黑暗中閃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