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亂入恐怖電影,你覺得自己是被一個白衣女鬼追殺可怕,還是被吸血鬼或者喪屍追殺更可怕?
相信多數國內觀眾的答案都是前者。畢竟相較於吸血鬼,取材自中國民俗、傳說的女鬼,除了背後的文化背景會讓觀眾更熟悉外,這種“平日裡熟悉事物發生異變”的感覺,也更能誘發人內心的恐懼情緒。
而這也是如今國產恐怖遊戲多數都往“中式恐怖”題材上面靠的一大原因——想要嚇住中國玩家,自然要從他們從小長大的環境、文化或者人物上入手。
所以第一次知道《黑暗世界:因與果》(以下簡稱《黑暗世界》)背後是一家國內工作室時,我著實有些意外,因為這款恐怖遊戲的背景被設立在1984年的東德,題材也變成了國產遊戲平日裡鮮少涉及的“反烏托邦”內容。
利維坦思想局外
1
如果不事先說明,相信多數人在看到《黑暗世界》時,都不會想到這是一款國產遊戲。
你看,遊戲裡的大公司叫作“利維坦”,故事發生在1984年,主角所在的部門叫“思想局”,還有一個時刻在控制整座試驗區的MOTHER——怎麼看都是對《1984》的直球致敬。
遊戲的場景和人物設定
而遊戲的美術設計也很對味。老式的顯像管電視、氣動閥門、撥盤電話,窗戶外拉著“Mother is Watching You”標語的飛艇,色調泛黃的辦公室,以及由電線、顯示器、打字機和大型監測儀器所組成的“審訊室”:
Mother is Watching You
這些設計細節和美術表現,都更像是冷戰年代的東德風格,並非刻板印象裡國內開發者擅長的範疇。而除了題材獨特,《黑暗世界》裡比較直接的Jumpscare內容,相較於其他國產恐怖遊戲也更為稀少。
按理說,這些因素都會讓遊戲顯得“沒那麼恐怖”。但《黑暗世界》從立項之初,開發團隊月壤工作室以及背後的製作人王勇赫就確定了這款遊戲走的應該是“心理恐怖”的路線。
什麼是“心理恐怖”?和過於直白,單純用來嚇人的Jumpscare不同,王勇赫希望遊戲能從心理上帶給玩家一種遞進的感受,可能當下玩家沒有察覺,但隨著遊玩的深入,劇情演出的鋪墊,這種感受會在某個階段被釋放,從而讓玩家產生震撼或者驚訝的情緒。
沒有駭人畫面,但依舊讓人心裡發毛的場景
對於恐怖作品來說,倘若能實現心理層面上的“驚嚇”,固然是一種更高級的表現手法,但這也對遊戲的敘事、劇情編排、文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麼一款中國人做的反烏托邦恐怖遊戲,能否實現這樣的效果?
2
如今玩家在其他類型遊戲中時常提及的所謂“代入感”“沉浸感”,反而應該是恐怖類遊戲最為需要的東西。
試想一下,無論是RPG、動作還是策略類遊戲,劇情上代入感的缺失,都可以從相對獨立的玩法層面所獲得的正反饋來彌補,而唯獨恐怖遊戲(特別是以“步行模擬”作為主玩法的那類),劇情體驗和玩法高度綁定,想實現更好的恐怖效果,“沉浸感”就不是加分項,而是必需項。
如果想讓玩家在感受恐懼後還能反過來稱讚遊戲品質,那勢必需要一個合乎邏輯、能讓玩家感同身受的背景舞臺或者設定。
一個簡陋的JumpScare也許能嚇住玩家,但這隻會降低遊戲的評價
而從一開始,《黑暗世界》就試圖利用不同的手段和細節來營造這種“身臨其境”的沉浸感。
舉個例子,現在大部分遊戲都會在正式啟動前,提供給玩家調整畫面亮度、對比度或者音頻大小的選項,通常這部分內容並不屬於遊戲的一部分。
但在《黑暗世界》裡,製作組卻將這個原本和遊戲割裂的參數調整環節,化為了增進代入感的巧妙演出。
玩家扮演的角色在空無一人的病房甦醒,沒有任何旁白或者NPC出來解釋遊戲的世界觀和目標,此時一臉茫然的玩家只能推開病房的唯一一扇門,然後便進入了一個裝潢完全不同的房間,耳邊響起的是冰冷的AI提示音:
“歡迎,特別行動幹員。請就坐。”
這時候玩家才意識到,自己扮演的是一個剛康復的政府調查探員,在重回崗位前需要先接受一系列的感官矯正測試,而所謂的視覺、聽覺、空間矯正,其實對應的是遊戲內對比度、音量和視角範圍的調整:
“將亮度調整為使左側畫面隱約可見”
視角距離不僅顯示在UI上,畫面裡也會以指示牌的形式呈現
很自然的,這種模糊了遊戲參數調整和劇情設定的情節,對於玩家代入劇情,增加沉浸感有很大幫助,算是遊戲開始時一個挺有意思的設計。
而在這段調試劇情後,遊戲才正式進入了玩家更常見的,步行恐怖遊戲的那套流程——受命前往利維坦公司本部,調查一宗看似平常的物品失竊案,由此被捲入了一系列更復雜的案件中。
如果從後續的玩法上看,《黑暗世界》並沒有什麼太“新”的設計,無非就是恐怖遊戲裡常見的“找線索-解開謎題-獲得鑰匙或者密碼-前往下一個區域”,中間再加入一些追逐戰或者QTE。
但《黑暗世界》的亮點在於:幾乎所有的謎題或者互動,相互間的玩法或者表現形式都完全不同,而且與遊戲本身的世界觀或者當下的劇情設定非常契合。
就拿第一章來說,玩家扮演的探員來到發生失竊案的研究院,這段有一個恐怖遊戲裡很常見的玩法模式——角色試圖前往辦公區域,但需要先在當前場景中尋找解鎖大門的ID卡,而ID卡又被鎖在一個需要用密碼開門的房間中。
如何找到密碼?對於《黑暗世界》來說,這裡需要的不是搜查與分析,而是牆上那些無處不在的,用以監視員工行為的“攝像頭”。
在利用自身權限解鎖監控終端後,你就會發現利維坦公司對自家員工採取的也是嚴苛的高壓管理,哪個員工未保持制服清潔,哪個員工做了違規操作,哪個員工私下裡接受賄賂,統統被MOTHER操控的電屏記錄在案:
這就是“MOTHER is watching you”
在翻閱了部分監控資料後,玩家才最終獲得一條和密碼線索相關的監視錄像,從而推斷出密碼,進入下一個區域。
在前期的幾個謎題中,“電屏”既承擔瞭解謎鑰匙的作用,同時也是補充世界觀,提升沉浸感的重要元素。在後續的調查中,玩家還會在不起眼的角落發現利維坦公司對違規員工的處理文件,雖然這和主線無關,但卻非常有效建立起了玩家對“利維坦”冷漠無情的初步印象。
永久失去社會等級晉升資格
而到了第二章,玩家扮演的是一名社會等級更低的底層打工人,在某個需要推進的場景中,互動模式從搜尋線索的解謎,變成了更“枯燥無趣”的打工人模擬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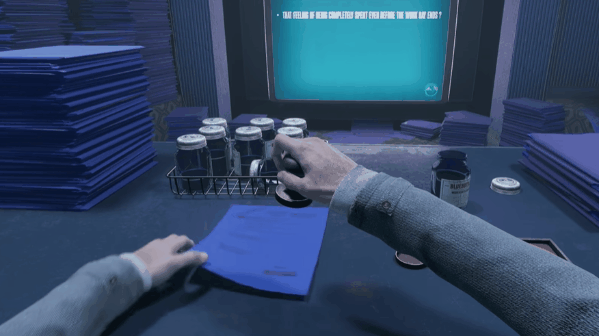 鼠標控制手臂移動,左鍵蓋章
鼠標控制手臂移動,左鍵蓋章按照利維坦公司的規定,每蓋章3份文件,印章就需要補一次印泥,我操作時自然也要嚴格遵守這個規定,任何一次誤操作,都會導致畫面扭曲震動,視野變暗,甚至是領導的“關切”,通過音樂和畫面的轉換,這段流程雖然沒有任何Jumpscare,但卻壓迫感十足。
可以說,《黑暗世界》針對每個角色身份、性格、經歷的不同,都設置了完全不同的玩法和劇情表現形式,到了下一章經歷更為曲折複雜的女研究員蕾切爾,甚至連畫風和操作模式都有了天翻地覆的轉變:
在某些特殊情節中,你需要操作的是一架紙飛機
這種針對多角色設立的不同呈現模式,好處是舞臺和視角都拉得更廣了,每一段新的劇情模式,對初見的玩家都是一次驚喜,而且也能將玩法和劇情更好地結合,沉浸感提升不少。
但它也有自己的不足,比如多內容、多視角、碎片式文案信息,同時又打亂了時間線的敘事模式,在沒有直白解釋的情況下,很容易給玩家帶來“謎語人”的印象。
3
在我花了7個小時通關遊戲後,我的第一反應其實是“最後到底發生了什麼?怎麼我還是一知半解?”
會有這樣的想法,一定程度上和遊戲的編排也有關係——多個人物、時間線相互交錯,不少專有名詞參雜其中,再加上結尾偏向“意識流”的演繹模式,讓玩家很難在第一時間就get到遊戲想要傳達的訊息。
但這種模糊的效果,其實一定程度上也是遊戲試圖呈現的部分。
作為遊戲製作人,王勇赫認為《黑暗世界》所呈現的“心理恐怖”,其實代表的是不同角色對自身情緒、記憶的掌控,這不太適合用過於清晰的表達方式,因為情緒和記憶本就是“片段型”的,存在模糊不清,甚至是錯亂的可能。
雖說是恐怖遊戲,但相較於“驚嚇”,製作團隊最開始打算做的,其實是一種“體驗感”,即讓玩家切身體驗和遊戲主角同樣的疑問或者經歷。
無論是恐懼、好奇,還是悲傷,想要完整地還原角色當下的感受(特別是被利維坦摧殘,意識模糊不清的某些角色),也許確實需要對信息加以限制,才能讓玩家有“感同身受”的效果。
另外,“碎片化敘事”要求玩家自己蒐集信息,拼湊出一個完整的故事,而以“步行模擬”為玩法的恐怖遊戲,本身就要求玩家蒐集信息,分析真相;那些因為“謎語人”而刻意留白、沒有明確解釋的設定,反過來也能成為很好的“恐怖氛圍製造器”,畢竟“未知才是最恐怖的”。
王勇赫也希望,在遊戲發售後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玩家和創作者們討論遊戲內的因果關係,碎片細節。
這麼一看,沒準平時大家厭煩的“謎語人敘事”,也許放在恐怖遊戲裡才最為合適。
結語
遊戲完整體驗後,我覺得《黑暗世界》跟其他國產恐怖遊戲最大的區別,其實不是“中式”和“非中式”,而是兩者對恐怖效果的呈現,就像製作人表達的那樣,自始至終《黑暗世界》都沒什麼太直接的驚嚇,更多的是“心理層面上的恐怖”。
但為了營造這份心理恐怖,遊戲十分具象地還原出了一個參雜虛構與現實、小說與歷史的東德世界,對於國內的獨立團隊來說,這都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