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內容主要參考論文《電子遊戲中可公度性的身體: 人與機器的系統耦合》,性質上接近論文導讀。感興趣者請參考原文。文章引用部分為論文原文內容。
本文將從簡略的由二戰開始的控制論發展歷史為軸,對電子遊戲,尤其是動作遊戲進行媒介批判。並淺談《血源詛咒》中以人機公度性為題的交互敘事(宮崎英高為什麼是最偉大的遊戲設計師)。
為什麼要從控制論介入電子遊戲研究?
使用模擬遊戲來代替成本極高,失敗損失極大的訓練和演練,在軍事領域的歷史由來已久。其中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訓練飛機駕駛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學習駕駛飛機在本質上意味著飛行和墜毀。”
直接使用真實飛機學習飛行駕駛,所帶來駕駛員真實的生命危險與飛機墜毀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對於個人和軍方都是極其高昂的代價。
最早的飛行模擬概念可追溯到一戰前夕,地面訓練裝置通過機械結構模擬飛機的多種運動。之後,隨著計算機模擬技術的成熟,數字模擬遊戲代替訓練的方案開始得到重視。駕駛員通過與計算機交互代,控制虛擬世界中的模擬飛機,代替真實飛機的進行交互。

如今,在我們的生活中,模擬遊戲早已不僅僅作為戰爭準備工具為存在。模擬遊戲的內容可以包羅萬象。動作遊戲也和模擬遊戲一樣也隨著如Steam等在線遊戲平臺的普及,蛻變為夠便捷地獲取的大眾娛樂消費品。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動作遊戲與模擬遊戲一樣,保留了之前的嚴肅軍事模擬遊戲的兩個重要的共同特點:人機耦合測試,以及基於用戶界面敘事的死亡循環。
人機耦合測試
人與機器在特定工作任務中,在高頻率的交互中相互配合又各司其職,以達成一種人與機器系統的高度協作狀態,這就是人機耦合。
駕駛飛機作戰的過程,就可以理解為駕駛員與飛機在緊張的高強度空中作戰任務中的二者通過不斷交互,形成一個整體系統,達成“人機合一”般的配合。
如今的電子遊戲,尤其是動作遊戲本質上也是訓練人機耦合的工具。玩家通過遊戲給出的影像,聲音,震動等物理反饋,快速即時自己調整的手部動作,追求熟練掌握遊戲預設好的各種可能操作。在遊玩遊戲過程中不斷磨練自己與遊戲(機器)的磨合程度,熟悉程度。最終通過擊敗BOSS的形式,達到遊戲設計者下達的人機耦合測試及格線。
每一次遭遇敵人都是一次人機協同訓練兼測試。遊戲正是通過反覆檢驗玩家與遊戲(機器)的耦合程度來判斷玩家的是否具有繼續遊戲故事的資格。(或者說,推進遊戲故事是與角色死亡相反的獎勵)
在這裡,玩家通關《黑暗靈魂》所需要的對遊戲(機器)的熟練程度與磨合程度與戰鬥機飛行員在一場空戰中殺敵並倖存所需要的對飛機的掌握度,在本質上都是一種人與機器的交互中,人機相互適應形成的人機耦合的能力。
用戶界面敘事的死亡循環
在飛行模擬中,飛行員的錯誤操作,即不符合模擬設定規則的與機器的交互,會導致本次飛行模擬失敗。模擬遊戲中的飛機墜毀,遊戲會在屏幕上通過界面提示用戶的角色,即電子化身在遊戲世界中死亡。而動作遊戲的失敗死亡提示與之一脈相承。說到動作遊戲的“死亡敘事”,那就更不用提“魂系列”那標誌性的死亡提示了。

死亡不重要,重要的是死亡之後是什麼?
而死亡之後,又是新的一次模擬訓練/復活,又是新的一次死亡。在這種循環中,“死亡”作為一種敘事上的懲罰不斷給予飛行員/玩家反饋,讓他們不斷熟悉整個機器系統的運作規則,不斷調整的自己的操作,以避免“死亡”。
“搭建這兩者(動作遊戲和模擬飛行)的工程方法論是控制論,一種反饋循環系統,所以,動作遊戲和模擬飛行一樣,它通過死亡循環檢測人機耦合效率。
這或許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從控制論譜系學的角度介入電子遊戲研究,進行媒介批評,並嘗試形成一種具有跨學科視野的普遍方法。這個想法主要基於以下兩點考慮:一是它自身作為橫跨神經科學和信息工程學的通用理論;二是電子遊戲中大量交互界面本身的設計機制也是基於控制論。”
反饋控制系統:機械與神經
二戰後期,納粹德國超越時代的武器——v1導彈在戰爭中登場。英軍的高射炮平均需要打出2500顆炮彈才能打下一枚導彈。為了提高盟軍防空系統的效率,那時早已涉足多個學術領域的天才學者維納受美國軍方邀請開始了開始改進高射炮控制系統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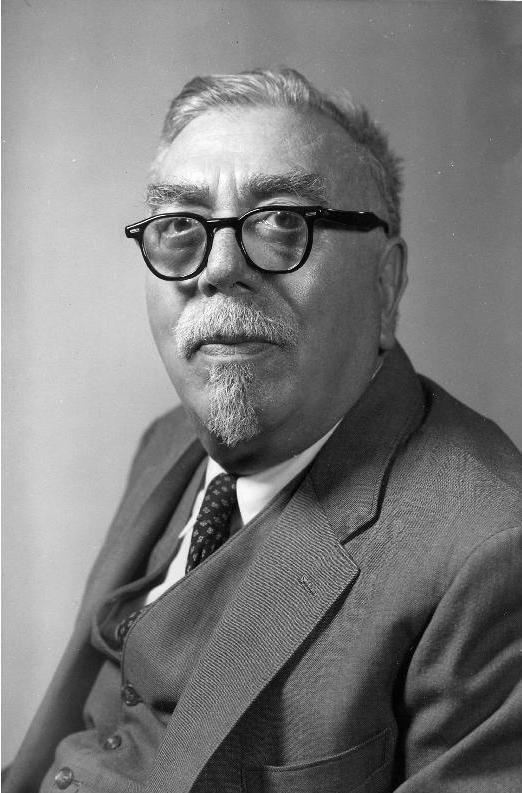
諾伯特·維納,跨學科領域大神,控制論之父
在觀察高射炮操作手的協調行動時,維納捕捉到了生物完成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反饋。以反饋為基礎,維納模仿生物的中樞神經系統的控制循環,開始設計讓人與機器自然高效交互的控制系統。
生物體的運動中存在一種的反饋控制系統。例如,人拍籃球這個動作。大腦會不斷依據眼睛傳來的關於籃球位置的視覺信息,不斷修正身體肌肉的運動。讓手跟上籃球的運動,在合適的時機用合適的力拍打籃球。
在機械工程學領域,機器部件的運動軌跡會因為各種無法避免的干擾因素,和工程師預先設計的軌跡而產生偏差。這時,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法,通過給機器輸入一段修正指令來彌補這一差距。
這種控制系統的關鍵在於,執行任務過程中,系統不斷收集反饋信息,判斷當前進度與目標的差距,並以此作為依據調整當前運作模式。這套系統的關鍵在於持續的反饋信息輸入系統內。
維納的防空火炮控制系統經過多次改進後,以圖像和符號取代抽象的參數,提高了用戶識別屏幕上交互信息的速度,以便用戶不斷及時對機器給出反饋。如今遊戲的交互界面幾乎都採用了同樣的設計理念。在以一幀為最小單位時間的遊戲世界,用戶需要快速識別遊戲系統在屏幕上給出的各種交互信息,快速控制機器做出遊戲當前形式下的合適操作。
幾年後,維納發表了《控制論》,“控制論”作為一項獨立學科正式進入學界。
SAGE系統:人機共生
1945年二戰結束,1946年冷戰開始。
伴隨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等區域性軍事聯盟相繼成立,到50年代中期,美蘇全面冷戰對峙。
蘇聯在50年代大力發展遠程轟炸機和洲際導彈。在幫助了盟軍抵抗納粹的空襲之後,美國軍工複合體再次將關注重點放到了防空系統。
與維納同為跨學科研究者的利克萊德,接過了他的衣缽,繼續研究改進軍事領域的人機交互。
在冷戰的現實主義威脅論背景下,利克萊德不會輕易放棄可能的防空系統改進方向。為了讓己方陣營在可能的戰爭中佔據空中優勢,防空系統的人機耦合效率需要更上一層樓。
在維納模仿生物神經系統的反饋循環控制的基礎之上,利克萊德進一步提出將“共生關係”這一生態學理論運用到人機交互中。與維納的“機器服務人類”式的人本主義的核心理念不同,他走向了“人機共生”的設想。
人類和機器在配合中,為了讓雙方都儘可能發揮出自己的所有潛力,利克萊德試圖讓人機雙方都更多地“奉獻自己”。
在利克萊德供職的阿帕演示小組的努力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SAGE——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誕生了。

SAGE系統
SAGE系統通過圖形界面進行目標識別標記與指令輸入,操作員可以像玩電子遊戲一樣處理防空任務。機器提供的即時的視聽反饋,開創性的圖像取代語言,讓用戶可以用更少的反應時間處理信息。在更先進人體工效學的設計下,人類可以自然地將更多腦力投注到機器之上,換句話說“更有沉浸感”。
“雷達系統通過角座標確定了物體的位置,這些角座標再根據雷達的位 置轉換為笛卡爾座標,並依次顯示在屏幕上。數據與現實的分離給圖形表示帶來一定程度的隨意性,因此不再是屏幕在工作(如威廉姆斯管的情況),而是使用顯示屏幕的用戶在工作……用這種方法進行處理,像素能夠在透明底圖上指出位置,就像在後來的奧德賽遊戲機中那樣。”
SAGE交互系統中誕生了“圖形交互界面”的這一人類工效學重大成果。人機交互時,不是屏幕在工作,而是看著屏幕的用戶在工作。用戶實際上是作為整個空軍防空系統機器的信息處理終端參與人機交互。
“編程程序的計算機和解決問題的人,都是信息處理類的物種”
同時相對應的,利克萊德設計的軟件也更加要求用戶配合機器,而不是為了讓人類的方便犧牲機器的效率。
為了追求對人機耦合效率的最大化,用戶需要在人界合作中付出更多。以往的“機器服務人類“的設計理念被替換,機器從“服務用戶”,變為“操縱用戶”。
在SAGE項目中,利克萊德對“人機共生”理念的探索與美國人機交互的技術積累,又間接影響了著名的阿帕網——互聯網雛形的誕生,不過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格鬥遊戲:閾值測試
這種對人機耦合閾值極限的不斷試探,不難讓我們聯想到動作遊戲,尤其是格鬥遊戲中,玩家對“遊戲技術”的不懈追求。以《街頭霸王》系列和《拳皇》系列等經典日式格鬥遊戲為例。一代代玩家們樂此不疲地研究遊戲中每一個角色每個招式的各種幀數數據,前搖幀數,傷害幀數,後搖幀數等被圖形用戶界面隱藏的底層“冗餘信息”。
在意識上,不斷攝取遊戲世界的有編程決定的運行規則作為養料,靈活運用並組合各種遊戲知識,開發、優化各種可能的新的策略。在肉體上,不斷訓練連招的肌肉記憶,應對的反應速度。
也之前內容提到的,人機交互中可以通過在人的方面來提高遊戲技術,當然還可以改造機器來達到相似的效果。
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格鬥遊戲界的控制器之爭。概括地來說,對於格鬥遊戲,雖然手柄,搖桿,Hitbox等不同的控制器都可以讓玩家正常體驗到遊戲應有的絕大多數內容。但由於底層技術的細節問題(其中既有遊戲編程設計,也有控制器機械結構設計的因素),讓這些不同控制器可能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存在微小的差異。例如,某些情況下,使用Hitbox釋放某個角色的某個招式,會比使用其他控制器快個幾幀。而在玩家以幀為單位精心計算的格鬥遊戲,這幾幀可能就是其他控制器不可能達到的,超越人類操作極限的差距。更有甚者,可以用特定控制器在遊戲中達成明顯不合理的有違遊戲設計初衷的操作。

感興趣請看天國大佬的這個視頻
美麗新世界
二十世紀後期,隨著計算機圖形顯示技術的進步,圖像越來越生動和逼真。圖形開始形成背景,組成人物角色。隨著圖像開始被賦予越來越多的意義,玩家沉浸感的也在不斷提升。遊戲的敘事能力越發強大,它逐漸成為一個允許玩家“進入”其中的世界。
觸摸的可逆性與機器系統的可公度性
玩家如何“進入”遊戲世界?人類與機器如何深度耦合?這裡我們引入梅洛-龐蒂對觸覺的可逆性來試圖作出解答。
(論文的這部分的大段身體與世界的抽象哲學討論對我來說相當難讀,並且我認為也偏離了我的主題,這裡只選取“身體的可逆性”這一小部分關鍵部分)
“觸摸者總是能夠變成被觸摸者” ——梅洛-龐蒂
用你的左手觸摸右手,你的左手在感知到右手上的指紋,毛髮或是溫度的同時,你的右手的被觸摸的部位也在感知你的左手用於觸摸的部位上的物理屬性。在觸摸這一過程中,觸摸者看似是主動一方,但其實它在觸摸的過程中,也將自己的用於接收刺激的皮膚暴露給了被觸摸者的感官。皮膚既是刺激接收器,又是刺激源。究其根本,被觸摸者與觸摸者擁有的兩套共通反饋循環系統,讓他們在交互時無分主次,互相作為信息輸入來源與輸出對象。此即為“身體/觸摸的可逆性”。
這也引出了論文標題中的“可公度性”的含義。人與機器,或者說玩家與遊戲,兩者各自內置的反饋循環系統,通過共同的控制論基礎,相互適應,相互調節,相互納入為自己系統的一部分。
人機互動中,人類觸摸機器,以為自己是觸摸者,而機器也在觸摸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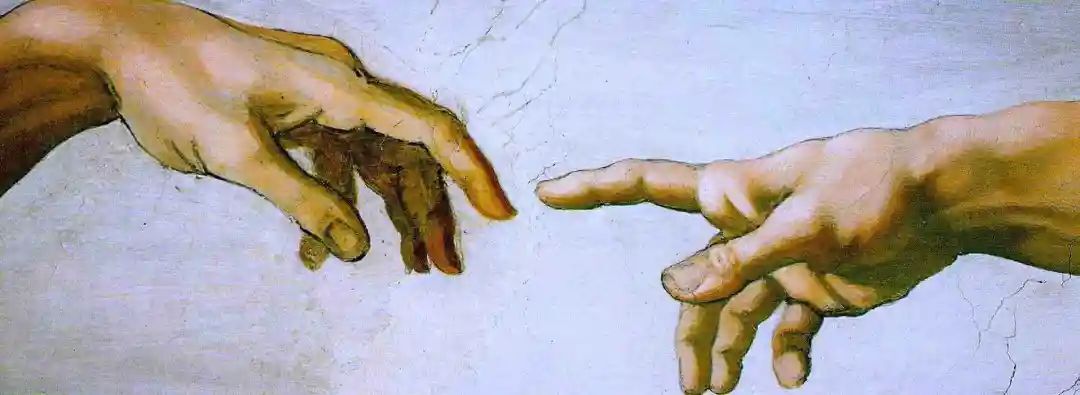
機器屏幕上的信息傳入人類的中樞神經系統的反饋循環,人類使用按鍵或搖桿將編碼信號發送至機器內部,機器內部的循環反饋系統同樣吸收並利用這些來自對方的信息。隨後機器給出自己的反饋——屏幕上的像素點刷新了……這段關係中,人類早已不是單純的主導者。
在動作遊戲的高頻率高強度的人機耦合檢測中,玩家與遊戲(機器)形成了一個更大尺度的控制循環系統。這個系統甚至允許一定時間的人機分離。比如,一位通關了《血源詛咒》的玩家,可以在幾個月後再次打開遊戲時,經過短暫的適應,就可以找回手感,快速上手。
即使經歷分離,仍然處於隨時可以“上手”的預裝配狀態(Pre-disposition 或 Pre-dispositif)。這便是我們對於機器的慾望,或者說對於影像的迷戀的形成原因, 一種習得性的“素質”(predisposition)。
也正因為這種可以習得的“素質”,在輸入的界面層,玩家永遠處於一種控制狂熱的狀態。將這種控制狂熱理解為一種界面時代個體的普遍“素質”,是之後在影遊融合媒介批評中面對大多數後人類主題或者賽博龐克主題的必要知識儲備。“
《血源詛咒》:詛咒之時亦是夢醒時分
從維納“機器服務人類”到其利克萊德的“機器操縱人類”轉變,人類需要在身體和精神上付出越來越多的東西來更好地配合機器,激發雙方最高效率。從現實主義的競技場中的生死存亡之戰(SAGE系統用於空軍指揮),到格鬥遊戲中的象徵技術實力的排行榜。在整個人與技術的異化歷史進程中,一位獨特的遊戲製作人用其獨特的動作遊戲將這種人機公度性暴露了出來。
那就是宮崎英高和他的《血源詛咒》。
《血源詛咒》通過巧妙地通過交互敘事設計將這種人機耦合暴露了出來。宮崎英高以具有自反性的元敘事,“掏心掏肺”式將自己的遊戲的控制論原理變為反派。
曼西斯夢境關卡中的特殊怪物,強大又可怕的“腦姐”在外形設計上特意使用了和友善NPC瑪利亞同樣的服裝。曼西斯的大腦對將瑪利亞視作敵人,所以誕生了可以畸變版本的瑪利亞形象。而這一怪物不僅能在遊戲系統內部威脅獵人的生命,也能在遊戲的外部,玩家大腦中的故事敘事中造成斷裂。玩家在對遊戲中獲取到的所有信息進行整合以得出一個符合個人意義的故事的過程中,不得不將和藹可親的瑪利亞的形象與這個噁心的危險敵人的形象重疊在一起。從而不可避免地交織出一副畸形融合的畫面。曼西斯由此實現了真正意義上對玩家的“精神汙染”。





1 / 2
同時又通過以“難度”(對人機耦合效率的高要求)為核心的一系列機制設計,讓玩家過度投注知覺於機器,造成知覺偏移。迫使玩家適應並反思自己與遊戲系統的互動,使遊戲過程中的人機耦合顯現自身。
這點可能再出一篇文章詳細扯扯。
總結與尾聲
從二戰的火炮改進到電子遊戲的風靡全球,控制論的歷史軌跡揭示了人機關係的本質遷移:隨著用戶界面的發展,人類與技術的關係已悄然從"操作工具"演變為"系統共生"。動作遊戲作為控制論最普世的實驗場,有著V1導彈攔截中的控制反饋機制的基因。這種跨越戰爭與娛樂的媒介批判啟示我們——數字時代的人類知覺與認知可能在與精密的電子元件迴路結合,被改造,被操縱。隨著而每一次屏幕的閃爍,維納的擔憂逐漸變成預言:人機共舞中,所謂"通關"不過是系統的編程邏輯暫時認可了我們的神經電流,達成了危險的公度性。
運用自己的熟練度,習慣般“遊玩”遊戲的玩家沉淪在控制機器的的快感中,這是賽博時代的新人類本能。人類使用媒介達成目的,媒介本身也在影響人類,而像《血源詛咒》這樣的優秀作品也在通過自我暴露“黑盒”來打破玩家的幻夢。

在人機合一的道路上,我們並沒有變得更文明,而是背離了維納發展控制論的初衷,在其後走向了自我武器化的深淵。